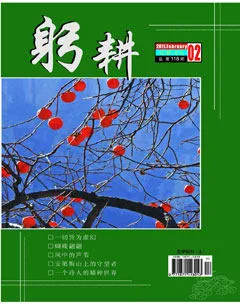蝴蝶翩翩
1
勤务兵小黑子来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肩上站着一只蝴蝶。我说,你肩上有只蝴蝶。他回过头看了看,说,没有啊。我眨了眨眼,蝴蝶不见了。我充满疑惑地看着他瘦得冬天的树皮一样的脸,也许我眼睛看花了?
小黑子的声音里充满丢失已久的喜悦,说:“连长,太阳出来了!”
我出来一看,太阳果然出来了。金色的阳光像一层层蚊蠓密密麻麻地飞过来,我把眼睛闭上的同时,朝着浸泡在战壕里的弟兄们吼了一声:“准备战斗!”
天气一晴,仗就会接着打了。硝烟会爬满我们的身体,从眼睛、嘴巴钻进五脏六腑,把我们的血肉噬光,只剩下惨白的骨头,与泥土和荒草混在一起,在月夜里散发着磷火。我看过地方志,大牛山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地方晚上总是有凄惨的磷火闪烁,有无名的幽灵在地下哭泣。开进大牛山的第一个晚上,小黑子看到满山的磷火时,居然吓得哭了。我给他讲了很多次,没有一点用,他总说那是鬼火。
我告诉他说,我们迟早都会变成那样的。从前他都不信,但这一次,看到山下一层层解放军把大牛山严严实实地包围了,他信了。不过,他又说,他不想在大牛山做鬼,他想回到老家黄地,他就是死了,骨头也要回去。我笑着安慰他说,没事的,你只是一个小兵,解放军不会怎么着你的,应该担心的倒是我们这些军官。他的眼睛泪光闪烁,嘴巴抽搐两下,低低地说,连长,那我就和你死在一起。
我笑笑说他真傻。那是一支和我们一样的正规军,怎么会杀俘虏呢?何况,我根本就没想过被他们俘虏。我希望解放军能说话算话,愿意回家的就给路费。这样的话,如果我战死了,小黑子就可以把我的尸骨带回老家,埋在父亲的坟旁,也许有一天,妹妹会拨开坟前的萋萋荒草来看我。
解放军开始进攻了。他们吹着冲锋号,高声地叫喊着,从四面八方向大牛山冲锋。在那些把云彩撕得破破烂烂的呐喊声中,夹杂着一些稚嫩的带着哭腔的声音。他们当然也是害怕的,所以,他们要在冲锋时故意扯着嗓子吼着,让我们以为他们不害怕。实际上大家都怕得要死。我们每个人都没动,但被淹在水里的双腿却在一个劲地颤抖着,战壕里的水像是即将煮开的水一样剧烈地晃荡着。他们都在咬牙控制着,脸上肌肉抽搐,汗水像灰色的蚯蚓一样爬着,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也可能那是比死亡更冷的冷汗。
解放军已经接近阵地了,他们急促的脚步落在地上,像无数只狗啃咬着大地,震得战壕上的土簌簌地往下掉,就像在水里扔了一层的钠,水真的就要沸腾了。信号弹突然升向半空,像拖曳着尾巴的花朵一样在空中盛开。我用尽全身力气吼了一声:“打!”嘴巴里有股咸味,也许是把喉咙撕破了。所有的士兵都从水中站起来,所有的枪都架在了战壕上,所有的枪都开火了。那些解放军就在不到百米的距离上,就像竖在田野里的麦捆,前面的一倒,后面的也跟着倒了,有些是被我们击中了,有些是有意卧倒的,有些还没反应过来,还闷着头往前冲,身上被子弹啃出一个又一个洞,他们双手在空中乱抓,跳着怪异的舞蹈。
那些疯狂奔跑着的麦捆消失了,所有的解放军都卧倒在地上向我们匍匐过来。这很讨厌,我们要想打中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身子更多地探出来,这样很容易被他们的子弹找到我们的心脏。很快,不断地有人栽倒在战壕里,身上的手榴弹和子弹袋把他们拖进水里,他们还不甘心地往外吐着血,很快就把水也染红了。我趴在机枪手旁边,指挥着他往人群密集的地方射击。他抱着机枪,就像抱着他的老婆,机枪的后坐力把他的身子弄得不停地抖动着,他咬着牙一声不吭,就像和女人做爱一样既投入又吃力。我刚要夸奖他一下,一颗子弹呼啸着扑到他脸上,红色的鲜血从眼睛里飞出来,带着黑色的瞳仁,掉在机枪上,就像上面落了一只红色黑色白色相间的蝴蝶。我刚要把他拉过来包扎一下,他却像到了高潮一样身子猛地向上一蹿,更多的子弹打过来,他脸上的碎肉都溅到了我的脸上,像铁匠铺里溅出来的火星一样烫烫的。我把他拔拉到一边,正要准备自己抱着机枪打时,小黑子窜过来,抢着趴在那里,说:“连长,让我来打!”
我知道他这是为我好,机枪手在战场上总是引人注目,好多的子弹都像发情的少妇一样想往他怀里钻。我退到一边,心想,等这仗打完了,我要给小黑子找个对象成家。他年龄不小了。说起来,我俩其实都是一起在黄地长大的。我父亲是老爷,他父亲是佃户。不过,向老天发誓,我早就把他当做自己的亲兄弟了。
将近五十米左右的距离,更加刺耳的冲锋号响了。解放军从地上跳起来,像海水一样汹涌地呐喊着冲过来,大地像蝴蝶的翅膀在微微颤动,他们脚上带起来的泥巴像花朵一样盛开。士兵们冲出战壕,双方短兵相接。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手榴弹跳来跳去地在周围不停地爆炸。我的一排长倒很勇敢,一直冲在我前面,我刚要叫他注意点,他猛地窜了起来,飞到了半空。我低头一看,他原来踩着了一捆集束手榴弹。我刚跑两步,有东西绊住我的脚,低头一看,一排长的上半身就在我的脚下。他脸朝下,一动不动。我正犹豫着怎么办时,一个小个子解放军扑过来,把我摔在地上。我的衣服上溅满血迹,血水滴滴答答地往下掉,衣服贴在身上粘糊糊地难受,脖子上也是血,他的手卡在上面很滑,虽然把我卡得直翻白眼,但还不至于喘不过来气。他扼不死我,这让他很委屈,眼睛里泪水都快出来了。我本来以为自己要死了,没想到他力气这么小,还当什么兵啊?我挣扎着抓起一把泥巴,挣扎着糊在他眼上,他手一松,我就翻过身来,把他压在身下,双手卡住他的脖子。他的脖子那么细,还那么白,这哪里像个士兵,简直是个女人嘛。他的双手在空中乱抓,甚至还抓到了我的脸,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疼。这个像女人一样的士兵彻底激怒我了,我把全身的力气用在手上,他的脸憋得通红,脑袋使劲地晃着,洗得发白的军帽被他甩在一边,露出长长的头发。这真是个女人!我的嘴巴大大地张着,两只手还卡在她的喉咙上,但与其说是要扼死她,不如说是在抚摸着她。手上的血液凝固了,软软地耷拉在那里,苍白得像死去的士兵的脸。我从她身上爬起来,犹豫着要不要伸出手把她拉起来。我看清了,她长得并不漂亮,脸盘子很大,涂满乱七八糟的黄色泥巴黑色硝烟,而不是像我妹妹,脸像涂了奶油,又白又有香味,小时候,我总是趁她不备,把嘴巴猛地凑到她脸上去闻那香味。为了这事,我没少挨妈妈的骂、父亲的打,但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一直到她长大了,我才改掉这个坏毛病。这个解放军女兵不可能是我的妹妹。但在那一刻,我的确是把她当做了妹妹。我也许是被他们的枪声和呐喊声震昏头了,我伸出手,把她拉了起来,喃喃地说:“你怎么在这里?”
那个解放军女兵瞪着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怪物。我的目光柔软,仿佛她不是一个敌人,而是一朵可以吃的花。虽然她装作不认识我,但我还是认出她来了,这是我的妹妹!这么多年不见了,她的变化这么大,身子胖了,脸也圆了,也黑了很多,眼角边还有了苍老的鱼尾纹。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来的。我紧紧地拉着她的手,再也舍不得丢开了,我怕一丢开,她又不见了。
但她还是挣开了我的手,往旁边一跳,脸转向我,冲着我大声地喊着什么,但她的声音被战场上的硝烟和划过头顶的枪声、刺进肉体的刺刀声击得破破烂烂。她很着急,使劲地冲我挥舞着胳膊。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想让我赶紧逃跑。我也想跑,但泥巴缠着脚,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身子软软的。她摇了摇头,转身消失在了硝烟中。整个战场模糊不清,枪声炮声仍然在浓重的空气中颤动,后来变得越来越远了,我听到蝴蝶扇动翅膀划过空气的沙沙声,听到远处树上传来咕咕的鸟叫声。阳光从黏稠的硝烟中钻出来,当它照在我的额前,我突然想起她的容颜,她像我的妹妹,似乎又不像。那么,她为什么要冲着我挥舞着胳膊,而不是丢过来一颗手榴弹呢?她认识我吗?她是谁?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颗子弹擦着耳朵飞过,炽热的火药灼得耳根发麻,但路过我的耳边时,它又变成一道闪电划过我的脑袋。我突然想起,这个解放军女兵,会不会就是半年前我遇到的那个娟子呢?战场上子弹与硝烟消失了,娟子的脸庞从岁月的水里浮上来,那么清晰,我甚至能看到她眼睫上挂着的晶莹的泪珠,听到她埋在心里的哭泣……
2
半年前的时候,我们部队一直在到处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但他们像夏天的一颗水滴落在水里,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在崎岖的山区里转悠一个多月,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抓到几个掉队的解放军士兵,但毫无用处,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在寻找他们的大部队。
那是一个黄昏,我们来到一个破烂的村庄。我们连队作为先头连,第一个进入村庄,并且找到了一座高大的砖瓦房子。玫瑰色的天空下,这座古老的宅院安静而又美丽。这一家人和我们家一样,应该是村里的大户人家,能让疲劳的士兵在这样的房子里度过一个夜晚,我这个当连长的当然很高兴。我让小黑子上去敲门,他抓着闪亮的门环拍了半天,那扇门像死去了一样毫无反应。士兵们等不及了,他们把门板摘下来,院里站着一个老太太,瞪着眼睛吃惊地看着我们。我忙安慰她说:“老大娘,你别怕,我们是国军,不是共匪,在这住一晚上就走,会给你钱的。”老太太皱巴巴的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恐惧与惊慌被笑容挤掉在地上,渗进土里,没有一点痕迹。她充满喜悦地说:“长官好,长官好……我儿子也是国军!”
我一下子觉得这个老太太无比亲切起来,甚至觉得她像我的奶奶一样慈祥。我好奇地问她,你儿子在哪个部队?她告诉了我,我有点失望,她儿子是地方保安团的,虽然还是个大队长,但我们正规军是从来都没正眼看过他们的。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像肮脏的虱子一样令人讨厌。老太太把我让进屋里,屋里正中间是一个用土坯垒起的台子,上面放着一些点心盒子什么的。奇怪的是,台子和墙之间的角落里蜷缩着一个妇女,她蹲在地上,头埋在膝盖上,头发像堆杂草一样,整个身子在簌簌发抖。老太太走过去踢她一脚,恶狠狠地说:“死到一边去!”她慌慌地抬起头,脸色比阴天的天空还要灰暗,比旱灾到来的土地还要干枯。她怯怯地看看那个老太太,又愣愣地看着我,目光落在我戴的钢盔上,上面有青天白日帽徽,目光又滑到我的衣领,上面缀着闪亮的中尉军衔,她不像别人那样目光躲闪,相反,干瘪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弱的亮光,像无边的夜色里一只孤独的萤火虫若隐若现,她的嘴唇神经质地哆嗦着,声音比蜘蛛丝还要细小虚弱:“救我……救救我……”
老太太立即冲过去又狠狠地踢她一脚,嗓子像破锣一样叫道:“你别做美梦了,你看看,这可是国军!”
她的行为让我厌恶。我把她拨拉到一边,弯下身子问那个妇女,这是怎么回事?她抬头看着我,像朵枯萎的花一样的眼睛突然有了生机,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是否要绽放。她伸出枯瘦的手抓住我的胳膊,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几乎要把我带倒在地上了。我忙把她拉起来。她的身子摇摇晃晃,就像屋顶上营养不良瘦弱的树苗,一阵风吹来就可以把它吹折了。我扶着她坐在椅子上,在她颤抖的声音里,在老太太凶恶的叫喊声中,我终于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叫娟子,是一名解放军女兵,一个月前跟随工作队在乡村土改时,被保安团袭击,队员全部牺牲,她被抓到后,这个老太太的儿子,也就是保安团的大队长,强迫她当了他的小老婆。
老太太讨好地看了看我,然后又撇着嘴充满鄙夷地看着她,恶狠狠地说:“你别做美梦了,国军会救你?哼哼,我看他们还会杀了你呢……”
我皱着眉头,充满厌恶地看着这个乡村的老太太,她再也不像我的奶奶了。我的奶奶不会这样的。娟子虽然是个解放军,但她还是一个女人啊,不,甚至只是一个姑娘。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柔和一些,问她:“你多大了?”
她的手还在神经质地抖动着,声音里仍然充满颤抖:“22岁。”
我扭过头去,院里那棵槐树的影子在残阳下拖得很长,大地呈现出一片腐烂的铁锈味。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有种想要呕吐的感觉。她只有22岁,一个月的时间,已经被摧残得像个三四十岁的妇女了。她要经历多少噩梦才会变成这样?我突然想起我的妹妹,如果她现在还活着,也是22岁了。她真像我的妹妹。士兵们正在院子里忙忙碌碌地准备着过夜的稻草,我忙定了定神,对自己说,周法五,你是个男人,是个国军的中尉连长,千万不能流泪。我其实多么想安慰安慰她,告诉她,你别害怕,我虽然是个国军,我们在战场上也许是敌人,但现在不是的,你只是我的妹妹,一个被伤害和侮辱的姑娘。我甚至还想让她趴在我的肩上好好地哭一场。
那天傍晚,我把她带到了村口。一切都很顺利,那个老太太瞠目结舌地看着我们走出她家的院子,一句话都不敢说。别说是她,就是他那个当大队长的儿子来了,对国军同样不敢有半点不恭。我看着她,她脸上有了些红晕,眼睛像受伤的蝴蝶,有种挣扎着要向天空中飞去的小小喜悦。她甚至还有点害羞,低着头喃喃地说:“谢谢你,可如果你的长官知道了……你怎么给他们交代?”
我苦涩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说:“我们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坏,我们其实都一样……你一直向东走,也许会遇到你们零星的游击队。”
她的泪水在眼里打着转儿,像梦一样的目光飘过我的头顶,看着不远处的山头,喃喃地说:“我们是敌人,可你、可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终于汹涌而出,我把脸扭向一边,喃喃地说:“我妹妹也是解放军……”
3
我没骗她,我妹妹的确是名解放军。
我知道妹妹当了解放军那段时间里,总是做梦,常常哭泣着从梦中醒来。那都是一些奇怪的梦。我经常梦到自己变成一只鸟,从我家的窗户里飞出去,飞到外面的树上唱歌,好像唱的是《义勇军进行曲》。那是和日本鬼子打仗时,一个叫田汉的词作家写的歌,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军,都喜欢这支砍向日本鬼子头上的歌。那时我们都是一家人。后来把日本鬼子打跑了,就开始打仗了。他们还把我父亲也枪毙了,说他是地主恶霸。我想不明白,他们杀了父亲,妹妹为什么还要当解放军呢?说到底,她从来没拿我们一家当自己的亲人啊。我感到很委屈,向老天爷发誓,我从来都是把她当做亲妹妹的。
妹妹是父亲捡来的。她刚出生就被扔在一条山沟里。那是我出生后的第二天。父亲那天正好从镇上回来,他把妹妹从苍蝇和蚂蚁那里夺了回来,塞进衣服里抱回了家。父亲给她起了个名字叫麦子。
每次回忆往事,我总是禁不住流泪。父亲是个好人。他虽然早就死了,但我还是很怀念他,在共产党没有来到黄地以前,他整天脸上都洋溢着天高气爽的笑容。共产党来了,他就成为恶霸地主被枪毙了。后来,我遇到黄地的一个乡亲,他给我说过父亲被枪毙时的情景,他跪在村子西边许河的沙滩上,很不争气地尿了一裤子。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他只是一个农民,一个有很多地的农民,一个天天起得很早挎着筐子捡粪的农民。我们当兵的都怕挨枪子,何况他呢?
在父亲死掉之前,我就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准确地说,有7年了。我是15岁那年离家的。那年,我和妹妹都在县城上完了中学,父亲说,到省城上大学吧。我们就去了,我上的是军校,妹妹上的是女子师范学院,她没上完,就参加了共产党,然后就跑出去当了解放军。我以后就只能在梦里见到她了。我很想她。我小时候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躺在我身边,经常和我一起争夺我妈乳房的小家伙并不是我的亲生妹妹。那时我不但不喜欢她,相反还恨她,她总是让我吃不饱,我嗷嗷地叫着,把母亲的乳头咬得很疼,有时母亲嘴里喊着“小祖宗”,但手却毫不客气地在我的小屁股上来上一巴掌。我长大以后读了很多书,按照书上的说法,我在潜意识里应该恨我妹妹,把她从小恨到大,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相反爱上了我妹妹。父亲一直对我的婚事放心不下,曾经托了很多人给我说媒,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喜欢的是妹妹。如果我能找到她,我宁愿不当这个军官了,带着她远走高飞,远离战争,和她安静地过完这一生。
那天,我把那个叫娟子的解放军女兵送走了,我告诉她,我妹妹叫周法玲,如果你见到她,请告诉她,他的哥哥一直在找她。我甚至冒着泄密的危险,把我们部队番号也告诉她了。后来我就再也没做过自己变成一只鸟的梦了,总是梦到长大以后的妹妹。她站在我面前,笑嘻嘻地淘气地看着我,阳光在她黑油油的头发上跳跃,她穿着英姿飒爽的军装,像一棵美丽的树。
惟一让我遗憾的是,我总是看不清她穿的是解放军军装,还是我们国军的。
4
过了几天,解放军的又一波进攻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漫延到了整座大牛山。
我们无法扼杀解放军的凌厉攻势,越来越多的国军士兵崩溃了,像一只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扔掉步枪,抱着脑袋四处奔逃。那些解放军士兵狂吼着,呐喊着,愤怒地朝远处的敌人射击着,朝近处的敌人抡起枪托,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狠狠地砸下来。那些国军士兵来不及哼叫半声,脑袋就被砸碎了,脑浆迸溅出来。解放军士兵脸上充满坚毅的杀气,他们向一切阻挡他们前进的敌人扫射、砍杀,他们自己生产的那种一炸就成两瓣的手榴弹再次发挥了威力,一排排手榴弹盖天铺地飞过来,像蝗灾时期的飞蝗一样,几乎要把阳光遮住了。到处是纷飞的碎肉和鲜血,他们跳过壕沟,踩着鲜血和地上的断胳膊断腿,冲进人群,只要是活的,他们就要把他消灭掉,让他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残余的国军只能边打边撤往山顶上的第二道防线。解放军尾随而来,他们从硝烟里冲出来,端着寒光闪闪的步枪,呐喊着冲上阵地。
父亲的亡灵在天上看着我,我只能把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把我杀死。从我听说父亲被他们枪毙的那一天起,这就是我注定的命运。如果遇到妹妹,我最想问她的是,她如何能做到没有仇恨的,如何去爱他们的。她如果能爱他们,为什么不能爱我们的父亲?她的爱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恨我的妹妹,还是爱她。爱与恨折磨得我快要发疯了。我多么想见见她啊!她是什么模样?容颜是苍老的,还是年轻的?是茁壮成长的树,还是含苞欲放的花朵?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亲人?是一个陌生人,还是我的爱人?
在血肉横飞的杀戮中,我挥舞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感觉杀死了很多人,有时是把刺刀捅到他们的脖子上,有时是捅到肚子上,拔出刺刀时,他们的鲜血喷出来,我的军装上都是血,我的脸上也是血,分不清是我的,还是他们的。它们甚至从额头上流到了下巴,滴滴答答地往下掉着。
我甚至都不知道捅死的是解放军还是国军,只要眼前有活动的影子,我都会扑上去。所有会呼吸的人都是可怕的,同样的面孔,同样的表情,我无法分辨,也无需分辨,我们都一样是群疯子。
一个铁疙瘩滚到我的脚下,很奇怪地冒着一股浓烟。我吸了一下鼻子,闻到了硫磺的味道。我瞪大眼睛,那是颗手榴弹!我的脑袋嗡嗡地叫了起来,就像被手榴弹砸了一下,眼前发黑,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了。我不想死,我现在不想死啊,可我就要死了,妹妹……
有个黑影突然蹿过来,使劲地把我撞到一边,猛地扑上去压在那颗冒烟的手榴弹上。我重重地摔在地上,当我抬起头来,一声闷响,泥土和血肉碎片朝我飞过来。它们虽然都很柔软,但打在脸上,还是有点疼,脸上像是爬满蚂蚁,痒痒的。我抹了一下脸,把那些泥巴和碎肉末子甩掉,把那个人的身子翻开。他的胸口被炸了一个洞,酱紫色的肠子挂在身上,就像缠着一条条可笑的绳子。他的眼睛虽然紧紧地闭着,脸也被火药熏黑了,但我还是看出来了,他是我的勤务兵小黑子。他是我当了军官后,他父亲把他送到我身边的,说是想跟着我出息出息。我感到很难过,胸口像被人狠狠地擂了一拳。我如果再回黄地了,他父亲如果要问我,我怎么说呢?他跟着我不但没有出息,反而死了。我怎么给他说呢?
我抬起头来,突然又看到了那个解放军女兵。她咬着吃惊的嘴唇,愣愣地站在那里。她的手里端着支步枪,枪刺上还滴着鲜血。她把刺刀指向我,但她既没有刺向我,也没有开枪射击,就那么呆呆地看着我,整个身子僵硬在那里,就像用泥巴捏出的塑像一样。我眼睛被血和汗水遮住。我用袖子擦了擦脸,再睁开眼时,她已经到了我跟前,那支步枪扔在脚下,刺刀温柔得像只猫。她低下头,从挎着的背包里抽出一条绷带,把我的胳膊抬起来,上面有条刺刀划过的长长的伤口。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少女的清香穿过刺鼻的硝烟弥漫过来。她的影子在我面前乱晃。我想用手拨开她长长的秀发,看看她是谁。但我的泪水又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模糊了双眼。她仰着脸看着我,我却看不清她。她也许是我妹妹,也许是娟子,也许是我前几天遇到的那个女兵,也许都不是……
一颗炮弹呼啸着飞过来,像个迷人的少女,远远地抛着媚眼。我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她,想再次把她压在身下,让她躲开那些像蝴蝶一样的弹片。但她还是把我重重地推开了,我看到她向天空伸着手跳动起来,舞姿优美,像盛开的花朵。接着,我就看到我的腿和胳膊飞起来,在半空中翻着跟头,呯地砸在地上黏稠的鲜血上。我重重地仰面倒下,鲜血四溅,就像躺在一朵花里。
我站了起来。小黑子也站了起来。他垂着头,伤心地看着被炸开的胸膛,慌慌地把肠子往肚子里塞着。那个解放军女兵也站了起来,她的身体上布满弹孔,阳光穿过弹孔射过来,晃得我眼睛总想流泪。她看着我,笑了一下。我忙也笑了一下。后来,我们就坐在阳光下,周围的枪声与呐喊声砸在地上,大地仍在颤动,但这已经和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坐的那块地上,非常干净,没有鲜血和破碎的肢体,绿草夹杂着无名的野花,蝴蝶翩翩起舞。她躺在我怀里,我拨开她的头发,用袖子擦去她脸上的鲜血和泥巴。她睁开明亮的眼睛,眼睛里盛开着红色的玫瑰花。我的泪水像家乡黄地的蝴蝶,落了一脸。阳光穿过厚厚的硝烟,她用手擦着我的泪水,微笑地看着我,喃喃地说:“哥哥,哥哥,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