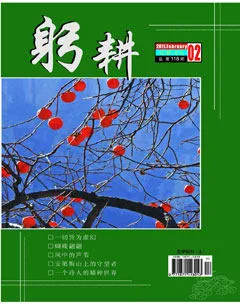一切皆为虚幻
1
左似乎听到卫生间外面有人喊:解个手也这么慢啊,准备蹲一下午?
其实左知道外面没有人。这栋两层小楼里就她一个人在家。她是在假设外面有人喊自己,赶快从这马桶上站起来,赶快把脑海里臆想的那个人赶出去。
但左突然意识到,原来想一个虚幻的人比排泄的痛快更痛快。这想法一冒出来,她禁不住吃吃笑了起来。
她从卫生间里出来。穿过一个不算宽的走廊,然后拾级而上。不用数,脚下连转台总共是23级台阶。她再熟悉不过了,她能一阶阶地蹦着上去。她喜欢走在室内楼梯上的滋味,那种贵族式的风格曾经让她非常陶醉。所以在夏天,她喜欢穿着长长的丝质裙子在楼梯上跑上跑下,去屡次领略那种贵族气质的美。那一刻,她或许感觉自己是一个贵夫人,或者是一个公主,无论是贵夫人或公主,都比她现在真实的平民身份要好得多。她厌恶平民的日子,所以她极端想使自己成为贵族,哪怕臆想一下都成,毕竟暗自过了一次贵族的瘾。
与其他情感相比,左更喜欢的是爱情。无论是贵族式的还是平民式的,她都喜欢,而且屡次品尝,百品不厌。潜意识里左认为自己天生是为爱情而活,假若没有了爱情,生命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当然,她也常为自己这样大胆的向往和追求而愤怒。她甚至鄙视自己——一个女人,一个有夫之妇竟然不懂得遵守妇道,不懂得三纲五常。但话说回来,左无论邂逅任何一次爱情,都基于与对方平等互爱的基础之上,并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举动(尽管非法的爱情其实就是对社会的一种伤害,无论它自己有没有刻意为之),甚至于非分的臆想都没有,她是真纯的无私的(除了情感上她是自私的以外),她可以坦荡得于心无愧。
左想着这些的时候,已经走到楼上书房里了。她打开电脑,漫不经心地在网上溜达起来。眼睛盯着荧屏,而脑子里仍然想着刚刚在马桶上臆想的爱情——那个男人。网络世界无论多么丰富,多么让人眼花,左始终打不起精神来。那个男人似乎鬼魅似地跟着她,撩拨着她沉寂的心扉。
此时刚刚入腊月。天气干燥而寒冷。暖气片在左的电脑前已经开了有些时候了,左渐渐感到了它的温暖。但左的手指却仍然冰凉不怎么听从大脑的调遣。左爱冷,打小就这样。她的手每每在冬天都会冻坏。记得小时候,常常是在腊月里用一条白色的棉纱缠起来,因为那手指上已经是冻疮溃烂不堪。缠了棉纱的双手不能着水,左就不洗脸,或者是让妈妈洗。但妈妈忙着的时候就无暇顾及她了,因此整个冬天里,左几乎都是脏着一张小脸。但左有一双特别明亮黝黑的眼睛,兴许是眼睛里的水特多,那双眼就格外黑亮有神。每当人们看到她的脏兮兮的小脸上一双黑乎乎的大眼睛水灵灵地看着大家笑话她的时候,就格外让人怜惜。于是,邻居就会为她洗把脸,还抹上一点雪花膏。左也就香喷喷的了。抹了雪花膏的左,心情愉快得忘记了自己的一双烂手,就会燕子似地在院子里飞来飞去。
坐在电脑旁的左,一心想着脑海里的那个他。他是谁?其实左也不知道。或许,他只是她的又一次杜撰的爱情?说不准。反正左这会儿时时刻刻在想着他。
左只和他通过三个小时的电话。左连照片都没有见到过。但左却深深迷恋上了他的声音。左只知道他和自己年龄相仿,有着一口非常柔软的普通话。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像从山涧小溪里流淌出来的泉水一样清澈活泼,又像清晨的一抹阳光那样纯粹明朗照亮人的心扉。他们第一次通电话的时候,是他给左打的。他是左的函授辅导老师,在北方一个理工大学任教。左的一篇论文问题百出,于是就接到了老师的批评。左知道老师有一个很俗的名字,叫尚官。没看字的时候,左还以为他姓上官呢,谁知道竟然叫尚官。大概老师的父母想望子成龙吧,就起了一个单字官。左素日里最讨厌做官的人,虽然她极力崇尚贵族生活,但充其量她也不过是幻想一下小说里那种优雅的西方式的贵族而已,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那种华贵美丽的贵族生活,而对于身边现实中的真正的官,她却嗤之以鼻。但老师是老师,自己不能强行把自己的意志加入进去。何况名字又不是自己起的,即使父母崇尚做官的也不为错。左当时也就只是这样想了一下老师的名字,随后也就很快忘记了他。直到那天她接到了尚官的电话,才改变了她对他的态度。
尚官说:左,你的论文可真让我刮目相看了。南辕北辙,你可真能写!你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吗?
左愣了一下,心想这是哪位老朋友啊,这么多事?就旋即问道:谁?你是谁?
当左听到对方报上姓名的时候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个辅导老师竟认真到和自己打电话的程度。一般说,他们这些函授生的论文,老师可以随意打分的,即使不合格学生也可以补写一次,再有怨言也没办法老师。还没听到过有哪个老师亲自为学生的论文打电话的。一时间,左有点不知所措。但很快,左从老师的口气中听出了自己并没有多少危险,而相反,这个叫尚官的老师非常关注自己。其实左很清楚自己的论文原本就是拿来应付老师的,她只是将网络上一些东西拼凑在一起罢了。而拼凑的时候自己也没有亲自动手,还是求了弟弟帮忙,然后打印出来就上交了。根本就没有细看那篇论文,还以为老师也不会细看就会给分的,谁知道竟然惹出来麻烦了。
让左更没有想到的是,尚官竟然在长途电话里给她谈了一个小时的论文写作。注意,是谈,而不是讲,是像朋友们聊天那样的谈。当电话挂断的时候,左甚至还有点恍惚,不知道自己今天是中了哪门子邪和一个陌生的男人通了这么久的电话。虽然他们只是谈了论文,但话里话外却格外亲切,就像分明早就认识,分明是多年的朋友似的。
尚官有意无意地给左说了一个电话号码。说出这个号码的时候,他说,这是我宿舍的号码,哦,我租赁的房子。嗯,可能我不会搬家的吧,就这个吧。
此后,左就知道了尚官家的电话号码。至于手机号,不知道为什么却并没有提起。后来,左放下电话发了一阵子呆才忽然想明白,尚官是一个人居住。他是只身一个人在北方工作,而他的家在左的中原。原来他们算是老乡,虽然左居住的城市离尚官的老家还很远,但毕竟是一个省份的。于是,左似乎从电话号码里悟出了点什么来,但又说不准。可无论怎样,鬼使神差,那个号码就像一串亲切的乡音冷不丁地就会响在左的脑海里。
左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就会不自禁地想起尚官来。她会把他昨晚甚至于很久以前电话里说过的话,仔仔细细地在心里过滤一遍,再重复一遍,而后,暗自笑笑,再继续冥想那些在自己心底听过又说过了无数次的话——总之,她对尚官的话百听不厌百想不厌。至于为什么,左只感到一种朦胧的愉悦,但自己也说不上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愉悦。
左去厨房接水的时候,听着水管汩汩流淌的水声,想着尚官的音容笑貌。其实他怎么会知道尚官的容貌呢?但说不清楚为什么,左固执地认为他绝对长得像一个人。像谁?左想了想,毫不犹豫地说:像牛怀玉。天,牛怀玉是谁?噢,就是正在播放的电视剧《京华烟云》中那个饰牛怀玉的演员!对,绝对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左为自己的第六感觉高兴。她喜欢牛怀玉,说不上为什么。或许是尚官的声音十分活泼柔和吧,或许尚官开朗的笑声和阳光一样的性格,总之,尚官绝对和牛怀玉长得一模一样。至少,他们有着弟兄一样的脸庞,都留着平头,个头也都是中等。左这样想着,那水壶里的水早就溢满了,一个劲儿往水池里流。直到那哗哗的水声把水池流满水漫了出来,左才如大梦初醒。
晚上睡觉的时候,左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有时甚至很短的一觉醒来就再也无法睡着了。左就闭着眼,在床上翻来覆去想心事。丈夫在身边鼾声一阵阵地传来,左似乎根本就没有听到。有时丈夫的鼾声大了,左就将身体翻到另一边,避开他那呼噜。而这时,左会兀自感觉自己犯了错误,脑海里有种不着边际的味道。究竟什么不着边际,她自己也无法说清楚。要说是自己犯了错误吧,可自己连尚官的面都没有见过,更谈不上有什么越轨之举了。可要说自己没犯错误吧,这怎么身边睡着一个大活人硬是生生看不见他?自己心里根本就没有他嘛。左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一直到天蒙蒙亮。
早上起来,左梳洗。毛巾在脸上使劲地擦来擦去,却忘记了该用什么护肤品。她想了半天,愣是又将洗面奶涂到了脸上,起泡泡的时候才想起来,已经用过洗面奶了。于是笑自己发呆,笑自己胡思乱想什么?
2
隔了几日,尚官的影子还是无法消失。准确地说,是尚官的声音加牛怀玉的容貌组合成了一个崭新的影子。那影子鬼魅一样跟在她的身后,在她举手投足之间跃跃欲出,她想甩都无法甩掉。于是,左就想给那个影子打电话。当然,那影子现在就是尚官。她必须打尚官的电话。可尚官究竟是否愿意接听她的电话?她没有把握。或许尚官会接,或许只是因为情面应付而接。而这些左都不能把握。如果尚官只是应付她,那多不好?那还不如不打,自己会很没有面子的。毕竟,自己是女人,女人应该有女人的自尊。左就这样犹豫着。
时间又过去了两天。尚官这个影子把左逼得快要窒息了。左没办法再犹豫了,于是就拨通了尚官的电话。尚官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是那么的近,连呼吸都听得很清楚。尚官的声音是那么柔软,那么温和,又那么活泼自然。这些都像磁铁一般强烈地吸引着了左。当这声音进入她的耳廓时,她立即感到浑身舒畅,血液流淌愉悦,整个人仿佛进入了一个偌大的磁场,那磁场给予了她神奇的快感。两人不知不觉就说了四十分钟。左知道这是长途,每分钟要七毛钱的,很贵。该挂电话了,左想。但尚官仍然是滔滔不绝。而他的声音又仍然是那样的清新甜蜜快乐,像一个天生快乐的孩子。于是,左又不忍心去说那个再见了。其实尚官也早就意识到该挂断电话了,也曾说了一句“不说了吧,该休息了”。左也“嗯”了一声。但不知道为什么,两人都没有挂断,而是不知道谁又提了个新的话题,接着说了下去。这样一说就说到了一个小时。眼看着电话机上的时钟闪到了60分钟上,左不得不和尚官说再见了。
左说:嗨,好了不说了,很晚了你该休息了。
尚官说:该休息了。
左说:嗯,再见。
尚官说:嗯,再见。
左接着说:晚安!
尚官说:晚安!
这样两人终于同时放下了话筒。
话筒放下的时候,左的手心里仿佛仍然温暖。此时她两颊绯红,鼻尖上闪烁着细微的汗粒。而这是十一月的深夜,寒气正一阵阵地缭绕在书房里。直到左感觉一张脸由发烫渐次变凉的时候,她才怔怔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然后下楼去盥洗间梳洗准备入睡。可那天晚上无论如何,左也只能是辗转在床上,脑海里不停地翻滚着刚刚交谈的话语。尚官——左假设的那张脸,在他刚刚消失的声音中越发生动起来。
星期天的时候,左去加班。当左忙完了手头繁杂的事物,忽然想起尚官来。尚官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在看书还是在逛街?在和朋友们一起喝茶聊天吗?左冷不丁冒出了这样的假设。于是她的眼不由自己地盯着了灰色的话机,就这么盯了几次,终于鼓足勇气拿起了话筒。可当她的右手刚刚拨了一个号码,就啪地一声挂断了。她想起来了,他们之间好似从来没有在白天通过电话,现在打合适吗?他的屋子里会不会有外人?他会不会感觉接听不便?会不会因为电话铃响不断而又不得不去接听,然后为此而不安烦躁发怒?想到这里,左就立即挂断了电话。可当左放下电话后又有点不忍心。面对话机,她的脸有些许的激动,又身不由己地想,现在是星期天啊,他一个人在北方生活,应该不会有什么客人吧?想到这里,左就再次拿起了话筒。
电话很顺利地接通了。尚官在遥远的北方好似一直在等左的电话似的,拿起话筒就说,我在打扫卫生!左笑了,兀自感到周身轻盈,情不自禁地笑着说,就知道你在家嘛!两个人愉快地聊了很久。就在电话快挂断的时候,尚官对左说他要回中原一次,下星期二回来,说是要给儿子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左愣了一下说,把儿子迁到北方吗?尚官肯定了。于是左骤然有点失落的感觉。至于尚官给儿子迁移户口有什么对或不对,左说不清楚。但她的确有些许的失落感。
转眼到了下个星期二。左惦记着给尚官电话。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左拿起了话筒,正要拨号转念一想,算了,也不能人家回来就给人家电话啊,显得自己多没有架子一个劲地屁股后面追着,还是明天再打的好。
第二天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左拨了尚官的电话。没人接听。左想大约尚官在单位还没回来吧。尚官说他住的地方离工作单位很远,要乘上很长一段路程的公交车才行。他每天几乎都十点左右回家的。想到这里,左就耐心地等待着。她打开电脑,也无心上网,就随手在键盘上敲打着自己的心情。等敲过之后一看,没想到敲出来的字全是尚官尚官,左禁不住开心地笑起来。
好不容易等到十点钟,左又拨了尚官的号码。电话铃响了四次,就听到了尚官气喘吁吁的声音。左就温柔地喂了一声。
啊我刚回来。是不是想我了?尚官说。左听到这话,倏地愣着了,一时竟然语塞,以为是尚官刚刚从单位回来,可好像又不对劲儿,又不知道该不该回答自己是否想他了。关于这个问题,似乎左还没有考虑到,但仔细一想,如果自己不想尚官的话,为何老紧紧地追着给人家打电话?那应该是想。可想吗,是不是显得太早,这话说得仿佛已经是一对亲密的恋人似的,可他们除了聊天什么私房话都没有说过啊。想到这里,左决定避开这个问题不回答,而径直问尚官是不是刚从单位回来?
谁知道尚官竟然说刚从中原回来。这一下左还真的愣着了,想到自己原本是故意往后拉了一天打电话的时间,没想到还是打在了尚官风尘仆仆返回的节骨眼上。这不明摆着自己一直惦记着尚官吗?也难怪他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想我了。想到这里,左很高兴,至少,尚官知道自己在想着他了,这说明他对自己也是有了感觉的。
左从尚官的声音中听到他果真一身疲惫风尘仆仆的样子,就不忍心占用他时间和他多聊了。正准备放下电话,没想到尚官却说,下一次打电话别这么勤了啊?隔几天再打。左一听这话,兀自脸红了起来。虽然她知道尚官看不到她的双颊发烫,但还是有点温怒。于是就佯装生气地说,好啊,你听着,我不给你打电话了!尚官笑了,赶忙说,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尚官还是没表达清楚我究竟是什么意思。但左知道,尚官是矜持的。他并没有拒绝自己的意思,但他同时肯定为自己刚才那句“是不是想我了”的问话而后悔。
电话挂了的时候,左下决心对自己说,这次非隔上一段长长的日子再打尚官的电话不可。
3
果真,有一段日子左没打尚官的电话了。但没打是没打,并不等于左没想他。他的影子仍然和他那温和爽朗的声音一起在左的眼前晃来晃去。
那天,左把重新写过的论文寄给尚官的时候,感觉应该写封信附在里面,起码也得说上几句感谢之类的言辞。于是她就顺手找到了一个很小的便笺。当她拿起笔写的时候却兀自写下的并不是感谢的话,而是这样写的:
尚官老师:
论文寄去,请审阅。另寄一篇题外话《我的童年》,那是我的自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顺便看看了解一下我的成长。当然,也可以随手投到碎纸机里去。只是,别忘记将钉书钉拔掉!
左 11月29日
写完这段话,她自己歪着头看了看,忽然想起那篇《我的童年》忘记带了。于是她想了想,记得电脑里存储的有,就重新打印了一份塞进了信封。然后用胶水封住了信封的口。做完这些,左才忽然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啊,怎么把自己的童年寄给他了,那可不是论文而是与论文风牛马不相及的啊!而寄给他又是什么意思呢?左仿佛忽然糊涂了似的,一下子竟然想不明白了。唉,怎么回事?她感觉自己有点不可思议。但信封已经封上了,就由它去吧。左这样想着。
那封论文寄出后,左天天盼望着尚官的回音。她知道尚官是不会给她回信的,可又通过什么方式给她说呢?噢,对,尚官知道她的电话。他肯定会打自己的电话的,至少也会给自己个短信说一下论文收到了。
但恰恰相反,十多天过去了,左并没有收到尚官的任何信息。他既没有打她的电话,更没有给她发任何短信。左想发过去个短信询问一下吧,又不知道他的手机号码。而打电话,左是万万不能的。自己决不能在人家刚刚谢绝了电话的时候,再打过去,那样实在是太没女人的面子了。女人原本就不该主动的。可是尚官迟迟没有音信啊,真急人。那么怎么不用其他的通讯方式呢?比如伊妹儿啊Q啊。哦,这些通讯方式可能尚官根本就不知道,或许他也没有电邮信箱和Q号码的。尚官虽然和自己同龄,但人家是事业型的,绝对不会是个网虫。想到这里,左突然很后悔,自己为什么在那么多次的电话中,不问他要手机号或者问问他有没有邮箱Q号什么的?唉,真是的。看,如今只能被动地等待了不是?
左如此想着,就只好耐心地等对方的音信了。
转眼又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