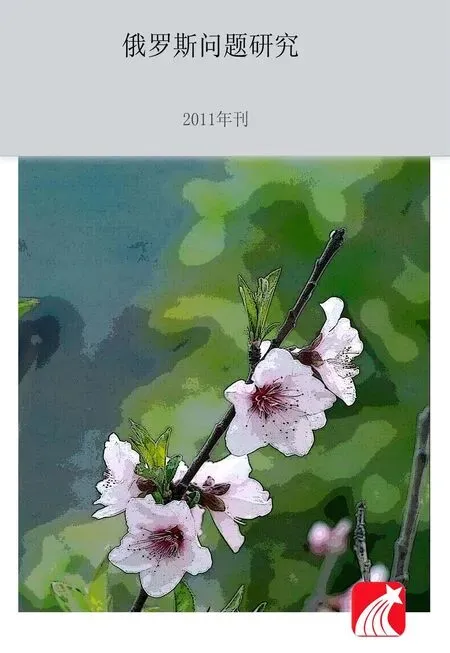关于苏联解体:你所了解的一切都是错的
列昂·阿伦 著 赵铁铸 编译
关于苏联解体:你所了解的一切都是错的
列昂·阿伦 著 赵铁铸 编译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7—8月号刊登了《关于苏联解体:你所了解的一切都是错的》一文,作者列昂·阿伦系美国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部主任。现将主要内容编译如下。
每一场革命都是一次意外。尽管如此,最新的俄罗斯革命应该属于最大的意外之一。在1991年之前的数年里,西方的专家、学者、官员和政治家没有一个预见到苏联即将出现的解体,因为当时苏联拥有一党专政、国有经济和克里姆林宫对国内和东欧诸国的控制。1993年,保守的《国家利益》杂志关于苏联解体的专刊文集标题就是“苏联共产主义的离奇死亡”。
事实上,1985年的苏联拥有与十年前大体相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当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大多数东欧国家,更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物资短缺、食品配额、商店前的长队和严重的贫困随处可见。然而,苏联曾经经历过大得多的灾难而且应对自如,丝毫没有放松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更不用说放弃控制了。
1985年前的任何主要经济指标都没有显示出一场灾难马上到来。从1981年到1985年,苏联的GDP增长率尽管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相比有所放慢,但是也达到了平均每年1.9%的水平。这种无精打采但也算不上悲惨的增长模式持续到了1989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财政赤字一直被认为是革命危机即将出现的突出征兆之一,但是1985年苏联的财政赤字不到GDP的2%。尽管苏联的财政赤字增长迅速,但到1989年仍然低于GDP的9%,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属于可控范围内的规模。与此同时,198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超过了2%,直到1990年的5年里,工资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继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了7%。当然,苏联的停滞状况非常明显,令人担忧。但是,正如卫斯理大学教授彼得·拉特兰所指出的那样,“慢性病毕竟不一定是致命的疾病”。
从苏联政权的角度来看,政治环境也不是那么棘手。经过20年对政治反对派的无情镇压之后,几乎所有知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要么遭到囚禁、流放(安德烈·萨哈罗夫自1980年后一直被流放)、被迫移居海外,要么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之中。
苏联似乎也没有任何其他的革命前危机迹象,包括传统上所说的国家失败的其他原因——外部压力。恰恰相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官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所说的那样,苏联在解体前的十年里接近于“实现了所有的主要军事和外交目标”。当然,阿富汗战争看起来越来越像一场漫长的战争,但是对拥有500万人的苏联军队来说,那里的损失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也不是苏联解体的催化剂。在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旨在遏制乃至逆转苏联在第三世界优势地位的“里根主义”的确给苏联帝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但是苏联在这方面的困境也绝不是致命的问题。
作为一场可能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的前身,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确实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它绝不会给苏联带来军事上的失败,因为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地知道,太空防御在数十年内都不可能成为实际部署。
当然,苏联的解体有许多结构上的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但这些原因不能充分地解释苏联解体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在1985—1989年间,在经济、政治、人口和其他结构性状况没有出现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苏联的国家及其经济体制是如何突然被许多人视为可耻的、非法的和难以容忍而注定要失败的呢?
像现代的所有革命一样,最新的俄国革命始于“上层”迟疑的自由化,而且它的基本原则远远超出了调整经济或者改善国际环境的必要限度。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核心无疑是理想主义的:他想要建立一个更合乎道德的苏联。
在1987年1月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告诉中央委员会:“苏联正在形成新的道德氛围。”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宣布“公开性”和“民主化”是苏联社会改革的基础。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公开性的教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回忆说,1983年,他在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十年后回到苏联,感到人们发出如下吼声的时刻就要到了:“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一切必须采取新的方式。”
戈尔巴乔夫最初的自由化小圈子的另一位成员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也对无处不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行为感到痛心。据他回忆,1984—1985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说:“一切都烂掉了,必须改变。”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队似乎相信,正确的事情在政治上也是可控的。戈尔巴乔夫宣称,民主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改革的精髓”。许多年后,他对采访他的人说:“不仅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而且在文化层面上,苏联模式已经失败。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大多数受教育者、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上拒绝苏联模式,因为它不尊重人,反而从精神上和政治上压迫人。”
到1989年,改革带来了一场革命。这主要是因为另一个“理想主义的”原因: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暴力深恶痛绝,因而在变革的规模和深度开始超出他的本意时顽固地拒绝诉诸大规模的高压手段。认为即使是为了“维护制度”而采用斯大林主义的镇压措施也是对他信念的背叛。
亚历山大·鲍文是苏联著名的记者,后来成为“公开性”的热情先驱。他在1988年写道,在人民对腐败、无耻的盗窃、谎言和诚实劳动的障碍日益高涨的“怒火”中,改革的理想“成熟了”。另一个见证者回忆说,对于“实质性变革”的期待四处蔓延,由此形成了一群规模可观的激进改革的支持者。突然之间,观念本身变成了革命发展中一个结构性的物质因素。
用雅科夫列夫的话说,官方的意识形态“像钢箍一样”将整个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结合在一起。现在,它的公信力正在迅速减弱,新的认知推动了对待政权态度的变化和“价值观的转变”。逐渐地,政治制度安排的合法性开始遭到怀疑。罗伯特·K.莫顿不朽的“托马斯定理”认为,“如果人们把一些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其结果这些情境就会成为真实的”。在人们对苏联政权表现的看法和评价发生了根本改变以后,也正是因为这种看法和评价的根本改变,苏联经济的实际恶化才作为结果产生了。这成为“托马斯定理”的又一例证。
在1987年写给苏联某杂志的信中,一位俄罗斯读者把他自己周围的情况称为“意识的彻底决裂”。我们知道,他是对的,因为俄罗斯的革命是第一次几乎由民意测验从一开始就勾画出其进程的大革命。就在1989年底,第一次有代表性的全国舆论调查发现,在四代人经历了一党专制之后,实行竞争性选举和让苏联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合法化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到1990年中期,俄罗斯地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政府允许个人自由行动”,“健康的经济”就更有可能实现。6个月后,一次全俄罗斯民意调查发现,56%的人支持迅速或者逐渐转型为市场经济。第二年,支持市场经济的受访者比例增加到64%。
那些灌输这种明显的“意识决裂”的人与那些引发现代其他经典革命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是作家、记者、艺术家。正如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人“帮助制造了那种普遍的不满意识、那种一致的公共舆论……从而制造了对革命变革的实际要求”。
苏联的状况就是如此。报刊亭前排着的长队——有时候早晨六点街道上就挤满了买报纸的人群,每天的报纸经常在两小时内销售一空,以及主要的自由派报纸和杂志订阅量急剧飙升,证明了大多数著名的“公开性”作家或者萨缪尔·约翰逊口中的“真理的导师”所具有的惊人力量。
对他们来说,道德的复兴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不仅要全面改造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推翻现有的社会规范,而且要实行个体层面的革命,改变俄罗斯国民的个性,正如1987年米哈伊尔·安东诺夫在《十月》杂志上发表的《我们究竟怎么了?》这篇开创性的文章中所宣称的那样,必须把人民从“他们自身中,从那些扼杀人类最高贵品质的道德败坏过程的恶果中”,而不是从外部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如何拯救呢?通过使新生的自由化成为不可逆转——不是赫鲁晓夫的短命的“解冻”,而是气候的根本变化。那什么能够保证这种不可逆转的过程呢?首先是“对精神奴役的重现具有免疫力”。《星火》周刊是宣扬公开性的主要出版物,它在1989年2月写道:只有“不论以何人或何种名义都不会成为警察眼线、不会背叛、不会撒谎的人,才能使我们摆脱极权主义国家的再次降临”。
这种推理具有循环论证的性质,要拯救人民,必须拯救改革,但是要拯救改革,改革必须能够改变人的“内心”。那些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人似乎认为,通过改革拯救国家与把人民从精神困境中解救出来是紧密或许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在深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原因后,托克维尔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与以前的政权相比,革命所推翻的政权往往并不具有那么大的压制性。为什么?托克维尔推测说,这是因为尽管人民“可能遭受更少的苦难”,但是他们“却更加敏感了”。像往常一样,托克维尔深入研究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从美国的“国父们”到雅各宾派和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在本质上相同的旗帜下战斗:提高人的尊严。恰恰是在通过自由和公民权利来寻找尊严的过程中,“公开性”的颠覆意识才得以存在,而且将会继续存在下去。就像《星火》和《莫斯科新闻》必定会对它所发表的文章能与“站在坦克上的鲍里斯·叶利钦”照片并列成为最新俄罗斯革命的象征感到自豪一样。
当然,强烈的道德冲动、对真与善的追求是国家成功改造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它或许足以推翻旧制度,但无法一下子克服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的国家政治文化。建立在道德革命之上的民主制度,无法在一个缺乏宝贵的基层自我组织和自治传统的社会中维持正常运作的民主。就像俄罗斯的情况一样。70年的极权主义造成了国内的分化和不信任,使俄罗斯的道德复兴困难重重。尽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摧毁了一个帝国,但数百万俄罗斯人的帝国式思维遗产使他们容易接受新威权主义的普京主义。普京主义的宣传主题是“敌对势力的包围”和“俄罗斯人站起来了”。此外,斯大林主义给国家造成的巨大悲剧从来没有得到充分正视,也没有得到补偿,正在腐蚀整个道德事业,就像“公开性”的宣扬者所热情告诫的那样。
这就是今天的俄罗斯再一次慢慢走向新的改革时刻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改革和今天的石油价格为数百万俄罗斯人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但是统治精英厚颜无耻的腐败、新式的审查制度和对民意的公开鄙视引发了公众的疏离感和犬儒主义,其程度开始接近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
2011年2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领导的自由派智库现代发展研究所发表了一份像是2012年总统竞选纲领的报告。报告中说:“过去,俄罗斯需要自由以便生活得更好;如今为了生存而必须拥有自由……我们的时代面临的挑战是全面审视价值体系和塑造新的思想意识。我们不可能用旧思维建立一个新国家……国家能够对人作出的最好投资是自由和法治以及对人的尊严的尊重。”
正是这种对自尊和自豪的相同的思想和道德追求——始于对国家过去和现在的无情的道德审视,在短短几年内掏空了强大的苏联国家,剥夺了它的合法性,使之烧成了空壳,最终在1991年8月轰然倒下。这种思想和道德之旅的传奇绝对是20世纪最后一场大革命的核心内容。
译者单位: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