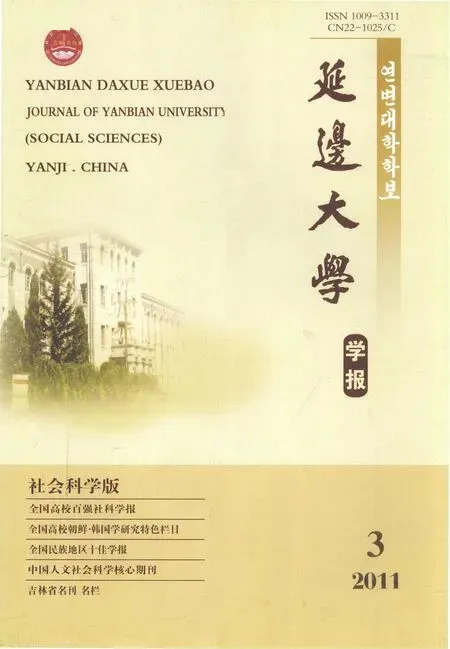国际人权领域悖论的宪政解读——以美国为例
吴 展
(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相比较国内保护而言,人权的国际保护是较为晚近的经验,在此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人权法因而是国际法中较为年轻的部门法之一。[1]尽管形成的时间很短,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却很迅速。在国际人权法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权标准和规范不断丰富,国际人权法的权利体系藉此不断扩张,人权监督制度亦不断完善。与国际人权法发展相一致的是,国际人权法对世界各国国内人权保护机制及实践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相关国家融入国际人权机制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并因此产生如何履行国际人权法相关规范的国家义务问题。①从理论上讲,签署和批准国际人权法律规范的联合国各成员国负有将相关人权保障规范和精神纳入国内人权保护机制的义务。但在实践当中,不仅签署和批准联合国国际人权法律规范的普通成员国,即使那些主导国际人权法律规范制定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也存在着在国际人权实践领域利用国际人权规范为借口压制乃至侵略别国而自身在相关国际人权法律规范的国内适用方面却存在模糊甚至抵制其国内适用的做法,从而被国际社会指责为在人权保护方面奉行“双重标准”。本文选择美国在上述国际人权实践领域的悖论表现进行一种宪法学的解读,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国际人权法律规范与其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为审慎地构建国际人权法律的国内保护机制提供若干借鉴。
一、美国在国际人权多边条约制度方面的悖论表现
美国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并未在国际人权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其只是对国际条约的一般地位进行了界定。根据美国宪法,美国对国际性规范的一般承诺方式是正式加入该条约或公约。美国总统获得出席参议院会议2/3参议员的批准,拥有经咨询参议院并取得其同意而缔结条约的权力。除此之外,美国宪法第二章第六条对总统的这项权力进行了拓展。该条规定,依据宪法以及与其相一致的法令的权力而缔结的条约,都是合众国的最高法律。②概言之,这可以视为美国宪法对多边条约制度地位的文本确认。以根本法宪法的形式对国际条约与公约的地位予以明确,可见美国对相关国际性规范存在较强的制定法认同。然而,制定法认同是一回事,其认同能否落实则是另外一回事,在上述国际条约的具体适用方面,美国却存在着广泛的限制。其中,最有力的限制来自国际条约非自动执行说。[2]根据非自动执行学说,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效力需经另外的立法或行政行为认可方可产生。在司法方面,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在此方面没有任何案例,州和联邦法院还是遵从了Sei Fujii v.State案③的先例,该案认为联合国制定的人权公约不具有自动执行性。实际上Sei Fujii v.State案的判决是美国对待国际人权条约态度的客观表现,在美国人看来,“美国只接受成为美国法律的规定”,④美国法院当然不能执行美国没有批准的条约,或者美国通过“保留,谅解和声明”加以弱化的人权条约内容。在美国宪政史上,如同上述认识一样,为了美国公民而执行美国之外的权利规范这一观念一直受到美国人的有力抵制。在国际人权领域,美国是参加废除人权奴役制度国际运动的最后几个国家之一,甚至在较晚建立国际联盟时期,美国总统威尔逊还抵制了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建议在国际联盟章程中加入主张种族平等权利条款的努力。因此,在上述时期,国际法的调整范围还局限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是其核心,而美国人对待国际人权条约的态度则是抵制适用的。
二战期间,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利用国家机器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对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意识到应当对这种极权主义进行负有责任的回应。1942年1月1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苏联、英国、中国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根据此前美、苏、英联合起草的一份有关战争宗旨和原则的文件草案,上述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首次将保障国际人权的宗旨宣布为反法西斯国家的共同纲领。宣言在赞同“大西洋宪章所载宗旨与原则”的同时,进一步表示:各国深信战胜他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卫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同时,他们正力图同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然而,1944年年末,当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⑤在旦巴顿橡树区(Dumbarton Oaks)开会,就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取代国际联盟而进行宪章方面的谈判时,西方国家对人权的热情已经消退。彼时美国参议院已经决定,美国在任何类似国际组织中的成员权应建立在强大的国内司法权条款之上,相应历史时期制定的国际人权规范显然无法回避美国的上述理念。果然,相比美国、苏联和英国的原意而言,1945年由44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宪章对人权进行了较多的论述。尽管联合国宪章此时已经确立了人权规范的突出地位,但因国家主权和国内司法权等因素,相关规范并未获得真正实施。在此背景下,1948年12月产生的《世界人权宣言》成为一部没有约束力的公约。⑥从总体上讲,二战以来的几十年间,虽然美国基于其国际人权理念远离联合国人权条约,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一起构成了国际人权法案,初步完成了国际人权法律体系的构建。但是,从上述国际人权规范制定的过程来看,美国并没有在其中发挥多大的作用。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国内外政治因素的综合作用,美国开始全面抵制国际人权公约。当然,对国际人权公约的抵制并不代表美国放弃了自己的国际人权理念。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案,这些法案均要求美国进行军事和金融援助必须以其他国家持续性地遵守人权规范为条件。但是,当美国国内或国际上的非政府人权组织监督美国遵守人权规范的状况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却通常是强烈的。
因此,尽管美国自身对国际人权法在其本国的适用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但在以国际人权法为由干涉他国内政方面却是不遗余力。诚如美国学者德累斯科尔所言:“在过去,属于内政管辖的最神圣不可侵犯事项之一,就是国家给予国民的待遇”,⑦但借助国际人权法来制造人权的国际保护,便可把原属于一国内政管辖的事项转换成可干涉的了。换言之,接受一个国家控诉另一个国家侵犯人权,为某些强势国家如美国攻击与其不友好乃至敌对的国家制造了一个国际法层面的借口,尽管其自身回避甚至抵制国际人权法的国内适用。
二、美国在国际人权习惯法制度方面的悖论表现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国际习惯法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接受为法律者”。[3]依照上述规定,国际习惯法的形成,需要同时具备两个要素:其一是通例的形成,称为“物质要素”;其二是该通例被各国接受为法律,称为“心理要素”。[4]就美国而言,国际习惯法是其参加国际人权制度的替代机制,即替代多边条约制度的一种方式。美国宪法对于作为多边条约制度替代方式的国际习惯法,并未像对待条约那样对其国内地位加以明确规定。美国宪法文本中仅有一处提及国际习惯法,即宪法第1条第8节第10款规定,美国国会有权“界定和惩罚……违反万国法的罪行”,此处的“万国法”即是美国制定宪法时对国际习惯法的通常称谓。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美国宪法文本上的缺失,才使得人们对国际习惯法在美国国内法的地位产生各种歧义性的认识。概而言之,美国理论界对国际习惯法的国内法地位存在三种观点:现代主义、修正主义及折中观点。持现代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国际习惯法同样涉及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因而构成联邦普通法。[5]与现代主义相反,持修正主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习惯法作为联邦普通法予以适用与美国相关司法政策不符。在实践中,美国国会仅将少数经过精选的国际习惯法原则纳入联邦立法。在现代主义观点援用最多的人权领域,美国当局在批准相关人权公约时,多做出足够多的保留和限制,这充分表明美国立法机构并不想使国际人权法律规范成为国内法院诉讼的基础。[6]折中主义观点为少数学者持有,他们认为,在司法领域,联邦法院可以将国际习惯法视做一种既不是州法律也不是具有优先地位的联邦法律,因而可以作为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判决规则,但并不优先于州法,也非联邦法院管辖权的基础。[7]
与制定法的缺失以及相关理论方面的分歧相一致,美国人权保护在司法实践层面始终对国际习惯法缺乏统一性的结论,且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存在着实践与文本脱节的悖论表现。早在1900年,美国最高法院就通过Paquete Habana案⑧确立,国际习惯法是美国法律的一部分,关于国际习惯法的权利问题按期呈交给法院的适当机构予以裁决时,该机构必须予以查明并管辖该案。在国际习惯法国内裁判的直接适用方面,这是一种有力的确认,它似乎授权联邦法院:“为了这一目的,一旦不存在条约,支配性的行政或者立法性法律或决策,必须向文明民族的风俗习惯寻求帮助;并且,这些风俗习惯见诸于法学家和评论者的作品……借助于这些作品,司法裁判机构不是要探究作者关注的法律应当是什么,而是确信实际上的法律是什么”。[8]法院不时也有其他一些类似的陈述,第二巡回法院的厄尔文考夫曼法官参考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一些国际机制,最终遵照了Paquete Habana案⑨的做法,即国际习惯法的进化原则,宣布可对人权的侵犯行为进行制裁。
在美国的具体司法实践当中,确有迹象显示联邦法院正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外国的司法观点,但据此认为美国法院广泛接受外国的法律或习惯则显然是错误的。在对 Knight v.Florida案⑩的复审意见中,布雷耶法官引征了外国法院在特定死刑案例中说服性权威的做法。在布雷耶看来,外国法院在几乎相同的条件下适用与美国几近相同的宪法标准,最高法院认为这两者之间具有相关性,并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因此,布雷耶认为,类似的观点虽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却在司法实践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与布雷耶法官类似,其他一些法官间或也在具体的司法判决中引征外国的司法观点作为支持。对这种倾向,伦奎斯特大法官及斯卡里法官都持反对态度。比如,斯卡里法官就认为,“我们必须永远牢记,我们是在解释美国宪法……如果不在我们自己的人民之间达成一致,其他国家的观点,无论法院认为它们如何能够启发法官,都不能将之通过宪法适用于美国人民”。⑪由此看来,在国际习惯法制度方面,认为司法分支可能更开放地通过分析国际习惯法而考虑外国价值的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却强烈反对在人权领域引征外国法律乃至习惯法。
三、美国在两种国际人权制度下悖论表现的宪政根源
事实上,美国在上述国际人权制度方面存在的悖论表现,是其所继承的一项20世纪的主要遗产。除了一般的国际、国内政治分析之外,我们必须转而探寻美国宪法及宪政方面所暗含的假设和传统渊源,以便对其正确认识。尽管国际、国内政治因素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美国之所以继续拒绝参加国际人权体制的主要原因仍然不是其外交隔离主义,不是美国人的排外或国际警察式的目中无人,而是其坚固的宪法根基。换言之,美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悖论表现实质上是一种宪政悖论。
其一,这种宪政悖论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强烈的文本主义宪法传统。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成文宪法,美国宪法已经走过了两个多世纪,但它的宪法文本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考虑到上述原因,美国历史学家艾里克霍布斯邦姆将“美国公共制度拒绝变迁的直接抵抗力量”⑫归因于美国的宪法文本传统。艾里克霍布斯邦姆认为,与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相比,美国陷于律师运行了两个世纪的1787年宪法的约束之中,其各种宪法制度长期以来处于裹足不前状态。此外,在宪法实施层面,美国不仅承诺遵循一部简单且具有暗含意义的文本,而且主要将其提交给司法系统对该文本进行解释,这样一种局限于文本主义的解释在诸多方面造成了实质上的阻碍。美国学者麦考利认为,美国宪法“只有帆,没有锚”。[9]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当宪法变迁产生遗传性的政治回应时,美国的宪法文本主义实际上起到了阻止革新的“锚”产生的作用。文本主义促使人们提出疑问,有时甚至挑战一些在美国人看来可能非常容易接受的革新。与理性相比,文本主义传统是本能性的,这使它不能接受既不植根于宪法文本,又不能从生活传统中发现的思想或习惯。因此,对于纳入那些国际人权制度中没有美国国内法律基础和生活经验的相关理念和制度而言,强烈的文本主义宪法传统实际上形成了一道非常强的制度障碍。
其二,这种宪政悖论产生的原因是美国宪政与人民主权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宪政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建构国家的实验。诚如哈耶克所言:“美国在宪政方面的尝试成绩斐然,而且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成文宪法的存续有它的一半时间长;但是,就它作为一种安排政府制度的新方法而言,它依旧还只是一项实验”。[10]在这种实验进路之下,美国宪法的制定并不像世界上某些国家所预订的那样,在承认人民权利至高无上的同时认为人民的理性永远正确。美国制宪者既不相信人民永远正确,尽管人民的同意是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源泉,也不认为统治者是圣人,尽管美国显然是精英治国。美国在承认人民主权的同时,坚信人民和国家的统治者可能因为人类一时的心智蒙蔽而背离长远和准确的目标。这就需要在保证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加强对各种人民权利可能的侵犯进行防范。正是在这种对人性的基本假定的基础上,制宪者才审慎地制定了1787年的宪法,创立了一套新的、操作性很强的宪政原则并付诸实施,这种制度既是对欧洲,尤其是英国宪政思想和实践的创造性的继承和发挥,⑬更是美国人基于自身历史经验的一种创新。从其结果来看,上述原则和实践构成了美国独具特色的宪政。该宪政机制为公民权利和自由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为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不仅为美国在过去200年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乃至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发展。[11]从表面上看,美国人民确有理由为其创设宪政制度而自豪。但是,在美国现代历史上,宪法的制定者多为有产者或精英,而普通人民实际上未曾参与正式制定宪法。美国人民基于人民主权和宪法有效性而建立的创造性的联邦主义观念,使得他们很难确认那些几乎是最令人敬仰的外国宪法制度和规范以宪法合法性。
其三,这种宪政悖论产生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美国所酷爱的权利传统。在美国人看来,政府、宪政的目的在于保护天赋的人权。例如,路易斯·亨金就认为“权利先于宪法,先于社会和政府而存在。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们原则上在有任何形式的政府之前就享有的权利;这些权利乃是造物主的赐予物”。[9]在这种权利传统的作用下,无论是独立宣言,还是美国宪法,都对天赋人权的保障进行了较多的规范。但是,通过对美国国际人权领域悖论表现的宪法解读,我们不难发现:在国际人权方面,美国的权利传统使它侧重于关注公民和政治权利,它对社会,特别是经济权利,却鲜有注意。在某种意义上,从宪法的角度观察,我们可以说宪法版本的冷战就是公民和政治权利与社会和经济权利之间的冲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张,如果市场基础上的民主国家保证政治和公民权利的话,那么它们将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从国家繁荣当中受益。但是,非西方国家则大多认为,只有在国家保障诸如工作、房屋和健康此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建立一个体面的国家。在美国人看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仍然与苏联的权利立场一样危险。这本质上是美国人权实践自我优越性的表现——美国人始终坚信:美国所执行的法律规范比同类的国际人权规范更为有力。在这种观念下,美国人倾向于确信,美国人对权利的历史概念是唯一有效的认识,或者至少它是实现宪法权利的最好进路。
四、国际人权领域悖论对我国相关问题的若干启示
尽管美国从其自身的宪政传统出发,在国际人权立法领域某些时期处于主导地位,但国际人权立法仍然是一项国际性的事业,美国以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相关领域亦多有作为。一直以来,我国在国际人权立法领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过程中,我国力促将人权内容纳入其中,并在国际人权保障机制的构建方面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1981年,我国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国;2006年,我国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此外,在国际人权立法层面,我国“参加了24个国际人权公约,认真履行保护人权的国家义务,为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2]同时,我国不仅在国际人权机制建设和规范创设层面积极参加并在表达符合自身利益的同时回应国际人权发展趋势的国际人权利益诉求,而且还在国内法层面积极适用国际人权立法。
在国际人权立法的国内适用方面,我国一般是采用积极转化和消极转化两种方式。[13]积极转化意指通过在我国法律中增加或者修改某些规定的方式将人权公约中的条款转化为我国国内法,而消极转化方式则是指当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有关条款相一致,就意味着该国际人权条约在国内得到了适用。在以上两种方式的运用之下,我国通过大量制定、修改和废止国内法律,将我国签署或批准的国际人权条约、公约予以国内适用,使得国际人权机制与我国国内人权保护机制进行良好互动,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然而,考虑到国际人权机制本身尚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在此领域也存在一定的悖论表现,我国在型构完善的国际人权国内保护机制方面,仍有一些有待改进之处。
在国际人权立法的国内适用机制方面,我国应当关注宪法的作用。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法,既是一国国家治理机构设置的政治蓝图,也是人权保障的根本文件。通过宪法对国际人权立法及其国内适用问题进行明确,有利于提升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法律地位。在国际人权立法的国内适用领域,我国应当在我国宪法和基本法律之中对我国业已参加的国际人权立法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以上内容是国际领域的广泛做法。但对于一般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国内适用问题,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就目前而言,相应的规范只是在一些法律的具体实施层面提及上述法律与国际条约冲突时的解决机制,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目前,我国已然初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国所参加的包括国际人权立法在内的国际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如何,其在国内的适用机制怎样安排?凡此种种问题,都应当在这一法律体系当中通过适当的规范形式予以明确。
当然,除了通过正式的制定法程序对有关问题予以明确,建构具体的国内人权规范以便适用国际人权立法之外,还应当在适用过程中注重发挥法律解释机制的作用。美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悖论显示,为了维护和最大程度地保障本国人权,应当具备特定的国内机制对相关国际人权立法作出灵活应对。在人权领域,中国与美国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国家利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和对立,人权理念和观念层面显然存在着深刻的可能分歧。[14]因此,考虑到国际人权等领域复杂、多变的态势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化演变特性,我国理应借鉴适当的法律解释机制予以正确应对。在国际人权立法的国内适用方面,法律解释作为立法方式之一,可由国家有权机关运作。其内在机理在于:在有关国际人权立法国内化方面,可由特定的国家立法机关对国内相关人权立法事先或事后进行一定的解释工作。在此方面,法律解释的功能在于它有助于我国应对国际人权立法自身的复杂变局,为妥善应对相关国际人权立法的型构提供一定的转圜空间。同时,法律解释权力的设置也助益于我国在波诡云谑的国际人权领域保持较大程度的自主性和适应性,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我国国家利益。
此外,从国际人权立法国内适用的角度来看,很有必要加强法院的人权保障功能。从国际人权范围来看,注重法院在人权保障方面的重要作用是晚近国际人权立法发展的一大特点。[1]比如,1998年11月1日生效的欧洲人权公约第11号议定书,就在欧洲人权保护体制内确立了单一的欧洲人权法院体系,以取代以前的政治、准司法和司法方法的混合体制,赋予法院对个人申诉的独断的强制管辖权。对于我国而言,相关宪法修正案业已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文本,这使得人权的保护获得了根本法的文本确认。但从具体的人权保障机制的构建来看,在人权保障的国际人权语境下,我国除了通过国际平台参与国际人权立法过程,在国内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保障人权之外,也很有必要加强司法在人权保障方面的独特功能。
注释:
①实际上,较好地履行国际人权法规范的国际义务也是国家融入国际人权机制的必要条件。一国一旦决定加入某项国际人权规范,就有义务将人权保护机制所设定的各项实体权利予以实施。参见焦世新的《中国融入国际人权两公约的进程与美国的因素》一文,《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133-138页。
②该条规定,“本宪法及依本宪法所制定之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的授权已经缔结及将要缔结的一切条约,应成为全国的最高法律;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其约束,不管任何州宪法或法律中有任何相反的规定”。
③242P.2d 617(Cal.1952)。
④U.N.Doc.A/50/40,para.279。
⑤与苏、美、英不同,此时作为即将成立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国际性组织及其制定的条约对人权的保障作用。比如,我国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以及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上述国际会议,对人权在联合国宪章中突出地位的确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参见黄进、邹国勇的《董必武国际法思想初探》,《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9页。
⑥由于当时联合国成员国之间人权理念不同,一些主要大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亦存在竞争,《世界人权宣言》尽管出台了,但对联合国成员国而言却缺失法律上的拘束力。虽然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世界人权宣言》作为一项国际公约,向世人宣示其目的在于为所有国家和人民确定人权领域的共同标准并促使其得以实现。通过这一过程促进全人类之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守,从而促成并发展各国间友好关系以维护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同时,《世界人权宣言》也借助29个条文对国际人权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明确确定。参见《世界人权宣言》,http://www.un.org/chinese/work/rights/rights.htm2010年6月25日访问。
⑦见[加]约翰·汉弗莱的《国际人权法》,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92年,第216页。
⑧175U.S.677(1900)。
⑨175U.S.677(1900)。
⑩528U.S.990(1999)(Breyer,J.,dissenting)。
⑪487U.S.815,868-69n.4(1988)。
⑫作为设计基本公共制度的宪法,其作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依据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发挥着相关制度进行变革的阻力的实际效用。参见 Eric Hobsbawm,Only in A merica,Chron.Of Higher Educ.,2003,at B9。
⑬美国人作为英国宪法思想的实施者,创造性设计了不同于英国议会至上的三权分立体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参见 Jeffrey Goldsworthy,The Sovereignty of Parliament:History and Philoso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04-215。
[1] 万鄂湘,毛俊响.冷战后时代国际人权法的新发展及其对现代国际法的影响[J].法学评论,2009,(3):58-63,58-63.
[2] 李浩培.条约法概论[Z].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387.
[3] 王铁崖,田如萱编.国际法资料选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985.
[4] 梁西主编.国际法(修订第二版)[Z].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45-46.
[5] Louis Henkin.International Law as Law in the Unitea States[J].Michigan Law Review,1984,Vol.82,pp.1561.
[6] Curtis A.Braaley&Jack L.G olasmith.The Current Il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itigation[J].Foraham Law Review,1997,Vol.66,pp.319-368.
[7] T.Alexanaer Aleinikoff.International Law,Sovereignty,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Reflections on the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Debate[J].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04,98(1):91-108.
[8] Robert J.Martineau,Jr.,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i: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Z].5Hum.Rts.Q.87,96(1983).
[9] [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159,10.
[10] [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 ,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242.
[11] 王希.活着的宪法[J].读书,2000,(1):48-54.
[12] 宋方青,傅振中.论国际人权立法的中国化——以民主权为中心[J].现代法学,2009,(5):131-138.
[13] [丹]莫尔顿·克耶诺姆.国际人权标准在丹麦的适用[A].刘海年,等,中国-丹麦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学术研讨会文集[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74.
[14] 杨和平.20世纪中美关系与国际法[M].成都:巴蜀书社,2002.188-193.
——来自广西金秀的田野考察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