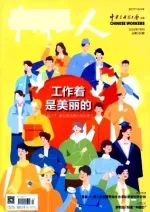给多少钱春节不回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爱玉
给多少钱春节不回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爱玉
一、问题的提出
据中新网1月13日的综合报道,1月19日春运大幕正式拉开,至2月27日结束,共计40天。春运期间,全国将有28.5亿人次通过铁路、公路等交通工具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其中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将突破历史记录,达到2.3亿人次,同比增加2554万人次,增长12.5%。由此来看,今年春运期间一票难求的现象仍会延续。
从最近几年春运的情况看,大规模返乡过年最主要的群体是农民工。按照2006年1月 18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的界定,“农民工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人员”。农民工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家乡附近乡镇企业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打工的农民工,也称"流动民工"。据估计,这一类别人口占全部农村人口的16%~18%。2009年时,两类农民工的数量为22542万人,其中外出务工人员为14533万人,占城镇人口的23.4%。广东是全国农民工会聚的第一大省,据统计,截至2009年上半年,全省流动就业半年以上的新生代产业工人达2600多万,约占全国的1/5,其中外省劳动力1900万人,约占全国跨省流动就业总数的1/3。从地区分布来看,86%以上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其中深圳800万,东莞700万,广州300万。可见,广东省农民工的春运之路,便是中国农民工的春运之路。
本文以2010年11月初至12月底在广东省五个城市171个企业中的2679个外省籍新生代产业工人的问卷调查资料为依据,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生代产业工人的春节返乡意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试图将其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相结合,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给多少补助愿意留在城里过年?
问卷调查设计了如下问题:“要过年时,假如您能顺利买到回乡的车票,给多少补助您愿意留在城里过年?”在4507名被调查者中,有2679名广东省之外籍贯的人给出了有效信息,其对问题回答的情况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给多少钱都不愿意,共155人,约占有效样本的6%,第二类,即使不给补助,也可以留在城里过年,共244人,约占有效样本的9%,第三类,给适当的补助,可以留在城里过年,约占有效样本的85%。
1.给多少钱都不愿意留在城里过年
什么样的人“给多少钱都不愿意留在城里过”呢?
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占37%,女性占63%,表现出以女性为主的特点。
从文化程度上看,普通高中、中专或其它技校高职类占43%,初中类占30%,大专及以上类占25%。与样本总体的文化程度结构比较,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选择一定要回家过年的比总体样本比例高出了8%。
从目前职位上看,普通工人占42%,文职人员占36%,技术工人占15%,基层管理人员占7%,与样本总体的职位结构比较,文职人员与普通工人选择一定要回家过年者的比例更高。
从婚姻状况上看,已婚者占34%,未婚者占66%,离婚者占1%。那些结了婚、配偶也在外工作的,回乡过年的意志更为坚定。
从身份和出生年代上看,城镇工占21.3%,90后农民工占17.4%,80后农民工占52.9%,70后农民工占8.4%。相比于样本总体的身份和出生年龄结构,80后和90后农民工选择一定要回家过年的比例更高一些。
从籍贯上看,来自湖南、湖北、安徽的打工者选择一定回家过年者的比例相对较高。
2.即使不给补助,也可以留在城里过年
回答即使不给补助也可以留在城里过年的男性为103人,女性为121人,分别占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比例的8.8%和9.3%。
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中有119人表示即使一分钱不给,也可留在城里过年,占相应样本总体的12%;高中及以上文化者中有118人做了这样的选择,占相应样本总体的7.5%。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程度较低者此项选择的比例更高。
从目前职位上看,普通工人表示即使一分钱不给,也可留在城里过年的比例较高,而文职人员则相对较低。
不同婚姻状况者在此项选择上无显著性别差异。
从身份和出生年代上看,城镇工和90后农民工选择即使不给补助,也可留在城里过年的比例更高一些。
从籍贯上看,来自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的打工者选择此项的比例较低,而来自河南、四川、广西的打工者选择此项的比例相对较高。
3.给予适当补助就愿意在城里过年
85%的外省籍被调查者表示,如果给予适当补助,可以留在城里过年,其中0.8%的人表示给的钱越多越好,比如100万之类的,1.2%的人表示还没有想好要多少钱,其余83%希望适当补助的人,从补助金额看,49%在1000元以下,15.6%在1001~2000元之间,6.3%在2001~3000元之间,6.2%在3001~5000元之间,6%在5001~20000元之间,平均值为2828元,接近其上月平均收入的1.5倍,是月基本工资的2倍。
从性别上看,男性期望的补助金额是3000元,女性期望的补助金额是2190元。
从文化程度上看,呈现出两头高的特征,期望补助金额由高到低分别是:大专及以上者为4292元、小学及以下者为3506元、高中及相等文化程度者为2605元、初中文化程度者为1728元。
从婚姻状况上看,已婚者期望补助金额为2642元,未婚者期望补助金额为2575元。
从身份和出生年代上看,四类群体期望的补助金额分别为:城镇工2981元,90后农民工2135元,80后农民工2568元,70后农民工2293元。
从户籍所在地上看,来自贵州、江西、湖北、湖南的被调查者期望的补助金额相对较高,来自云南、安徽、陕西、广西的被调查者期望的补助金额相对较低,详见图1。

三、表象城市化下的农民工与“春运”
以上描述了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的各类群体对于春节回家过年的不同态度,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每年春节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现象?为什么对于有些人而言,即使给多少钱补助都不愿意在城里过年?为什么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当给予适当补偿的时候,就愿意留在城里过年?本文试图从农民工城市化的视角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按照官方的统计,截至到2009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218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为47.6%。美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870年的25%提高的1920年的51.2%,用时50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860年的20%左右到1950年的80%,用时90年;日本的城市化水平由1908年的18%提高到1970年的70%,用时62年;韩国的城市化水平由1944年的13%提高到1990年的74%,用时46年。四个国家的年均城市化率分别为0.48、0.67、0.84、1.32。对于作为人口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国来说,这样的城市化率是很快的。但是目前的城市化,是一种表象的城市化而非实质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远未如统计城镇人口比例所展示的那样高,主要原因是作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其目前的生存状态无法与作为城市化主体的市民相称。
表象的城市化表现为:(1)非常规就业农民工大多集中于脏、累、险、重、苦、差的非正规部门,工作无保障、不稳定、低收入、高强度,承受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待遇。作为非正规、不稳定、临时性劳动力的主体,他们在城市打工获得的工资,难以维持其在城市中长期劳动力的再生产(安家或者在城市中赡养父母、抚育后代),并积累出可以支持其在城市中生根的资本和技能。外省籍农民工的每天工作时间为9小时,平均每天加班的时间为2.2小时,基本工资为1255元,上个月的总收入为1928元。(2)家庭分离的居住形式。根据问卷调查,离开家乡外出打工的时间,90后农民工平均为2.5年,80后农民工平均为6.3年,70后农民工平均为9.7年,有18%的人在城镇打工的时间超过了10年,最长的达到了33年。可是,农民工因其农村户籍而被排除在城镇房屋计划之外,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形式,以家庭分离的集体性居住为主。调查发现,在90后农民工中,67%居住在工厂集体宿舍,31%居住在出租屋;在80后农民工中,47%居住在工厂集体宿舍,50%居住在出租屋;在70后农民工中,46%居住在工厂集体宿舍,48%居住在出租屋。家庭分离的居住方式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能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不能真正地认同城市,融入城市生活。此外还有诸如社会保障的有限性与不平等性、政治参与和利益代表不足、平等教育权缺失等问题。
可见,农民工未能经由城市化而变为真正的市民,是导致每年农民工春运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春运问题的讨论与农民工对于给多少补助愿意留在城里过年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因为无法获得市民身份,无法在城市拥有自己的居处,家庭分离的居住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低城市归属感和低城市融入感,迫使他们在春节的时候要返回家乡。问卷调查设计了两个量表,用于测量农民工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融入感。两个量表各由8个题项构成,用以测量社区归属感的8个问题分别为“我很喜欢现在生活的地方”、“我喜欢我生活的地方那种家庭式的友好环境”、“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很适合我”、“我认为自己现在生活的地方像家一样”、“这个生活区内提供了一些我喜欢的业余活动”、“我很难下决心离开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在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人们都很尊重我”、“我的邻居让我很放心”,最低分为8分,最高分为40分,平均值为20分。用以测量社区融入感的8个问题分别为“我能够在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获得我想要的”、“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很好地满足了我的需要”、“我感觉自己是属于这个生活区的”、“我感觉自己是这里的一分子”、“我能说出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都发生了什么事”、“在我住的地方,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我感觉自己与这个生活区是连在一起的”、“我与邻里相处得很
好”,最低分为8分,最高分为40分,平均值为20分。两个量表的信度系数分别为0.87和0.85,信度系数很高。总体而言,农民工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融入感都不高,其得分只是略高于平均水平而已,得分平均值分别为24.6和24.3分。相比较而言,归属感与融入感得分由低到高分别为90后农民工、80后农民工与70后农民工。表1是对三个农民工群体根据春节回家过年的不同态度而对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融入感的得分所作的比较。从表1可以看出,对于三代农民工而言,给多少补助都不愿意在城里过年者,其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融入感的得分都是最低的。详见表1。

表1 三代农民工的春节回家意愿与社区归属感、社区融入感
那些愿意获得适当补助而选择留在城里的农民工,也并不是因为其对城市有很高的归属与认同,而是因为他们收入低下,一年辛苦工作劳累后所留无几,因而会理性地算计自己的回家成本:相对于收入而言,火车票不仅贵而且很难买,往返交通费用开支大;人情往来多,花少了怕别人瞧不起,花大方点儿又招架不住,等等。因此他们愿意在获得适当补助的情况下留在城里过年。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所要求的补助也就是其月基本工资的2倍,月总收入的1.5倍而已。
四、结论与建议
农民工与学生一直是春运的主要对象,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民工跨省流动规模的扩大,春运的压力也是一年胜似一年。对于70后农民工来说,他们外出打工的时间平均而言达到了将近10年,80后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时间也有6年之多。他们中有的甚至在城市辗转打工达30余年,但他们依然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他们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农村还是他们的根之所在,城市只是一个谋生的地方。为了谋生,他们忍受骨肉分离、亲情相隔的家庭分离的居住形式和生活。为了亲情和归属,他们选择在春节期间回家看望父母儿女、拜访亲戚朋友。他们对于“给多少补助,就愿意留在城市过年”的回答,正是这种城市漂泊、无根化生活的写照,那些城市社区归属感和融入感得分最低者,绝大多数也正是那些即使给多少钱都不愿意留在城市过年的人,而那些愿意获得适当补助留在城里过年者,也并不是因为其对城市有很高的归属感,并不是真正融入了城市,而是因为一年的打工积蓄有限,回家过年的成本太高,因此愿意获得适当的补助而不回家。
如果我们希望在今后看到农民工不再成为春运期间令人关注的对象,不再希望因为这个庞大的群体春节期间希望回家过年而导致交通运输部门的焦头烂额,那么真正的出路唯有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民工的市民化,首先需要对农民工的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需要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对农民工的市民化予以高度重视,对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定位、路径安排等要有整体性的规划与布局,要将农民工看做是公民而不仅仅是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只有这样,农民工的市民化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出了问题需要寻求药方的应急性问题。其次,需要国家全面系统地改革现行的社会政策体系,而不仅仅是考虑改革户籍制度甚至取消户籍制度本身。全面系统的社会政策体系改革,首先是要开放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与公共服务,让户口成为仅仅是一种登记的凭证,而不是一种享受不同福利与公共服务的身份标志。第三,需要改革财政收入和分配体制,增加劳动报酬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劳动报酬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从1983年的57%,降至2005年的37%,2007年,这一数据是39.74%;而在过去的22年里,资本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利润挤占工资的现象突出,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农民工能否市民化,能否融入城市,取决于其能否获得足够的收入并支付城市生活费用的能力。第四,要推进教育制度和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特别是住房制度的改革,应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计划之中,解决其在城镇的居住问题。
栏目主持:纪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