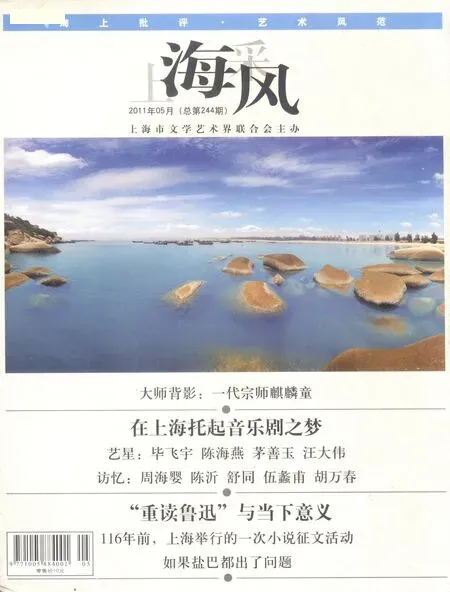当前中国文化的隐忧
文/余秋雨
当前中国文化的隐忧
文/余秋雨
余秋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艰难的文化》一文,其中阐述了对当前中国文化的隐忧——
第一个隐忧,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
最近几年,国内突然风行起复古主义,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这情景就像在一个居民社区里,我们正要劝说对街的邻居把播放交响乐的音响调得轻一点,没想到自己家里突然锣鼓喧天。
复古文化其实是从极“左”文化衍生出来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极“左”文化在今天只剩下了局部的标牌作用和回忆作用,因此不得不寻找新的精神立足点,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同样带有极端色彩的民族主义。它的文化替代物,就是复古主义。
其实,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要怀古,比中国更有资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们不创新,怎么能奢望在现代世界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我们国家也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但是很遗憾,打开电视、报纸、书刊,很少有一个创意思维引起广泛关注,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老戏重拍。本来,做一点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但在文化判断力不高的现代中国,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运动,传播热点是一种心理召唤,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几年下来,广大民众心中增添了很多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创新的敏感度,这不是好事。
复古文化在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对话和交融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
让人警惕的是,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东方智慧”、“制胜良策”。相反,复古文化从来不去揭示中华大地上千家万户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已伤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质,伤害到了后代的人格建设,也伤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股复古思潮甚至对近百年来发生的某些社会文化现象也进行过度夸耀。例如在我生活时间较长的上海,一些人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乐门”的滥情描述,对于当时还处于起步状态的学人、艺人的极度吹捧,就完全违背了基本常识,贬损了一个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仅是上海,这些年各地已经把很多处于生存竞争过程中的民间艺术、地方戏曲,全都不分优劣地当作“国家遗产”保护了起来,把它们称作“国粹”、“省粹”、“市粹”,顺便,还把老一代民间艺人一律封为不可超越的“艺术泰斗”、“文化经典”。这在文化史上闹了大笑话,还阻断了民间艺术新陈代谢的自然选择过程,反而恶化了文化生态。
由于很多文化官员对于文化发展的大势缺少思考,这股失控的复古势头也获得了不少行政支持。结果,当过去的文化现象在官方的帮助下被越吹越大,创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
第二个隐忧,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
康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这句话的关键词,除了“公共空间”就是“运用理性”。但这些年来,理性文化还没有来得及被广泛运用,却受到民粹文化的严重冲击。民粹和复古一样,都是在一个失落精神信仰的时代所设定的虚假信仰。任何虚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骗。照理,每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应该重视民众的呼声,但是,这种重视必须通过真正民主的原则和程序来实现。如果没有民主,民粹就会以冒牌的方式火速蔓延。现在民粹文化所推行的典型逻辑,是把网上发言看成民意,又把民意看成是最高原则。其实按照正常理性,我们必须承认世上许多重大课题,一般民众是感受不到,也思考不了的。例如,在我的记忆中,如果三十年前拿着“要不要改革开放”的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肯定很难通过,因为这牵涉到很多“铁饭碗”保不住,而一般民众又无法预计中国后来的发展。又如,现在如拿“低碳”、“减排”、“禁猎”、“限牧”、“休渔”等等问题交付民意裁决,情况也很不乐观。
如果“民意”就是最高原则,那么,人类为什么还需要那些苦苦寻求真理的文化大师,而且他们都那么孤独?孔子流浪十几年,一路上没有什么人听他的,除了身边几个学生;老子连一个学生也没有,单身出关,不知所终。如果让当时的民众来评判,他们这些默默赶路的人什么也不是。民众追捧的,是另一类人物。
前不久先后见到三位从欧洲回来的学者,他们分别向我说了差不多的话:“中国确实需要大力推进政治民主,但希望不要借着对网上言论的过度重视来取代民主。过度重视,也损害了那些发言者。因为他们本来有轻松发言的自由,一加重,也就立即变得不自由了,只能表演民粹主义。 ”
民粹很像民主,却绝对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不民主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专制让人向往民主,民粹让人误解民主。民粹主义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低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作第一坐标。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美学都告诉我们: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本是历代大师辛勤架设的提升人们生命品质的阶梯,民粹主义拆掉了所有的阶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闹。当然,嬉闹也可以被允许,但是应该明白,即使普通民众,也有权利寻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权利享受高出于自己的审美等级。这就像在学校上课,本来最受学生尊敬的一定是等级很高而又训导有方的教师,但是民粹主义驱赶了教师,只让最低年级的学生来编写课本。
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
第三个隐忧,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
现在经常有人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却为什么迟迟不能出现真正被海内外公认的文化成就? ”我想,答案一定与文化的耗损机制有关。
今天中国的“文化耗损”,主要耗损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尽管现在上上下下都看到了这种体制对文化创造没有帮助,在提倡文化体制改革,但是不少行政官员舍不得丢弃可控的排场,不少从业人员舍不得丢弃实际的利益,结果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仍在体制之内,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却在体制之外。
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某些官方协会中。它们一定也做过不少好事,当然还可以继续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里边。但是现在应该尽早厘清它们的真实性质,免使它们继续受到不必要的指责。它们实质上是一种传统的行业工会,没有太多权力;它们与体制外的大量同行也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又没有太多代表性。它们可能给部分人员一些“名片身份”,却无法面对文化创作上的任何问题。
其实目前处于文化创造第一线的,是远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他们天天遇到的障碍、挑战、挣扎、乐趣,是某些官方协会无法想象的。这中间的差异,就像“野战军”和“军人俱乐部”之间的天壤之别。现在的体制似乎把“军人俱乐部”里的活动当作了战场,错把大量的国家文化资源和荣誉资源都给了他们。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却风沙扑面,蛇蝎处处,缺少支援。
近两年,很多地方都在为缺少文化人才而着急,准备放宽政策、重奖重赏、多方引进。其实,在我看来,只要阻止了“文化耗损”,文化人才就成批地站在眼前了。真正杰出的文化人才数量有限,居无定所,永远在寻找着能够守护文化等级和文化安全的地方。
讲了当前中国文化遇到的三个隐忧,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少烦恼。这些问题发作的程度已经不轻,什么时候能够缓释?什么时候能够解决?
对此我想做一个让大家宽心的判断。我认为,复古文化的热潮现在已经越过了峰尖,开始降温。原因是人们已经发觉那些老句子、老故事、老谋略对于当代生活帮助并不大,产生了厌倦。更重要的是,复古文化遇到了一个正在逐步走近的强大对手,那就是各地都在兴起的文化创意产业。这些文化创意产业中还会有不少古代的阴暗内容,但是由于本质是创意,事情可以稍稍乐观。
同样开始引起人们厌倦的,是那种“文化耗损”机制。那么多争权夺位的协会,那么多假大空的晚会,那么多早已失去公信的评奖,那么多近似于“楼堂馆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大刀阔斧地收拾一下呢?不少官员也看出了其中的虚耗成分,但觉得反正有钱,用文化做点“面子工程”也未尝不可。但是,事实证明,这种“文化耗损”越热闹,真的文化创造就越难产。这个毛病的克服,好像与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关,因此急不得。
我最为焦虑的,是民粹文化的泛滥。我已经一再警告,这里埋藏着一场超过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的巨大人文灾难。但是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能够有效抑制它的观念和方略。反而,天天看到上上下下对它的畏怯、喂食和娇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