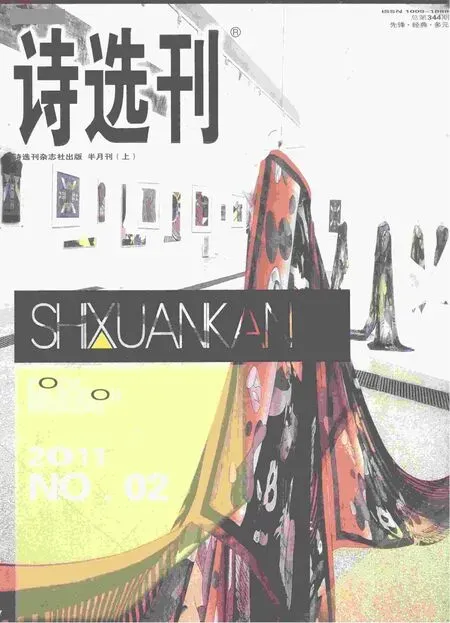韩作荣:《词语的感应》
■韩作荣
韩作荣:《词语的感应》
■韩作荣
尖锐的石头
在开罗的边缘,撒哈拉沙漠
几座金字塔
随着车程的临近
在视线里一点点庞大
才能感知它的壮阔、雄伟
那些宽厚笨重的巨石
砌筑在方形的塔座之上
越接近底部,越是沉实
而岁月的剥蚀
在石表留下风雨噬咬的痕迹
一些石头堆垒着另一些石头
在渐次瘦削里上升
在虚弱的高处变得尖锐
仿佛石头都失去了重量
成为触目的形式
一种挺拔的力量,向上的力量
在锥立中抵达极致
让摆脱重拙的尖顶承受天光接引
只有当阳光偏移的时候
它才在自己的阻碍和遮蔽中
留下浓重的阴影
在卡瓦菲斯故居
亚历山大。吕埃·莱普西乌斯公寓
已经陈旧、灰暗
这是你哀叹时间消逝的地方
声称枝形吊灯
并不为怯懦的肉体所准备的地方
只存一支蜡烛的柔光
以全部接纳,召唤爱情阴影的地方
而今,你也早就消逝了
只留下几个狭小的房间
以及诸多的遗物
今日,六名不同国度的诗人
来探访你的故居
在你的画像前,用不同的发音
倾吐你那独一无二的语调
在雕塑和面膜上
面对瘦弱与忧伤
哦,一位水利局的职员、同性恋者
一生只选定一百五十四首短章
死后才出版的希腊诗人
去世后才广受推崇。直到今天
仍有诗人纷至沓来
观赏你数十种文字的译本
研读手稿,试坐宽大的座椅
注视烟缸里遗留的一枚烟蒂
是的,我熟悉你诗的高贵、简约
虚拟的年代,独特的视野
无奈、悲哀,无法摆脱的困境和痛苦
可我只能用汉语表达敬意
在留言簿上,第一次留下汉字的感言
可耳边回响的,仍是你的慨叹
——“我能在哪里过得好些
下面是出卖皮肉的妓院
那面是原谅罪犯的教堂
另一边是供我们死亡的医院”……
夜 航
走过铁桥的时候
倾听拍打堤岸的水声
我只能用脚步丈量河的宽阔
看被水波摇碎的灯光
随着夜色沉落的昏暗
河滨的层楼参差错落
让大河变得逼仄
水缓缓流动着
河上漂浮游移着一船灯火
尼罗河沉潜在苍茫里
只有河滨泊居的楼船
灯红酒绿,注释都市的繁华
和夜生活的气味
远处,则一片漆黑
夜色遮覆着不可见的奥秘
似乎只能听到水的抖颤、呼吸
和我心脏的搏动
嗅闻城市里熟悉的气息
让我迷惑、随意且懒散
可蓦然间一艘快艇驶过
掀起陡涨的波涛,拍打游轮
唤起平静里久违的激情
让我沉寂的心音也为之搏动
如同一脉动荡的河水
沙漠玫瑰
是谁?从什么时候起
让玫瑰失血
让柔润的花瓣开始僵硬
哦,撒哈拉的沙漠玫瑰
沙黄的,半透明的晶体
不再凋谢
以瓣片的锋刃相互切割
让死去的爱情刻骨铭心
或许,这就是撒哈拉的爱情
失水的爱情
没有轻盈,没有枯萎
连玫瑰都成为生长的石头
哦,那坚实的花瓣
那石头开出的花朵
它告诉我:即使死亡也并非灭绝
爱情,成为一种重量和强度
意 外
我记住了日本的一个故事——
海边的大树倒下,被制成船只
运送淡水
当船遭毁弃,又被当成劈柴
煮海制盐。树消失了
仅剩的一块木料
却被匠人制作成琴
琴音则长久留了下来
如同窗外的楼隙,仅有的虚空
车灯闪烁着惊悸般的光亮
在我的感觉里,日本
是个务实且精细的国度
如同这狭小的房间
窄窄的楼梯,精致的轿车
在适度的节制之中
精当地分割着空间与时间
惜土如金,等级分明
固守义理。可我也诧异
那些从事相扑的男人
为何竟那般丰肥、庞大
岚 山
秋天穿透了木叶
挂在枝头
在山林短暂地停留
经霜之后的秋叶
斑斓、艳丽
抵达透彻
以盛大的辉煌
挥霍着即将消失的生命
我想起一位咯血的女人
披着婚纱
成为爱人怀里死去的新娘
哦,这奢华的哀伤
清冷中的热烈
在嚣闹、明丽的色彩
与肃杀的风里
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
看不见的人
这些面具
让人与兽在一张脸上聚合
是否在告诉我
人也是由兽而来
这真实的可以触摸的虚假
不知它的背后藏着什么
或许,面具的背后是俗常的脸
可脸的背后呢
又隐匿着什么
当面具被一批批复制出来
成为到处兜售的商品
已和鬼神无关,与野兽无关
也与人生和艺术无关
它仍旧是一小块木头
被雕饰的木头
成为一次访问的纪念
可我也时而恍惚。看着它
总感觉面具的背后有一个人
一个看不见的人
他存在着
时时窥视着我的内心
(选自韩作荣诗集《词语的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