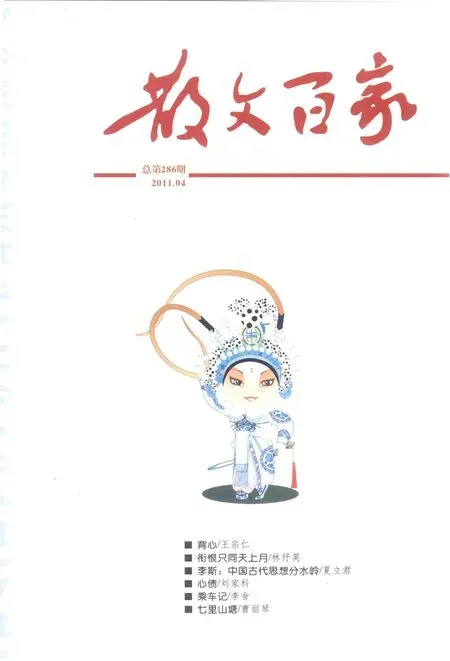被唾沫淹死的女人
●韩冬红
被唾沫淹死的女人
●韩冬红
1
在我的记忆深处,一直有个女人的身影挥之不去。她清秀端庄,说话柔声细语,从来没给谁红过脸,更别说给谁吵过架了。这样的女人在乡下实属罕见。曾经在当地算是文化人的二爷对女性有这样的调侃,他说不结婚的女子一张脸,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女人不要脸,调侃进一步解释为:女子结婚前众人前羞羞涩涩,不曾说话先脸红,可结婚生育后,那张嘴便没有了把门,想说啥说啥,不只是吵架,就是开玩笑也是淫言秽语,低俗不堪。虽然我母亲不会像那些没素养的女人一样开那些低俗玩笑,但她脾气暴躁,几乎很少给过孩子好脸色。我说的这个女人,她不但没有说过脏话,面对孩子的顽皮淘气,最多也就说一句:你这孩子怎么越学越不听话哩!那时我就想如果母亲有这个女人一半的好脾气,我也不至于在二哥因调皮捣蛋,挨打受骂时,吓得躲进柴草屋不敢出来,于是我就在心里记住了这个女人,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这个女人叫啥名字。
在女人家里,和她同样好脾气的还有一个人,那人就是女人的男人。那时,我父亲去世没两年,母亲遇到想不通的事、过不去的坎,没少给女人她男人絮叨,就连我们兄妹六个,都觉得母亲絮叨起来很烦人,可女人她男人不嫌烦,他每次都是认真听母亲说完,然后为母亲一一解开心头的疙瘩,因为这点母亲曾不只一次地说女人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遇到这么一个好男人,不像我父亲生前,你给他商量个事,要么不吭,要么就说些抬杠话。
女人她男人不但脾气好,而且还是百里挑一的好男人,他在县城一家国营企业当厂长,每到星期天一准回家,帮女人担水做饭、下地干活。这在当时,别说当厂长,就是在小县城当个普通工人,回家也是把头扬得高高的,哪里还能让自己的贵体受那份罪?因此,女人就让许许多多像母亲一样给土坷垃打交道的乡下人羡慕不已。
令人羡慕的还不止这些。女人生有三女二男,大儿子因患小儿麻痹症成了瘸子,但并没影响他日后到县医院工作,也没影响他娶妻生子。女人的大女儿命更好,高中一毕业,就被她男人托人安排到了县政府上班,一家七口,有三人吃皇粮,这在乡下人看来,不是烧了高香就是祖上积了阴德。不信你看那些相貌也不差,既不缺胳膊又不缺腿的小伙子、大姑娘,为什么都爬不出这沙土窝?
一次母亲从地里回来早,什么都不说就急匆匆拉我到了女人家,女人递给母亲一个小板凳,坐在她家那小枣树下。蜜蜂们哼着歌,穿梭在密密匝匝的枣花间,一阵阵春光吹来,嫩绿的枣花像雪花一样洋洋洒洒落在地上,也落在母亲和女人头上,女人用修长的手指拂了下乌黑的短发,继续她的话题,她说村会计和妇女主任都在给她儿子介绍对象,一个介绍的是自己的侄女,一个介绍的是自己亲妹妹,女人说她上愁,不知道该让儿子选谁家,所以叫母亲来出个主意。母亲一听笑了,她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就这样,那瘸儿子却娶了个花容月貌的勤快小媳妇。
2
虽然村里的大多数都羡慕女人一家子,但也有少数人眼红,嫉妒。他们不是说女人家的大闺女长得嘴角耷拉,将来是个没福气的主,就是说女人的大儿子模样长得不像他爹。于是这些传言就被闲着没事、从东荫凉倒到西荫凉的长舌妇们越传越玄,直至最后说成女人和老公生前如何如何。
依稀记得一个秋风气爽的下午,我跟母亲去生产队里拾棉花。也许是风撩拨了那些荷尔蒙丰沛的少妇们的心,也许是美丽的景色让她们想起男女之间的那点事,总之,长舌妇议论起了女人,她们的头时而靠近,时而离开,突然间有人先“呸”了一口。又大骂一声:真是不要脸的狐狸精!
那时我并不知道那些人到底在窃窃私语什么,但是我清楚那最后一句话的含义,于是母亲再去女人家串门时,我就会以“作业没写完”为借口,不和母亲同往。若干年后,当我居住的家属院经常有三两个妇女凑在一起咬耳朵时,我明白了她们是在议论别人的私生活。
怪不得母亲当年就说,这唾沫星子能淹死人!而那时我少不更事,根本不明白这其中道理。
后来每家分得了责任田,村里那些好说闲话的女人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再次发现了女人新秘密:你瞧瞧那娘们的地,草都长过高粱了,也不来锄锄,说一定让哪个野男人搂着睡觉呢。
也可能是女人想向那些长舌妇证明什么,一段时间,无论在晨曦中,还是在黄昏下,在地里给猪羊拔草的我总看见女人紧紧拉着男人的手,仿佛稍一松手,男人会像地上的蒲公英,遇风飞走似的。可这一切再次成为街头巷尾议论的热点,那些好事之人和长舌妇们,一个个把嘴撇成“八”字,你一口,她一口得向地上呸唾液,仿佛不这样用力地呸,女人“有伤风化”的行为,就会污染了她们干净的嘴巴。
那时,也有长舌妇给母亲传播女人的所谓稀罕事,母亲就当面说她是吃饱了撑得。后来那些人也就不敢再在母亲面前说女人的坏话了。
3
当家家户户忙碌着掰玉米时,女人她男人因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女人哭得死去活来,她不但没哭活男人,反而把自己哭成了半瞎子。据说她男人是半年前被检查出心肌严重缺血的,从小和男人一起长大的女人,抛开农活,一心照顾男人,静养半年后的男人刚回到厂里,昏倒在会场,送医院途中就停止了呼吸。直到此时,那些长舌妇们才明白,她们冤枉了女人。
然而,那些长舌妇并没从此改了好说闲话的毛病,反而还想着要看女人以后如何生活的笑话。有次很多人都在忙着给大风肆掠后歪七扭八的谷子培土,几个长舌妇又聚在一起说起女人,其中一个说昨晚见有个熟悉的男人身影进了女人家,另一个说一定是女人耐不住寂寞找男人了,说着几个人毫不顾忌得大笑起来。实在看不过眼的母亲,把手里铁锨向长舌妇投掷过去,差点铲到一个人脚上,随后母亲的话也像飞镖一样,向着他们飞去:“你们也不觉得愧心啊,看把人家女的说得一文不值的,人家也不进个男人,就真进个男人又怎么了?挨你们什么事?你们还是人不?”几个女人一听就红着脸,掂起自己的铁锨各自干活去了。
在女人失去男人的日子里,我随母亲多次去看望女人,每次都见女人像雕塑一样盯着男人的遗像。嘴里重复着那句话,早已被我背得滚瓜烂熟:“二嫂子呀,我这睁着眼,就觉得他在看着我,有时候我就喊着他的名字,可是他连答应一声都不肯……”
母亲也同样重复着不能再让我熟悉的话,“要坚强,你还有俩没长大的儿女要照顾哩。”之后女人就不再说话,两行晶莹的泪水顺着数月前还清秀,如今却憔悴不堪的脸上流淌下来。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门槛上,看着有着同样命运的两个女人说话。至今,我脑海中还记得母亲拉着女人的手现身说法,她说在我父亲刚去世不久,感觉一个人拉扯六个孩子太辛苦,就想到了跳井而了却残生,可命不该绝,自己一条腿被人挑水忘到井台上的井绳拌了一跤,才没掉进井里,当回到家看到当时还不到三岁的我,内疚了好久。母亲说倘若阎王真收了她的命,九泉之下,她也不能瞑目。母亲还说从那后她把对父亲的那份感情封存在心里,带着我兄妹六人送走一个又一个不使她感到快乐、但已看到微弱希望的春夏秋冬。
女人听了母亲的诉说后,便苦笑着擦干眼泪,向母亲保证,她以后学着慢慢忘记丈夫,权当是他因了工作忙,而一直没回家。
4
现在想来母亲的这番话,并没有使女人真正从痛苦中走出来,不然,她就不会出现后来的错误,而让那些长舌妇真看了女人的笑话。四年后,我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片故土,但心中却一直惦念着这个女人,不久母亲也由乡下来到都市,我对女人的惦念便就此搁置下来。
不知不觉,我来到都市已是第三个年头。那是一个暮春时分,我独自漫步街头,老乡迎面向我走来,寒暄片刻,我便问起女人的现状,老乡向我叙述了女人的遭遇,听完后我不禁潸然泪下。
自女人她男人死后,她整个像换了一个人,女人时而悲伤,时而兴奋,时而去男人坟上静坐,悲伤时能一晚上不停地哭,兴奋时能一整天不停地在院子里手舞足蹈。为了让两个没结婚的孩子有个像样的家,家族中的长者就找来一名能驱魔降妖的“大师”,为女人驱邪。“大师”煞有其事地来到女人家,里里外外查开一遍,说女人今天这样子完全是因为邪气缠身,得抓紧驱走,否则女人有性命危险。女人的小儿子一听,厉声大哭起来,并跪下来求“大师”救救他妈。
“大师”驾到,引来村里无数看客,他们将女人门口围得水泄不通。
“大师”掐算一番,对家族长者说得等到三天后才能把鬼驱走。三天后一个夜冷星稀的晚上,“大师”重新来到女人的房屋前,橘黄色的灯光下,女人的皮肤如瓷一般洁白细腻……
天空星光迷离,房内灯光摇曳,一阵寒风吹来,连着橘色光亮的方格木窗被邪恶涂得一片漆黑。看客中突然有人吹起口哨,女人的儿子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慌,破门而入,他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一幕。在与“大师”的撕打中,女人跪下替“丈夫”求饶,她说她是和“丈夫”“在一起”,是光明正大的事,求儿子放“丈夫”走。“大师”趁机把衣裤穿好,正准备溜之大吉时,被堵在大门口的人团团围住,而后你一拳我一脚,直至“大师”昏死过去。
气愤之余,乡亲找来一辆排子车,把死猪一样的“大师”拖到车上,趁着夜黑,一路小跑将其抛到了荒郊野外。
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悲剧在愚昧的土地上发生了,可好事儿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而震撼,反而像看了一场老电影一样,乐此不疲逢人就讲。尴尬被插上了翅膀,向四面八方飞去,成为方圆百里几乎家喻户晓的故事,从此被人们当作茶余饭后笑谈的话柄。
说也怪,女人的病一下子好了,她说她像做了一场梦,可女人家再也回不到从前宁静的生活了。可怜女人的大儿子和大女儿都不敢在白天从县城回村里,他们怕遭遇那些人的指指点点。
眼看女人身边的一对儿女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可没谁愿意给当红娘。无奈,小儿子隐姓埋名去了东北,小女儿到了南方,一家人就这样散了。女人家除每年春天还有很多蜜蜂围着那棵枣树采蜜外,那绕梁多年的燕子呢?也许它们不愿看到女人过着那冷冷清清的日子,躲到别处流泪去了。
时光的流逝,也许老家那些人淡忘了当年发生在女人身上的一切,但女人的儿女们恐怕一生都不会忘记,是那些长舌妇,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