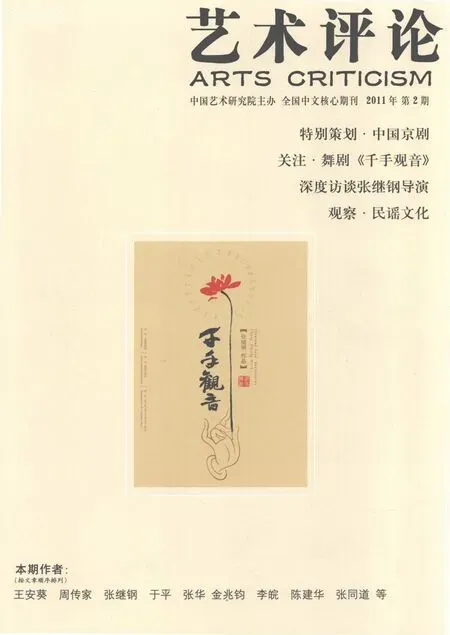大师时代的终结——纪录电影的历史命运和时代选择
张同道
所谓大师,就是那些以个人身影覆盖历史的人。他们被历史选择,又创造历史;他们终结一种传统,又开辟另一种传统;他们撑起一片天空,又留下浓重的阴影。世界纪录电影百年历史犹如一座峰峦连绵的群山,而那些大师正是高耸的巅峰:弗拉哈迪、维尔托夫、格里尔逊、伊文思、罗伦兹、詹宁斯、让·鲁什、梅索斯兄弟、怀斯曼、小川绅介、基耶斯洛夫斯基……
传统是一条波动不息的河流,但传统不是一条直线,它在特殊时空发生转折甚至回流却与特定人物密切相关。纪录片是电影的长子,后来却沦落为故事片的穷兄弟,因为它自创世纪就选择了一条颇有贵族气质的道路:非娱乐化,拒绝向大众趣味低头。弗拉哈迪、维尔托夫与格里尔逊塑造了纪录片最初的品质,也为纪录片开辟了三条不同的道路:弗拉哈迪以《北方纳努克》终结探险电影的命运,挽回纪录片失落的尊严,开创了一种最为贴近纪录本性的拍摄模式和一种记录人类生活的电影类型,显示了人类学家的气质;维尔托夫提出电影眼睛理论,锤炼电影语言,《带摄影机的人》集先锋电影之大成,开创了纪录片的表现方法和创作模式,显示了艺术家的风采;格里尔逊缺少对电影本体的热情——除了创造纪录片(documentary)这一名词,却把维尔托夫的先锋实验和弗拉哈迪的观察记录熔为一炉,打造纪录片的社会功能,显示了记者的风范。学者的良知与思考、记者的社会责任感、艺术家的心理敏感与个人表达引向三种不同风格的纪录片类型。时至今日,这三种类型依然是纪录片的主流,虽然创作方法发生变异,类型风格趋于杂糅。维尔托夫与格里尔逊的电影始终与商业无关,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尽管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却是一次意外,此后他的所有电影再也无法重复这次经验——弗拉哈迪的天真之眼无法看懂华尔街的生意经。
然而,纪录片也并不总是守候青灯黄卷、天涯海角,一旦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纪录片往往尖刀一样切入时代的心脏,置身于社会的漩涡。伊文思与里芬斯塔尔把电影和政治扭结在一起,编织了一个眩目的神话,虽然他们都自称艺术家。伊文思凭借与中国、古巴、越南、老挝等多国政界要人的特殊友谊拍摄了普通电影人无力完成的电影《人民和枪》、《北纬17度》、《愚公移山》。里芬斯塔尔也因为与希特勒的私人关系才拍摄了《意志的胜利》,尽管她极力声辩自己是艺术家,不懂政治为何物。也正因为政治人物发现了纪录片作为大众媒介的威力,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之后,好莱坞导演卡普拉披挂上阵制作了《我们为何而战》,最厌恶战争的剑桥才子詹宁斯制作了《倾听不列颠》、《伦敦可以坚持》。同时,法西斯分子也制作了大量宣传纪录片为邪恶张目。第三帝国宣传部长戈倍尔曾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纪录片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为了摆脱任人打扮的命运,在新兴技术协助下,纪实语言成为纪录片新的美学形态:自然光、同期声、长镜头、跟踪拍摄。20世纪60年代,法国人让·鲁什以《夏日纪事》开创了真理电影流派,美国人罗伯特·德鲁、梅索斯兄弟、理查德·利科克等人开创了直接电影流派,纪录片进一步贴近电影的记录本性。就在这时,越南战争来了,纪录片被迫打破沉默,跳动着时代的良心:伊文思以70高龄奔走在枪弹呼啸的战场,与法国新浪潮导演一起制作了《远离越南》,美国人德·安东尼奥制作了《猪年》,抗议美国政府的越南战争政策,而日本人小川绅介在东京郊区一个名叫三里冢的地方与村民一起坚持七年,制作了七集系列电影《三里冢》,抗议日本政府强征土地——抗议成为这一时期纪录片的突出品质。美国人迈克尔·摩尔继承了抗议传统,自己站在摄影机前以个人的姿势直接挑战权力,《华氏911》直指美国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
中国古人说“文如其人”,纪录片的品质来自于纪录片制作者的品质。世界纪录片史上的杰出人物中,出身于非电影专业的人占据了多数,他们把不同体系的知识、文化和方法带进纪录片:弗拉哈迪是探险家,维尔托夫是先锋诗人,格里尔逊是大众传媒学者,伊文思毕业于商学院,罗伦兹是左翼报纸评论员,里芬斯塔尔是舞蹈演员,孙明经毕业于理学院,詹宁斯是剑桥大学文学系的才子,让·鲁什出身于桥梁工程专业,梅索斯兄弟毕业于心理学专业,怀斯曼是一位想当作家的律师,摩尔是报人,只有卡普拉、罗姆、马勒、小川绅介、基耶斯洛夫斯基等人毕业于电影学院,或来自于电影片场。在塑造纪录片品质的这些杰出人物中,不少人把纪录片作为信仰与生命的选择,与这一选择结伴而行的往往是贫穷和寂寞,弗拉哈迪、维尔托夫、格里尔逊、伊文思、孙明经、让·鲁什、梅索斯兄弟、怀斯曼、小川绅介……莫不如此。他们不懂得投机取巧或见风使舵,他们的作品缺乏娱乐大众的元素,也不流行。然而,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和信仰的尊严:弗拉哈迪一生都以他的天真之眼坚持自己的拍摄模式,从《北方纳努克》到《摩阿拿》、《亚兰岛人》、《路易斯安纳州的故事》,哪怕八年才等到一位投资者;维尔托夫坚持电影眼睛理论,即使斯大林政权剥夺了他的创作自由,退守机房成为一名普通编辑;伊文思一生清贫,晚年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却不拿信仰交换金钱;孙明经从38岁就失去创作自由,并遭受批判,仍然著述不停,珍藏对纪录片的挚爱;阿尔伯特·梅索斯直到80岁还在持机拍摄,坚信“直接电影”是纪录片最好的方式;怀斯曼从1967年拍摄《提提卡蠢事》,至今已完成35部作品,所有作品都采用同样模式、同样风格;小川绅介以生命拍摄电影,每部作品都是与拍摄对象一起长期生活的结果,最后穷困潦倒,生命耗尽,仍不改其初衷。用当下中国的时髦词儿来说,这些纪录片人有点轴。
也惟其这股轴劲儿,才锻造了纪录片独具一格的品质:担当时代良心,肩负社会责任。法国导演克莱德·朗兹曼花了11年时光制作长达9个小时的《浩劫》,仅仅为了给犹太幸存者留下一份证据;韩国女导演卞英珠耗费7年时间制作了三部曲《低吟》,记录慰安妇凄凉的晚年;美国导演怀斯曼穷毕生精力记录美国社会,从学校、医院、兵营、公园、警察局、屠宰场到歌剧院、缅因州……选择纪录片大都与名利无关——像迈克尔·摩尔这样名利双收的幸运儿微乎其微。我很想采访这些纪录片人一个问题:为什么选择拍摄纪录片?职业、责任还是信仰?如果作为职业,纪录片实在算不上一个好选择,既无名又无利;如果作为责任,纪录片确实是一种可供采用的有力媒介;如果作为信仰,纪录片则远远超出了作为电影的自身价值,变成为信仰而斗争的武器。事实上,伊文思正是一个纪录片人的典型标本。他从13岁第一次接触电影,到90岁完成最后一部电影《风的故事》,职业电影生涯长达60多年,完成作品65部,其中包括12小时长度的《愚公移山》。他以《桥》和《雨》确立了电影诗人的地位,以《菲力浦收音机》建立了广告制作人的美名,一个诱人的名利前途拉开电影人生的序幕,可是他却偷偷地跑到比利时煤矿拍起了地下电影,此后带着摄影机远走西班牙战场、中国战场、古巴战场、越南战场——那时他已70高龄,曾经一起去西班牙拍摄的美国作家海明威说,“正当我们庆幸有这么一个适于观察而又没有危险的地方时,一粒子弹飞过来,打在伊文思脑后的墙上”,并断言伊文思早晚会被子弹打死。伊文思没有倒在战场上,但与伊文思一起去西班牙、中国战场的摄影师卡帕壮烈于越南战场,而归来的伊文思则在贫穷中继续拍摄。1973年来中国拍摄《愚公移山》时西装袖口已经磨损,请求陪同人员帮他缝补,周恩来动用总理基金为他订做了一套西装。为信仰而工作,这是伊文思的人生原则。
执著的是信念,善变的是美学。假如说信念是一座矗立的山,美学则是一条流淌的河,绕山而行,曲折婉转。每一位优秀导演都以自己的独特风格丰富了纪录电影美学:淳朴、自然如弗拉哈迪,尖锐、凌厉如维尔托夫,硬朗、华美如格里尔逊,机智、冷峻如罗姆,里芬斯塔尔追求神话的力量,苏克斯多夫向往童话的境界,小川绅介的作品透出泥土的芬芳,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溢满光影声色的华丽技巧……在众多大师级导演里,伊文思与怀斯曼宛如两座对峙的高山,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创造两种风景:前者是高峰入云,每升高一层都是新的风景,从先锋派、左翼电影、干预电影到超现实主义,一生都在变,变幻莫测;后者则是群峰并立,绵延不断,气势雄浑,从第一部电影直到最新一部,35部电影风格完全相同。
纪录片从创世纪以来的80多年间一直笼罩在大师的光辉里,那些卓然独立的先行者命名纪录片、创作方法、美学流派、美学运动甚至某一段电影时间,他们为纪录片立法,确立新的标杆;他们扭转历史的航向,创造新的美学;他们担当时代的良心,留下不朽的经典。一部纪录电影史就是大师与大师交替的历史。
然而,大师时代无可挽回地终结了。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电视替代电影成为纪录片主流,BBC、Discovery Channel、NationalGeography Channel等电视工业形态成为纪录片传播的主要空间,纪录片品质发生明显变化,娱乐元素骤然增加,美学风格整齐划一,导演变成一个技术性职位。纪录片被迫面对后大师时代,以电视为代表的工业形态已经成为纪录片市场主流。
当然,独立制作领域还将出现一些大师性人物,虽然他们的座椅被搬到电影节、大学和博物馆里;他们的作品也许还会创造市场奇迹,进入大众传播领域,虽然那只是偶然事件。但大师的美学创造和文化价值却不会因为大师时代的终结而终结,相反,在电视工业发达、流行文化横行的时代,大师独特的文化价值与美学个性格外重要,大师时代终结并不等于大师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