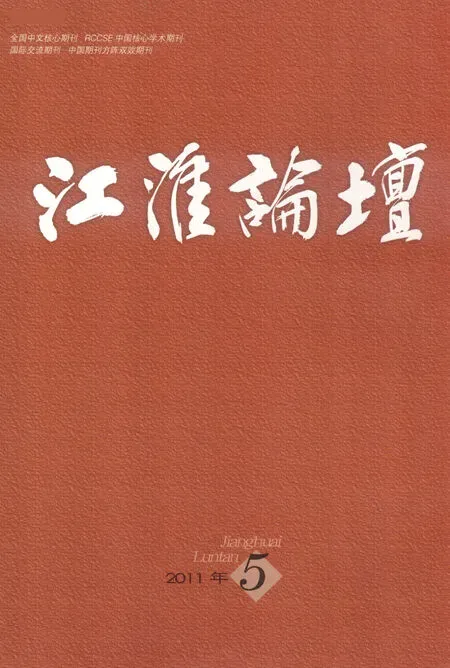皈依与升华:人类的诗意栖居*
——论当代生态小说的回归想象
吴怀仁
(陇东学院中文系,甘肃庆阳 745000)
皈依与升华:人类的诗意栖居*
——论当代生态小说的回归想象
吴怀仁
(陇东学院中文系,甘肃庆阳 745000)
生态环境保护、低碳生活、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关键词,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解决人类的生态危机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生态小说是生态文学的一个门类,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主要突出人与自然的齐同和谐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更强调人对自然的敬畏亲和态度,强调人的本质还原、自然的返魅、生命的归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凝结了创作主体浓厚的生态亲和意识,剖析了人类自身的悲剧,突出了鲜明的生态保护回归主题,多角度塑造了具有自然人性和生态人格的新形象,深思了人类回归自然家园、实现自我救赎梦想的诸多可能。文章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自然回归想象从文化渊源、土地回归想象、家园回归想象和童年回归想象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当代生态小说;生态意识;回归想象;土地;家园;童年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极大的威胁,人与自然的关系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21世纪以来,生态环境保护、低碳生活、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生活的关键词,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解决人类的生态危机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文学领域,自1962年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生态文学时代的来临,从此,开启了一个运用文学形式自觉地表达生态意识、深入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阶段。生态文学是以现代生态主义运动与思潮为契机,崛起于20世纪中期,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生态保护、传播生态伦理思想为基本主题的文艺思潮。在生态文学评论家王诺看来,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探询生态危机社会根源的文学。”表现“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1]生态小说主要是突出人与自然的齐同和谐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更强调人对自然的敬畏亲和态度,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生态小说对人的本质的还原、自然崇拜的返魅、生命的精神归根的强调。因此,当代生态小说题材的现实性倾向为生态小说获得了主题的严肃性与崇高性。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乡土小说、寻根小说开始至今走过了两个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作家们大都运用纪实或魔幻的方式,大量书写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问题,是对生态环境进行拯救的急切呼声。进入第二阶段,生态小说的创作队伍也逐渐扩大,这些小说通过对自然界的感性生命表现,创造了神秘而又和谐的大自然审美空间。总体上说,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凝结了创作主体浓厚的生态意识,突出了鲜明的生态主题,多角度塑造了具有自然人性和生态人格的新形象,剖析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深思了人类回归自然家园、实现自我救赎梦想的诸多可能。
一、当代生态小说回归想象的思想文化渊源
西方生态小说主要表现的是生态末世论和宗教救赎思想,而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主要表现的是对于大地和自然万物的钟情与热恋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意识和回归想象,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于创作主体的潜在影响。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古国,其文化与文学贯穿着强烈的对于大地和自然万物的钟情与热恋的家园意识和回归想象,这为当代生态小说写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化资源。老子《道德经》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表明了处于天地之间的人必须遵循自然法规,与自然和谐相处。孔子《论语·先进》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归于自然家园的理想精神情结的想象。《庄子》中“夫大备矣莫若天地。”“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奚为哉?天地而已矣。”[2]这些言论表达了万物齐同,物物转化,毫无界限,主张忘情寡欲,心斋坐忘,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生态思想和观念。其它如《墨子·尚贤》中“‘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故圣人之德,盖总乎天地者也。 ”[3]《中庸》中“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4]天地自然的厚重、沉静、坚韧、富于涵容、德化同类的人格化品格,人类不敢擅自僭妄的威仪,这些也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尊天地自然而小人类自身的生态思想观念。《易经》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哲学思想典藉,这部著作以天人关系为中心,展示了中国传统“生生之为易”的古典生态智慧,包含着浓郁的蕴涵哲理性的精神家园意识和回归想象。《易经》中的乾、坤二卦中关于天地自然的论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还有“元亨利贞”四德之美与“安吉之象”的论述[5],表现了天地自然生态为人类生存之本、精神之源的精神家园意识和回归想象,也表现了治家有道、天下安定、家庭相融都与天地自然的和谐有着极大的关系,人类应安静以守,附丽光明,返本回归。可见,家园意识与回归想象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从而,这种思想观念也就潜移默化地成为当代作家生态小说创作中家园意识和回归想象的集体无意识情结。在文学创作传统上,从《诗经》开始,就有大量的文学典籍抒写了先民择地而居,选择有利于民族繁衍生息地的诗性篇章。《大雅·绵》记载了周先祖古公亶父率民去豳,度漆沮、逾梁山而止于土地肥沃的周原的过程。《小雅·采薇》中写游子归家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表现了梦中家园的回归想象。《卫风·河广》则更加具体地描绘了客居他乡的宋人面对河水所抒发的梦园思归之情。“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6]《诗经》对自然的敬畏思想和家园回归想象对后代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以致于南北朝时期产生的山水田园诗和家园思归想象主题一直延续至今。
总之,从中国传统的盆地思维所产生的思想文化或古代文学创作,体现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之情,追求一种人与自然的齐同与和谐。这种文化积淀促使当代作家的生态写作从潜意识里生发出一种对自然万物的守护与对于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回归,体现出区别于西方对自然破坏的末世情怀和宗教救赎思想,而是感性地创造一种理想的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精神家园而去苦苦追寻和想象中的回归。
二、当代生态小说中回归想象的主要对象:对土地的回归想象
处于天地之间的生民,对于自然万物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激之情。对于天地化育的膜拜,对于自然万物的崇敬与感恩,从古至今,都是作为生态写作取之不尽的诗意源泉。人类无权为所欲为地攫取自然资源、剥夺自然生命。相反,人类
对自然万物要有敬畏之心,小心遵守自然规律,当好世界万物看护者,创造出只能通过使世界完美才能完善自身的理想世界。而现代科技理性所建构的现代社会意识,造就了人类的惯性的力量和智慧,约束人类回归自然的想像意识,使人类已经与纯粹自然环境告别,狭隘的城市空间和被破坏的农业生态、自然社会以及不再有未被开垦过的荒野,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危机日益显著。尽管人们在努力制造城市绿地和人工恢复自然生态,但一室之绿难为春,这只能使人们更多地偏离了自然,放弃了自然回归,放弃善待自然、与自然万物和谐同生的生活的情感与多样选择的可能。可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它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7]中国当代生态小说首先从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的文化蕴藏中努力汲取丰富的生态思想和观念,并以此创作出大量的生态小说,形成了对土地和其上生存的万物的齐同、回归想象。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所写的“故乡的大地”,是母性的象征,其上由血滋养的生命,如此的盛大而壮丽,对洪荒境界的生存体验,农业社会的温柔敦厚,体现了作家寻求陌生的文化感受与美感,是一种对于原始自然的一种理想化的回归想象的体验。张承志置身于辽阔的大草原时,于万籁静寂中捕捉到了自然世界的神秘,听到了自然世界对一个孤独灵魂的低声召唤,字里行间流动着对自然呓语的由衷感动。他在《黑骏马》中写道:“此刻,宇宙深处轻轻地飘来一丝音响。它愈来愈近,但难以捕捉,像是在草原上空的浓郁空气中传递着一个不安的消息。等我刚刚辨出了它的时候,它突然排山倒海地飞扬而至,掀起一阵壮美的风暴。”[8]作家在自然的柔情中,反复领略自然世界的宽厚仁慈,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与其合二为一,从中体现出了他对自然天籁的向往和回归想象。正如台湾作家李桥在《寒夜三部曲》的总序中所说的:“万物是一体的。而大地、母亲、生命(子嗣)三者正形成了存在界连环无间的象征。往下看,母亲是生命的源头,而大地是母亲的本然;往上看,母亲是大地的化身,而生命是母亲的再生。生命行程,不全是人意志内的事;个人在基本上,还是宇宙运行的一部分,所以看春花秋月,生老病死,都是大道的演化,生命充满了无奈,但也十分庄严悠远。人有时是那样的孤独寂寞,但深入看,人还实在濡沫相依中的……”[9]姜戎的《狼图腾》以狼的故事的许多片断结构完整的情节,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草原人的游牧生活,在草原生态被破坏的背景下,揭示草原上各种生物包括人的内在关系的同时,又揭示了游牧民族对生命敬畏、对自然生态崇仰的内在精神和回归情怀。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以商州人与狼仇杀作为叙事结构框架,以家族血缘的叙事方式,描写了商州猎狼队消灭野狼的过程,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表现了对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生态性思考。以人类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变异,隐喻了生态环境整体系统失衡之后的灾难性症候。小说在虚实交错中渗透了大量的对人与自然关系和人对于原始自然世界的回归的象征性意象,从而建构了形而上的生态回归主题。怀念狼就是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追寻和回归,狼的悲剧将是人类未来的悲剧。这是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第一部具有反乌托邦性质的生态预警启示录和自然回归想象小说。正如芭芭拉·沃德所说:“在这个太空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养育着全部生命体系。地球的整个体系由一个巨大的能量来赋予活力。这种能量通过最精密的调节供给了人类。尽管地球是不易控制的、捉摸不定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它最大限度地滋养着、激发着和丰富着万物。这个地球难道不是我们人世间的宝贵家园吗?难道它不值得我们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都倾注给它,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我们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 ”[10]
三、当代生态小说中回归想象的理想状态:对家园的回归想象
回归想象中的家园意识是生态文学永恒的主题和梦想。“‘家园’一词在汉语中原本是对出生地和栖居之地的经验性表达,它寄予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性因素,诱发着人的乡情、亲情和思乡感、归家感。海德格尔诗学传入中国,‘家园’又被赋予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如‘接近源泉之地’、‘接近极乐的那一点’,且与‘存在的敞开’、‘诗意地栖居’、‘澄明之境’等等相联系,‘家园’在这里是一种比喻,一种象征,特指理想或幻想中充满了幸福、和谐与温馨的所在。”[11]当代生态小说作家们用小说来反拨现代文明,理解自然,这就使得他们作品对现代生态的思考和讨论中时常流露着一种有家归不得的怀乡病。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对家园的理想性回归想象就是对人类黄金时代的梦幻式追忆,而且伴随着梦醒后的痛苦与失落,这种哲人般的诗性情怀,从灵魂深处影响着人们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对理想家园的想象性回归。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生态文学不是诞生于愉快的创造冲动,而是诞生于人和人民的痛苦及其灾难深重的命运,诞生于拯救全人类的思考。”[12]王蒙小说《烙饼》中对家园的想象是“烙饼使他想到家乡、童年、母亲、前妻,他都快要掉泪了。”施叔青在《牛铃声响》中对家园的想象是“牛铃声响——那是记忆中家乡黄昏从晚烟深处传来的。”在当代生态小说里,家园想象不过是家乡村口的那棵老槐树,院子里葡萄架下听老人们讲故事的小木凳,静夜里的蛙鸣或蛐蛐叫,这一切都使人们能从现代都市的嘈杂中走向记忆,回归家园,想象人间最质朴的温情,像诗人叶赛宁说的“找到家园,就是胜利”。当代小说家在生态小说的艺术还乡中,往往借助于记忆材料的喷发激情,寻找想象中的家园。如郑万隆对“华严浩荡的山林”的艺术呈现,犹如对生命力量的呼唤,对生命图腾的苦苦寻求,体现了回归渐远的家园想象中既有心灵的安抚,又有灵魂的煎熬。张承志小说中于大草原的回归,极尽渲染,颇为张扬,是一场家园回归想象的盛大飨宴。莫言小说中对高密东北乡的家园回归想象透出泼墨如血的狂放激情,家园是在目力不及的记忆的漩涡中流淌出的辉煌。这些作品中对家园的回归想象是一种仪式化的,是对当代工业文明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潜意识的抵制,是一次发自心灵深处的绝不愿告别的告别,是一次为当代人逝去的梦乡的一次痛苦而美丽的追寻,是当代人对于自然的罪行的一次宗教式救赎。
人类置身于自然世界中,每时每刻都离不开自然界无私供给的清纯的空气、洁净的水、明媚的阳光、翠绿的植物、活泼可爱的动物。当代生态小说的生态话语就是从这些天然朴素的情感中提炼出来的,从生态到环境再到文学的想像就是书写自然与人和谐的理想状态,通过对家园的理想化构建来改变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适应,从而也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生态形式。想像建构了当代生态小说中人与生态环境的共同体系,在充满想像的家园回归中,人类才能不断地创造真正的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并充满想象的生活。家园回归想像培养和保留了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生活状态,也保存了人类理性的选择自然和谐生活的智慧。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作家大都具有浓郁的诗人气质,对自然世界十分敏感,他们用心地聆听和观察自然万物。张炜的小说《怀念黑潭中的黑鱼》用具有寓言风格故事,表达了人应与动物和睦相处的思想。杜光辉的中篇小说《哦,我的可可西里》,将故事的背景置于青藏高原上广阔美丽的可可西里,将其比作人类的发源地,以可可西里秀美的风光与过度开发造成环境破坏的对比,针砭当代社会中的人性堕落,呼唤对自然生态平衡的保护,召唤人们进行精神的家园回归。温亚军的《寻找太阳》讲述了人与动物相互依存、和谐相处的故事,洋溢着人与自然在和谐自然关系中所蕴涵的温情,引导人们尊重自然,亲和万物,在与世界万物的齐同共生中构建人类与自然的理想家园图景。这些作家对自然万物的描写优美而细腻,对自然的赞美性描绘、对回归理想家园生活的神往,呼唤人类对自然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呼唤人类重返和重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家园。正如马丁·海德格尔所说:“按照我们人类经验和历史,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13]
四、当代生态小说中回归想象的终极表达:对童年的回归想象
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让我们如大自然一样自然而然地过上一天吧,别因坚果壳和掉在铁轨上的蚊虫翅膀而脱离轨道。……任他人来来往往,让晨钟敲响,让孩子们娇啼吧——下定决心,我们要过好每一天。”[14]在生态小说创作中,童年、孩子、动物也就自然地成为回归想象中的关键意象和主要话题。在中国当代生态小说中,童年则脱出事实,渐次被赋予形态和意义,成为小说文本关于回归主题的童年想象的情感经验。正是对童年想象的不同状态的抒写,使得当代生态小说回归想象中关于童年的想象呈现出复杂性。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学中说道:“童年或者说少年时代的阅历构成一个人生命情结的本源,构成一个核心的意象,此后的一生中,这个人的精神永远在追寻童年种下的梦幻,或者在寻找少年丢失了的东西。”[15]因此,关于天堂般美妙的童年想象的梦境也就必然地出现在当代生态小说之中并成为其主要的叙事主题,也成为当代生态小说抵制现代文明对于自然世界侵害的最佳精神抚慰剂。王蒙在《蝴蝶》中对折磨着成年人类的童年的怀念这样说:“在他还不是张思远,当然更不会是张教员、张指导员或是张书记,在他只是石头,或者像母亲称呼的那样——小石头的时候……”[16]这里童年的记忆想象成为作者心灵的宗教圣地、施洗的圣水,是一种对于自然而美好的童年生活的一种自我意识的展示,是一个赤条条的本我,是一种作为生态伦理境界的永远的诱惑。张炜在 《童眸》中说:“……最要紧的是质朴了,是纯洁了。最伟大辉煌的东西,从来都是质朴的人创造出来的。而质朴和诚实一样,来自河流、土地,来自童年的记忆和留恋……”“童年的朋友是什么?是田野,是树林和小河,是质朴和忠诚!”[17]郭雪波在《大漠狼孩》中以孩童的视角写到了对现代人类的失望。小说中最终被劫匪杀死的瘦子对少年的父亲说,大家都说狼残忍,其实狼比人可靠。在这里,少年眼中的狼体现了小说所要表现的主要价值意义,作为现代人性堕落的对照,狼身上体现出了可贵的人性。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无论是对于童年的记忆还是于童年生活最接近的动物、植物世界的抒写,都是人类回归想象的表现,是人类纯真的心灵世界的展示和呼唤,是引导人们介入到现实中去为人类的将来的生存寻求一条充满希望的路径,是作家们用乌托邦的热情和精神创造了一个人类诗意栖居的理想生活,是人类生态想像所带给人们的理想生活境界。当代生态小说中的关于童年的回归想象就是这么构造了生态的思想或理想境界,从而影响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行为选择,为人类提供一个灵魂安居的精神生态空间,找回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的精神家园,当然也就成为当代生态保护想像的一个核心隐喻。管桦在他的作品中写到:“豆棚瓜架浓荫里,贴着红色剪纸的小窗,那母亲居住的小屋,便是我的祖国。那池塘边,土坎上最早开放的一棵金黄色的迎春花,从长满枯草的墙头上露出来的几枝粉红色杏花和红色的桃花,池塘映着蓝天白云的水里,冒出一片片尖尖苇笋,可以清楚地看见白翅膀的鸭子在清澈的水中,滑动着鲜红的扁脚掌,便是春天给我的烟景。……我和男女小伙伴挎着笼筐,拿着圆形小铁铲,在池塘边挑野菜时的说笑声,便是醉人的乡音。”[18]作家所创造的童年的世界,是人类心灵的世界,是现代社会生态破坏后人类精神救赎的世界,它连接着过去的想象,又是未来世界的想象。当代生态小说作家们面对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他们没有妥协,没有逃避,真诚的忠实于自己对大地、万物的感受,从童年梦境的想象性创造中寻找回归自然和谐之路,让现代人那浪迹尘世的灵魂在大自然温暖的怀抱中得到精神的抚慰和心灵的安宁。阿诺德·伯林特说:“整个地球,不仅是沼泽地,是一种充满奇异之地,并且我们人类——我们现代人类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把这种庄严放进危险中。没有人……能够在逻辑或者心理上对它不感兴趣。”[19]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生态小说注重对自然生态的哲学性思考,以此获得正确的生态价值判断,并用其探索生命个体在自然界重获精神家园的新的感知方式而形成了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独特的审美维度。就当代生态小说的主题来说,大都重在关注自然中心主义和人与自然的齐同和谐,探索人类走出生态危机、拯救世界万物,为人类的未来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的可能性,寻找人类与自然重归于好的和谐世界的新途径,进一步提升人在自然这个伟大的母亲的怀抱中生存的内在精神境界,从而获得正当的生态思维和家园感并重新激发人类热爱自然生命的天性,重新恢复人类的精神世界和自然关系的内在和谐,并以此形成了当代生态小说运用土地想象、家园想象、童年想象来构建其救赎人类迷失的心灵、回归自然生态理想境界的生态小说观念。这里,用克罗奇的话来给本文所论述的中国当代生态小说的回归想象作一个形象的注释是很准确的:“当人们又重新拾起旧日的宗教和局部地方的旧有的民族风格时,当人们重新回到古老的房舍、堡邸和大礼拜堂时,当人们重新歌唱旧时的儿歌,重新再做旧日传奇的梦,一种欢乐与满意的大声叹息、一种喜悦的温情就从人们的胸中涌了出来并重新激励了人心。 ”[20]
[1]王诺.什么是生态文学[N].中国绿色时报,2006-2-13(4).
[2]郭庆藩.庄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87.
[3]墨子.墨子[M].施明,译注,广州:广州出版社,2004:49.
[4]朱熹注.四书五经(中庸)(上卷)[M].北京:中国书店,1988:12.
[5]郑玄注.周易乾凿度(第二卷)[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23.
[6]朱熹注.四书五经·诗经(中卷)[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8:37.
[7]可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M].徐波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29.
[8]张承志.黑骏马[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37.
[9]李乔.寒夜三部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6:1.
[10]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M].国外公害丛书编委会,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60.
[11]王友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7.
[12]别尔嘉耶夫.别尔嘉耶夫集[M].汪建钊,选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6.
[13]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熊伟,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305.
[14]亨利·大卫·梭罗.瓦尔登湖[M].王金玲,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59.
[1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9.
[16]王蒙.王蒙中篇小说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37.
[17]张炜.张炜作品自选集[M].南宁:漓江出版社,1996:237.
[18]管桦.文学:回忆与思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544.
[19]阿诺德·伯林特.环境与艺术:环境美学的多维视角[M].刘悦笛,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91.
[20]克罗齐.美学原理[M].朱光潜,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58.
(责任编辑 岳毅平)
I247
A
1001-862X(2011)05-0164-006
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1010-03);陇东学院科研基金项目(XYSK0607)
吴怀仁(1966-):男,汉族,甘肃庆阳人,陇东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写作基础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