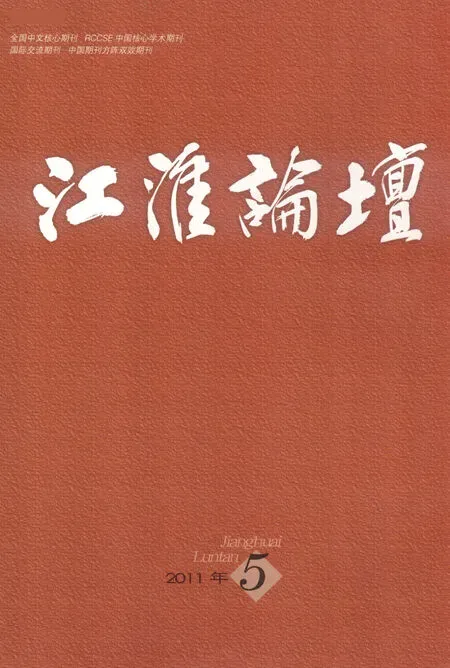论哈贝马斯“媒介化”公共领域的嬗变*
解 葳 高宪春
(1.济宁学院,山东济宁 272000;山东师范大学,济南 250014; 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论哈贝马斯“媒介化”公共领域的嬗变*
解 葳1高宪春2
(1.济宁学院,山东济宁 272000;山东师范大学,济南 250014; 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一种主流媒介的转变会导致社会公众话语结构的改变。文章对不同时期“新媒介”技术对公共领域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性探讨。从印刷媒介时代被启蒙的大众到电子媒介时代的孤独的人群,再到网络媒介时代夜总会的狂欢者和受幻象蛊惑者,人们沉溺于技术带来的快感,忽略对自身本质的关注,感性的冲动替代了理性的行动,人们丧失了公共领域的理性自我。公共领域被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为技术至上论。技术不能替代人性中光辉固有的属性,公共领域的衰落只是技术异化人、降低人的尊严的一个表现。人其为人不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而是因为对自身尊严的维护,对他人友善的交流和对自然的崇敬。个体和技术的博弈将决定公共领域中的人是WIKI技术的主人还是仆人。
公共领域;新媒介;技术;理性;娱乐化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意义在于提供了反映人类某一共性的参照话语体系,“一种新的硬性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 ”[1]15大众媒介对公共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使我们由此出发,探究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各阶段生活的现实影响成为可能。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每种新媒介[2]的兴起都促成传统传播模式的颠覆,影响了“话语共同体”参与社会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技术对生活现实性的改变,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凭借不同媒介对于周围环境实践与认识发展的结果。
不同时期不同“新媒介”的应用普及,不是单纯技术科学领域的问题。换言之,技术升级的新媒介以及它所构成的新符号环境和公众话语方式,主导着各个层面公共空间的变化。从现实看,“日常生活媒介化,媒介生活日常化”已构成人们生活的宏大背景,技术渗透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主义成为技术媒介追逐的主导性发展潮流,人们普遍享受技术神话带来的快感,公共领域批判力逐渐衰落。我们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关于人类发展共性话语为参照体系,对不同时期“新媒介”的发展对公共领域技术异化进行批判。批判目的在于更准确地理解当下新媒介技术发展带来的变化,并作出理性预判。
一、被启蒙的大众:乐观——启蒙的开始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介于公共权力机关和私人领域之间,能够对“具有公共性质的……一般交换原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1]32,“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1]35。哈贝马斯设定了一个极具理想化的言语情景[2],他假定人们的言说是为了交流而做出的努力。在这个只能无限接近的标杆之下,我们以为重要的并不是这一先验的主体假设,而是实际贯穿于其论述始终的大众媒介——文字、印刷、电子媒介等——的作用。正如大众媒介“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1]15哈贝马斯理性的公共领域是依托于一定的媒介,尤其是大众媒介实现运转的。
不同时期的新媒介亦会形成各异的媒介环境,不断改变人际交往关系、交换关系,继而影响到人们所在公共领域的变化。“一种重要的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是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方式。”[3]33我们依据各个时期主要媒介(Index Medium)将哈贝马斯“媒介化”的公共领域及受众的衍变做如下划分:印刷媒介时代(被启蒙的大众)、电子媒介时代(孤独的人群)、网络媒介时代(夜总会的狂欢者和受幻象蛊惑者)。这种划分旨在明确新媒介所发挥的作用——因为特定的媒介形式会偏好某种特殊的内容,适合某些人观念的表达,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当到达某个临界点,外部条件(包括技术条件)成熟后产生的,印刷媒介时代被启蒙的大众是探讨起点。
起初革命思想占据公共领域中心。哈贝马斯继承了马克思媒介启蒙主义的乐观态度[4]:具有革命意愿的“理性个体”而非受制于经济的乌合之众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这理想中,人们在生活世界构建起作为言论市场的公共领域,以“文化的商品化”作为报纸积极意义的依托,人们得以走出咖啡馆。这种乐观是基于印刷术呈现的世界,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而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的完善自己。”[3]67“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 ”[3]80
公共领域生来是交流批判的。哈贝马斯认为,起初人们在咖啡馆里借以文学的批评,形成介于公共权力机关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 “协商”的空间,随后转入政治领域,人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对重要议题进行协商,形成观点,没有受到惩罚或暴露隐私的担忧,人的自由权利得以充分显现。一种观点认为媒介技术是中性的和客观的,其影响力主要是来自于它本身的工具特点和科学属性;但这显然忽略了它作为意见协商交流工具和平台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倾向,尤其新媒介的发展扩展了人们的公共空间,使多样性的意见交流成为可能。尤其是使用媒介的媒体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组织或机构,有自身整体规范,受到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其意见往往代表组织机构的整体判断。
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决定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技术决定意识形态,而技术则是生产方式核心所在。他乐观地认为“理性个体”天赋地拥有理想主义光辉的希望和冲动,会运用新媒介不断地打破既有的文化和秩序,大众媒介起到了启蒙者的作用。
二、“孤独的人群”:悲观——空间失落的逆转
随着电子媒介的出现,娱乐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人从咖啡馆里走出来,进入啤酒屋,他们寻求的不再是咖啡的提神作用 (咖啡象征着理性),而是啤酒的麻痹作用(啤酒象征着非理性)。在酒精带来的幻觉中,人们沉醉而不自省。哈贝马斯不能忽略一点:媒介更替促使人们感受的变化——人们是自愿选择 “沉醉不知归处”,并非“老大哥”[5]强权独裁威吓的结果,而是听从了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召唤。
电子媒介让人们减少了交流的冲动,或者说为人们的独处提供了条件。虽然电影需要集合在一起观看,但电影奉行理查德·瓦格纳精英主义美学的理念:屏幕的明亮和观众席的昏暗形成了对比。原来敞亮的交流空间,被幽暗的沉默空间取代。互不相识的人们在幽暗的空间欣赏电影,成为城市共同体中类似宗教的体验,“人虽挺多,但大家都感到孤独”,非日常的体验让人们暂时忘却生活中的苦恼,获得了某种解脱感,同时,人们渐渐遗忘社交习惯,缺少了交流的冲动。
广播电视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普遍性的交流”媒介,一诞生就被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先是割裂了声音与肉体,也使得人们的视觉变得越来越统一化和单一化,造成了人们 “空间感的失落”,大众缩在狭小的空间里,如同隐于“山洞”,依靠电波和“光点马赛克”构成的声像,自生自灭,从根本上去除了“市民公共领域”的成立基础。与具有话语权特性的沙龙咖啡馆和报纸广场文化不同,广播电视是“无回应的言语”,不可能让人们谈及往事,也不可能让人参与其中。
电子媒介让理性公民变成了感性消费者。正如君特·罗特斯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阐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强调了“以阅读为中心,以交谈为核心的公共交往的合理层面[1]4”,因此他认为“平民公共领域的产生,标志着小市民和下层市民生活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将经济市民变成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只有在这个时候,公共领域才获得政治功能……自我组织以自由组织起来的成员间的公共交往为渠道”[1]11。表面上与公正相关的各种议题得到讨论,实质是以市场消费的大众文化消解了公共领域的存在。电视摧毁了业已建立的公共领域的根基,将大众拖进封闭的空间里,公民成为了消费者,理性提问已经在媒介娱乐的冲击中消褪,人们与其说在理性地观看事实真相,倒不如说是一种意象快感的获得和满足。
电子媒介的柔性暴力剥夺了交流的空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3]201。电子媒介显然是后者,它不是要强行地禁止人们进行理性的交流,而是柔性地以娱乐方式取代思考方式:人们不是不愿思考,而是因为缺少思考的媒介语境,被改造的不会思考了。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对着荧屏呆呆傻笑已经成为“共像”,电子媒体柔性暴力剥夺了人们思考的空间和能力。
“电视人”[6]、“土豆沙发人”等构成了“孤独的人群”[7],理想的交流成为奢侈的期盼。一种重要媒介的转换,会导致公众话语结构的改变,会使用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象征符号,在社会环境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继而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受到电子媒介熏陶的人们渐渐脱离哈贝马斯的理性言语情境,更谈不上理性的交流。印刷——电视媒介的这种转变促使从启蒙的大众转向孤独的人群,电子媒介成为膜拜和批判的“神灵”。
三、“夜总会的狂欢者”:混沌——时空失落的褪化
在对电子媒介的批判中人们迎来网络时代。“网络媒介去中心化的分散式结构,使得对一种新型的‘公共领域’、‘公共社会’以及话语‘狂欢’的憧憬愈加明显,而对文化霸权和中心化的社会文化控制则做出了乐观的判断”[8]人们为网络的草根性欢呼,表现出理性交流复兴的期望。人们“把自己的中枢神经扩展到了地球的各个角落,”在我们时空已经弥合消失的地球上,网络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已经超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设想,已经成为公众自由进行话语交流的新型公共领域,形成多元化的交往特征[9]。网络诸如匿名性、即时互动性等至少在条件上提供了理想交流的可能。“话语权在本质上不是能否说话的生理、物理问题,而是话语之间关系的社会问题”[8]。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网络数字化加强了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单向监管的力度。媒介文化塑造了公共领域的总体观念和个体观念,两者的消长,常常表现出同公共权力机关关系的亲疏。理想状态下,理性总体观念是在差异性个体观念基础上产生的,而且前者应给予后者更多的自由、协商的时间和空间。商业化媒介技术的强力进入,使这一切发生了变化,媒介技术与媒介文化是不同的,这在前互联网时代是明确的,但是当下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形成“媒介技术=媒介文化”趋向,由此总体观念逐渐挤占了个体观念,甚至可以随意地屏蔽或改变个体观念。以往打断言语的交流需要实体——个人、群体、组织等——的介入,但是在运用新媒介过程中,无论是何种形态媒体,数字化使得“打断”两端或多端的交流,都已经绕过了实体,以虚拟的电子波形态进行,轻而易举且不会留下一点痕迹的实现改变差异性个体观念的目的。人们感到了时空的失落,因此没有了自我个体,而代之以“混沌的总体”。
网络带来的“时空感的失落”造成人们思考能力的丧失。宽裕自由的时空促成成熟有效的思考和讨论,却被新技术媒介篡改成了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的狂欢。向真、向善、向美的追求是与现实世界中人们的时空观念紧密相连的,表现了人们认识自我、他人、自然存在的不懈努力。一片混沌中,人们的理想开始崩溃。理性的思考变得孱弱,肆意和矫情成为常态,“美”的东西被扭曲;怀疑一切的态度毁灭了人们对“真”的信仰;当谎言骗取眼泪和同情的情况屡屡发生,影响不断扩大时,人们对“善”的追求变得迟疑不决。形式上类似“火星文”的革命只是对不满形式上的颠覆,丝毫没有触及 “景观社会”(Society of Spectac1e)对理性的公共领域侵害的本质,却造成了实际交流的不便和“特权化”。
以公开性、具有独创性和自由通畅的交流为条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为人们提供了社会交往的途径和共同体的意识,目的是为了人们有能力对公共领域本身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各种实践活动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各种新技术、新媒介和文化形式的发展,促成了依仗于消费的各种个体化形式的泛滥和堕落,不是公开辩论和讨论的各项原则的贯彻和发展。仅从网络对待黑客的态度上,人们就可以明白,这不是哈贝马斯们的理想时代。哈贝马斯的“理性的咖啡馆”搬到网上,却成了“夜总会的狂欢”,从电子媒介进入到网络媒介,“孤独的人群”进入到喧闹的虚拟时空,开始肆意狂欢,人们没有在意:自己纵身跳入的“现时”世界与过去和未来有无关联?时空感的失落让意义的探寻变得不合时宜,及时行乐成为主流,随着蕴含着人类理性精神传统的衰落,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渐渐失落在了“蛊惑人的幻象”之中。
四、“受幻象蛊惑者”:迷失——虚拟指代的盛行
夜总会狂欢者迷幻于网络重构的 “娱乐化”的文化和现实,对理性交流的目的和行动变得更加迷茫。时空感的失落导致以往媒介的“现时”意识形态与网络的“虚拟”意识形态的鲜明对照。网络带来流动化、分化和细节化、碎化和片断化不断加深的社会现实,同时给人们带来了一种虚假的体验。网络却让人们感到能够体验复杂社会生活的全部,但现实中的个体是不可能。正如盖伊·塔克曼所说的新闻是“社会性的构建物”[10],网络同样只不过是提供社会局部现象的解释框架,以一种伪理性促成电子波构成的虚拟网民间的交流,它采用典型的超链接方式和关键词的搜索功能,让网民忽略掉这一“建构物”的侧面是什么样的,再使用“匿名”发言,调动人们“自主地”展览本性,忽略了公共领域个体理念的理性意义。
理性交流的目的性被“超链接”的焦虑代替。人们进入到一个又一个的“有意义”的层面,每一层面又不断地突出其意义和价值,引向另外更多的层面,人们原本专注于某一问题讨论的精力,被分散到多个层级的问题中,随着更多超链接的点开,人们越来越焦虑“是否要进入下一层链接”的选择,更糟糕的是原本所要交流的问题被“遗忘”,网民焦虑于自我的迷失,更焦虑自己交流目的和意义的迷失。
理性的公共领域变成了蛊惑人的幻象。无聊的内容在人们的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正如塞缪尔·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所展现的那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当“顶”字充斥网络,而缺少争辩和解释时,那么危险的“伪理性”就出现了:似乎人人都能够畅所欲言,协商可能实现,但人们又真正表达了什么理性的意见呢?早在上世纪20年代,沃尔特·李普曼就警告过我们 “无法觉察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也不可能进行理性的协商。人们异常兴奋地把更多模糊的片断、更多被隔离成碎片的场景看成是交流全部时,它所构成的图景使公共领域变成了蛊惑人的幻象。特伦斯·莫兰说,没有了连续性和特有的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对人类社会现实生活来讲,技术提供了两种可能,墨菲法则再次发挥起作用。
网络交流是消费社会感性的符号交换,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波德里亚认为,媒介社会充满了能指和所指的符号。这种公共领域需要信息技术与媒介文化、信息生产与信息符号交换通盘考虑的批判。网络是通过自然的接触让人们产生共感的社会媒介,点击鼠标、键盘网民往往会把自己看成是自由强大的选择者,这一“理想的”误读让人们沉溺到虚妄自大的“酒桶”,不能明晰指出网络对公共领域带来的实质影响:被蛊惑的个体丧失了理性,陷入虚拟世界,尚不能自知。理性王国由于娱乐现时虚拟的指代而坍塌。
现代诠释学代表之一的狄尔泰曾言“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这是在理性之下有序、有逻辑实现的,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亦是水到渠成的。但是当人们被虚拟的指代障眼时,激情代替了理性,快感代替了思考,激情和视觉快感必然扭曲了公共领域,理性的语境先是由于图像的大量侵入,后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而变得支离破碎,以致被摧毁,人们迷失于被扭曲的公共领域。
五、结语:技术的膨胀和个体的挣扎
由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技术的非理性膨胀。新媒介逐渐强化了日常生活媒介化,媒介生活日常化的倾向。人们若盲目乐观想象新媒介带来根本性、有意义的改变,会遮蔽公共领域对个体私人领域侵入的真相。哈贝马斯认为:“社会进化表现为三个层面,即生产力的提高,系统自主性(权力)的增强以及规范结构的变化。”[11]在技术的推动下,这三个层面实现了社会进化。但悲剧在于公共领域的挤压更多层面是对私人空间领域的侵入,具有批判力的公共领域却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这并非哈贝马斯理想的初衷。哈贝马斯理想中“有理性的市民”物化为一个个匿名的“节点”,虚拟的电子波构成了对于个体的认识,网络的极端个人主义充斥其间,不是理性的思考,而是情绪的宣泄。网络中不恰当的言语会被屏蔽,隐晦暧昧的信息却大畅其道。网络中充斥了民主的泡沫,绚丽而脆弱。
我们也看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批判力的衰落。由出版和报纸“被启蒙的大众”到电子媒介“孤独的人群”,再到网络“狂欢的草根”,哈贝马斯理想公共领域异化为“狂欢的夜总会”,并最终陷落于“蛊惑人的幻像”之中,公共领域的批判力不断地蜕化、消逝,私人空间被挤占。而其危险性在于,这种挤占是人们在欢笑中自愿接受的。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不断告知我们的,人们可能毁于自己所热爱的东西。或者我们应该警醒:人们感到痛苦的不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3]211在狂欢的夜总会里,人们希求能带来理想公共领域,但最终却是一个绚丽的幻象,缺少了理性的批判。
消费主义和娱乐化使交流的感性超越了理性。人们受制于形式为民主的“所指”,对垄断的“能指”视而不见,个体从他人的角度证实自身的存在价值,首要来源是他们所展示和消费的符号与意义。娱乐化则消解了我们向真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浸染与娱乐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3]90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否认,理性的个体在挣扎,并未因被技术异化而彻底地边缘化或放弃抵抗。康德认为,作为一种价值,个体性从未被总体性的要求而完全淹没[12],在不断的矛盾运动中,文化被更新,社会在变革,人们未放弃对自身思想独立的追求,“文化在现代从本身推动形成了那种合理性(交往行动)的结构,及马克斯·韦伯后来作为文化价值领域发现和描述的那种合理性的结构。”[13]公共领域亦有着向世界中的多种存在良性发展的可能。
恩格斯指出:“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14]
在“技术崇拜”的现实中人们需要保持理性的清醒,而不是感性的冲动,技术不能替代人性中固有的光辉属性,公共领域的衰落只是技术异化人、降低人的尊严的一个表现。人其为人不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而是因为对自身尊严的维护,对他人友善的交流和对自然的崇敬。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重要,否则诸如WIKI技术[15]就会成为人的主人,而不是仆人。
注释:
[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5。
[2]本文认为“新媒介”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它是“以全新技术实现既往未有的传播功能,或对既存媒介在传统技术与功能上实现了某种质的超越的媒介”(吴信训:《“新媒介研究”课程讲稿》,2007年。转引自:吴信训主编,《世界传媒产业评论》2008[1],6页。)不同时期指代不同的“新媒介”与使用它们所形成的新的媒体形态,作用于社会实践,形成人们认识社会现实的凭借和参照的媒介环境。本文认为媒介是工具,媒体是指运用媒介的组织机构等,两者是不同的。
[2][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43页。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想的言语情景必然意味着言说者的所言是可理解的,言说者的所述是真实的,言说者是真诚的,并且说出的话符合规范性语境,即人们理性交流的善、美、真倾向。
[3][美]尼尔·波兹曼.[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3。
[4]马克思毫无遮掩地肯定了当时新媒介——报纸——的对于个体的启蒙作用,在1843年1月日的《莱茵报》上,马克思写道:“(报纸)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共甘苦、齐爱憎。……它体现出那种本来意义上的‘独特’方针”。参见[日]佐藤卓己:《现代传媒史》,诸葛蔚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5]“老大哥”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未来独裁者的形象,小说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
[6]“电视人”是日本学者林雄二郎提出的概念,指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与在印刷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父辈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由于收看电视是在背靠沙发、面向荧屏的狭小空间中进行的,这种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弱。
[7][美]大卫·理斯曼.孤独的人群[M].朱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在大卫·理斯曼的论述中,高速公路、和郊区化、大众媒体(电视)的兴旺发达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变迁,美国人性格的变化,家庭和社区的解体趋向,人们渐渐地形成了他人导向性格导向的明显的逃避倾向,这与哈贝马斯的理性交往的理性言语情境相悖。
[8]徐翔.异化的“去中心”:审视电子乌托邦[J].南京社会科学,2010,(10)。
[9]罗艳.网络时代的多元化公共领域[J].青年记者,2007,(5)。
[10][美]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做新闻[M].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版。他用“解释社会学”的观点,解释了新闻只不过是社会建构的产品,是新闻专业人员按照日常工作惯例所完成的产品而已。
[11][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8页。
[12][美]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M].单世联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56。
[13][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论功能主义理论批判[M].洪佩郁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506。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9页。
[15]Wiki技术是Web2.0的一种典型应用,也是知识社会条件下创新Web2.0的一种典型形式,从技术原理来讲,它是可以调动最广大的网民的群体智慧参与网络创造和互动的工具。
(责任编辑 焦德武)
G206.2
A
1001-862X(2011)05-0154-006
解葳(1975-),女,山东金乡人,济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高宪春(1976-),男,山东兖州人,曲阜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新媒介与社会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