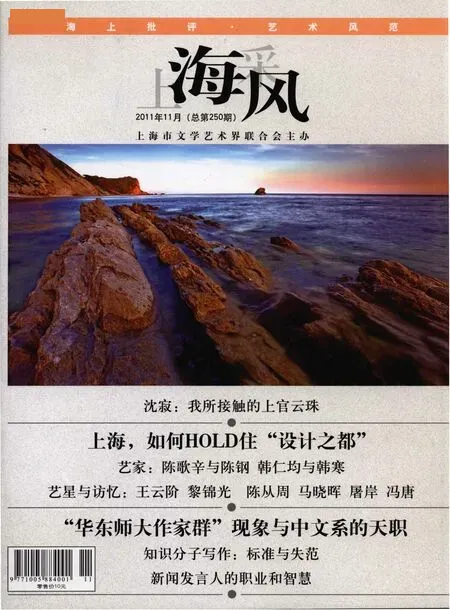表演社会与角色意识
文/郭小聪
任何时候,众声喧哗的“表演社会”也要比万马齐喑的“沉默社会”好。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什么叫“万马齐喑”,那时尽管也号召“大鸣大放”,但“那只是以群众性恐怖冒充历史性解放,把一场社会倒退的大灾难最初表现得像是一场胜利庆典”。实际上,“它既让人匍匐,又让人狂欢,既让人造反,又让人就范,差不多把每个内心里战战兢兢的人都变成了表面上兴高采烈、张牙舞爪的人”,正像我在一篇文章中感慨的。而在今天的社会生活形态中,即使一切浮躁如水蒸汽,我至少还有一份沉在水底、拒绝挥发的自由。
实际上,众声喧哗的“表演社会”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符号作用,就是它标识自由。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被四卷本《光荣与梦想》中描述的那个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的美国社会震撼过。但当书页合上时,却合成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印象:自由。不要小看了这一符号的隐喻作用——选择的自由,放纵的自由,乃至为自由的自由。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就像青春期性的荷尔蒙,而且越是来自于禁欲、压抑、单调的社会,越会有某种天然向往、孤陋寡闻和低人一等的感觉。在21世纪初拍摄的一部影片《俄罗斯音乐祭》里,俄国人也在反省为何看似无根的美国大众文化生活当年风靡了苏联一代人。同样是在前几年,当后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并照例居高临下地提及自由时,中国大学生也正是以同一符号回答了他:“先生,您今天晚上就可以到上海街头去,繁荣的商业区和你们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有更为灯红酒绿的娱乐区。”
为什么窗外熙来攘往的世俗生活会和精神自由扯上关系呢?也许是因为,任何一种斯巴达式的军营生活都满足不了人们的本能欲求。一个正常社会应该既像一个大市场,又像一个大舞台,人们在其中既互通有无,又展现人性:既相互竞争,又互相协调。而且一般说来,社会角色分得越细,相互间协作越复杂,个人的选择和表现机会越多,说明这个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融通性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活本身就像一出大戏剧,社会中每个成员本质上都像演员,有自己的特定身份和位置,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但与舞台剧不一样的地方是,衡量好演员的标准,不是看他是否有戏剧感,多么会做戏,而是看他是否有责任感,能否称职,尽好本分,也就是所谓角色意识。
不同的社会角色在人格上应当是平等的,但在社会影响力方面无疑有强弱之分。一个普通人在路边上故做惊人之语,也许不会引起社会多大的注意。但如果他是戴着学者、教授或官员的头衔在权威媒体上信口开河,人们却会把他当作某方面专家洗耳恭听,结果吞下的却是只苍蝇。所以,重要的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恰如其分地表演,忠于自己的本分,扮演好相应的社会角色。
一个社会,人们如果过于关注大庭广众之下的戏剧性效果,那就不仅导致角色的错位,也会造成生活的混乱。譬如当学者、教授像说书艺人那样在电视上短话长说,拿腔作调,打诨插科,操心电视收视率胜过专注学问,那就失去了应有的学者气质,也混淆了社会角色之间的区别,即使出名了,也难得到尊重。一位国际大公司董事长就曾讽刺说:“有些学术界的人知道商业界的人也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还会感到震惊。说这些话我并不想特别冒犯哪个人,因为商业界的人们有时发现某个教授并不是睡眼惺忪的梦想家也同样感到震惊。”
正因为如此,真正导致社会生活浅薄浮躁的,与其说是众声喧哗,不如说是喧宾夺主。如果多一些角色意识,少一些镜头意识,也就会多一些兢兢业业,少一些不伦不类。学者像个学者,老师像个老师。事实上,一个当之无愧的著名人士,不仅是被谈论的对象,也应当是被效仿的榜样。我们都知道居里夫人,她在丈夫去世后被聘为法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教授。教育部长、校长、教授们都挤在教室里等着听这位传奇妇女的第一堂课,无论她讲些什么都将是历史性的。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位全身肃服、脸色苍白的知识女性,在长达5分钟的欢迎掌声过后,第一句话是:“当我们考虑到19世纪开始以来的放射性理论引起的进步时……”没有任何繁文缛节和扯闲话,重要的是工作,这就是大学者的风范,而人们永远折服的,正是这种朴素的本色,而非任何做作。
所以,有时我想,究竟有没有一种专门的公共知识分子?那种公众意识、社会责任感,究竟是来自于在公共场合以公众名义东鳞西爪地说一些惊人之语,还是在长年探求中荣辱不惊地推动人类思想行为的变革?这的确是个问题。最怕那种像学者的政客和像政客的学者,如浮在水面上的泡沫无足轻重,却占据了显眼的位置。而伟大学者身上都有某种磐石般的沉静,他们不在乎别人的关注,只尊重事实,既不轻易定论,也不隐藏结论。当年,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在写《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已经患癌,正在化疗,伴随这部书问世的,只有商业公司的诋毁和社会的冷落。两年后她便去世了,然而她的声音注定永不寂静,因为她的研究第一次揭开了农药毒化大自然的可怕真相,开启了人类环保意识的新时代。她并没有标榜过什么,默默为自己的超前思想付出代价,但也尽了本分。
实际上,在任何时代的人生戏剧里,人们活着时都平凡,只有谢幕以后还活着才可能是真正伟大的,如司马迁、哥白尼。所以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告诫我们说,当今世界可能有英雄,但他们的光芒被名人遮蔽了,“名人之为人知是因为他们具有知名度。英雄让人看到人类天性所蕴藏的能量,名人则让人看到传媒的能量。英雄创造历史,名人制造新闻。时代造就英雄,时间却使名人不再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