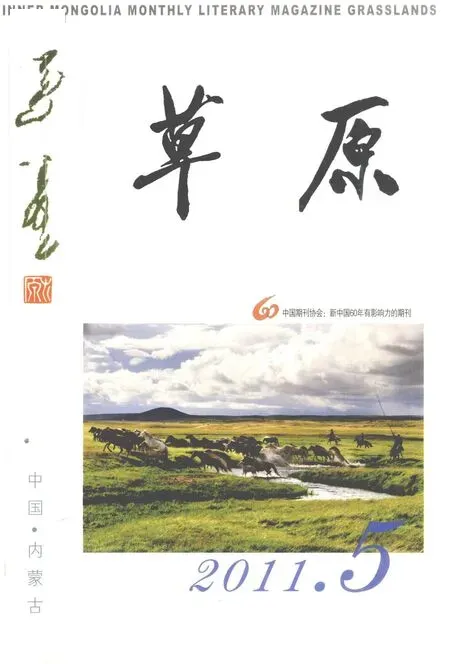我和蚊子相处的日子
□回到拉萨
我和蚊子相处的日子
□回到拉萨
一再声明,我们要和平相处,蚊子不乐意,我的一再声明就显得一厢情愿了。
蚊子趁我不注意,在我身体裸露的部分,狠狠叮上一口,唱着歌飞走了。这我不乐意,把灯打开,四处寻找叮咬我的蚊子。还真让我找到一只,它趴在墙壁上摇晃着脑袋,从它那近似夸张的表情中,我甚至能看出它得意忘形的样子。“啪”一声,我的手掌打在墙壁上,翻开手掌,它身体的某个部位粘连在墙壁上摇摇欲坠。墙壁和我手掌上,却没有丁点的血迹。这多少有点不人道,我们尊崇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道理。挂在墙上的蚊子,肯定不是吮吸我血的那只。
我上班的地方是一个叫发科岭的乡下,你如果看到一大片破旧的厂房,你就能在那里找到我。你不用找蚊子,蚊子很快就会找到你。厂区里多是大草蚊,它们个头大,飞行速度快,下手歹毒。如果把城里的蚊子比做温柔一刀,那厂区的蚊子就是土匪一个。城里的蚊子多喜欢女人和孩子,厂区的蚊子是见一个叮一个,谁也不肯放过。它们饥不择食的处事态度,和我上班的环境脱不了干系,这个厂区被人废弃了,里面荒芜得厉害,几车间锈迹斑斑的钢铁供我们几个人看守,剩下的就是满眼杂草和灌木,没有多少人愿意来。这里的蚊子远远多过这里的人,摆在它们面前的就是僧多粥少,它们长期生活在饥荒中,虽然骨架大,严重的营养不良一直困扰着它们。城里的人多蚊子少,城里的蚊子在食物面前,是挑剔的。在叮谁不叮谁的问题上,城里的蚊子比厂区的蚊子有更多的可选择性。
日子清苦的岁月里,母亲曾经问过我,你最想吃什么?我说,肉。我估计厂区里大草蚊也是这样想的。
一只蚊子悄无声息地在我身上叮了一口,叮就叮吧,最让我可恼的是,它到我耳边唱着歌盘旋了好一阵子才飞走。我不知道蚊子唱的是什么,是不是像人一样耀武扬威地说,我就咬你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我再次起床开灯,哪里还找得到它半点踪影。抓挠着身上泛起的红疱,我嘟囔着,这也太欺负人了。
蚊子不叮人是可以活下来的,比如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厂区的时候,它是靠什么活下来的,靠什么延续着子孙后代呢?估计就是草叶吧。我们来了,原本素食的它们找到了天下最好的美味,所以它们隔三差五来看看我们,叮叮我们打打牙祭。
它们也会结伴而来。情况是不是这样,大一点的蚊子对小一点的蚊子说,我说兄弟,某国企开了一个大饭店,我去过一次,那里饭菜绝对好吃,我领你去尝个鲜。大哥,那新开的大饭店宰人吗?别肉没有捞到嘴里,反搭上一条命。小的蚊子对大一点的蚊子说。我说兄弟你就放一百个心,饭店老板是我朋友,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大一点的蚊子说道。大哥,是这样呀,大哥你等着,我把小三小四小五也叫上。就这样,一群蚊子唱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歌一路结伴而来。离我很近的时候,那只冒充我朋友的大蚊子说,弟兄们,你们在这里等着,我过去给老朋友打个照面。大蚊子蹑手蹑脚飞到我身边,他落在我的腿上,胳臂上,用手摸了摸我这里,摸了摸我那里。看我没有丝毫苏醒的样子,便哼着歌子招呼它那一帮弟兄们。等我醒来的时候,那群蚊子早已旗开得胜凯旋而归。身上一片一片的红疙瘩,痒痛得让我无法再次就寝。
一个大活人让几只小小的蚊子闹得疲惫不堪,这不是多有脸面的事情。一天晚上,再次受到攻击之后,我把床拉到电扇下面,风挡扭到最大。一觉好梦睡到天明,起床后才感觉头重脚轻,随之而来的是咳嗽,抹眼睛流鼻涕。在医院,女医生像一只蚊子嘤嘤地说,严重感冒。裤子扒了下来,还没有回过神来,臀部就有了刺骨的疼痛,比蚊子叮咬的还要狠,不禁“哎哟”一声。提上裤子,旁边一个病人把头凑过来,附在我耳边说,她是个实习生。我摸了摸前天晚上蚊子叮过还残留在身上的红疙瘩想,估计这些,也是一群叫实习生的蚊子给叮咬的。医生递过来的账单让我目瞪口呆,我还能说什么,医院比蚊子厉害,只能这样讲了。与其这样,还不如就那样放开四肢让蚊子痛痛快快地叮咬。
有的蚊子是认识我的,熟人见面,总要哈哈两句。它飞到我脸边,哼哼两句,我因在梦中不理睬它,这家伙着实很生气,它找到它自以为可以弄醒我的地方,狠狠地叮上两口。见我没醒,自己一声不响地走了,甚至有点落寞。
我还碰见过不要命的蚊子。灯亮着,我坐在床上,那只不要命的蚊子极有可能饿得正常的思维也丢失了,跑过来就是一口叮在胳臂上,一巴掌拍过去,我的身上涂着我的血。想想这些没有脑子的蚊子,甚为它们悲哀,为图那口血,把小命都搭上了。
因郁闷而不眠,我会枯坐一个晚上念书,蚊子躲在我不易发觉的角落,在暗处琢磨着我,它们想搞明白,我什么时候去睡觉。时间久了,见我没有丝毫的倦意,它们的忍耐也提升到极限,它们从角落里飞出来,唱着近似愤怒的歌,在我身边飞来飞去,公开和我叫板。只要你们不叮咬我,我是不会和你们计较的。就这样对峙着,有时我会在翻书页的时候偷看它们两眼,它们也在看我。为了避免它们采取强硬的手段接近,我会在某一个时刻让身子突然抖动一下,这个方法是我从一头牛身上学到的,对付蚊虫,牛尾巴触及不到的地方,牛会让身体忽然抽搐几下,便于把它们吓走。如此反复,蚊子唱歌的声音越来越小了,甚至有点跑调,这可能是源于气力的不足。当窗外的一抹白光挨近窗台时,疲惫的蚊子带着满脸怨恨一声不吭地飞走了。这是不是像一个小偷,惦记某件东西惦记了一个晚上,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那是多么沮丧的事情。我有时候会感觉到很对不起它们,好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人家毕竟陪了我一夜,毕竟唱了一个晚上的歌儿给我听,走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有给予它们。
蚊子折腾了一个晚上,什么也没有得到,可以说是不得志。蚊子饿着肚子走在回家的路上,会不会想,会不会抱怨,这个晚上的运气如此差劲,这一生的命运如此不佳,这仅仅是蚊子的事情吗?
记得有一次我用风油精把身子整个涂抹了一遍,一个晚上,我和蚊子相安无事。它们只是在附近飞来飞去,不再来靠近我。又一个晚上,我如法炮制,早上起来,身上还是有几处被叮咬的痕迹。由此我想到了习惯。
我会抽出一些时间来,仔细观察一只蚊子的尸体。看那薄薄的翅膀,窄窄的身体,瘦瘦的脚,细细的嘴,我纳闷的是,我越来越不会红着的脸庞,它怎么轻而易举的就能刺破呢?这只蚊子的确不是我打死的,它的尸体很完整,没有一点被人伤害过的痕迹。它死了,静静地躺在灯光下,我揣摩它因何而死,看到它还年轻的样子,我否定它是因为年迈而亡。那它到底是怎么死掉的呢?它的腹部,还有一点针尖的红,那有可能是我昨天的血。晚上读一本书的时候,我用书中的故事推测这只蚊子的死,极有可能是正确,也是最合理的解释吧!书中是这样说的,一个长期在化工厂做工的人,被眼镜蛇咬了一口,做工的平安无事,一命呜呼的竟然是眼镜蛇。故事读完,我不寒而栗,我已经确定,我是一个有毒的人了。
一只附在我身上的蚊子,还没有来得及做些什么,就被我拍死了,这在蚊子界,应该是一种悲剧。还有更多的蚊子不知道我把它们中的一个干掉了,它们还在前赴后继着,悲剧还会继续上演,关于食物,关于血肉,有着太多无法抑制的诱惑。
哑巴蚊子咬死人。哑巴蚊子应该算是城府很深的蚊子吧!他们颇有心计,收获的也颇丰。我就被这样的蚊子叮咬过,没有一点声音地叮你一口,没有一点声音地离去。等到你疼痛时,蓦然回首,它在哪里?你甚至不知道它是叫张三还是叫李四,更多的时候,是你守着疼痛,望天长叹。
蚊子得不了手,离开的时候也会怅然,也会嘤嘤哭泣,也很想找一个蚊子把满腹委屈诉说给它听,后来想想就算了,免得别人耻笑。
我发现自己脚面上的两个疱是紧贴着的,从疱的大小和红肿的程度来看,这绝对是两只蚊子干的事情。哦,我笑了,叫张三的蚊子和叫李四的蚊子打赌,看谁叮咬得更大一点,这样紧紧地挨着,只是便于比较胜负罢了。
我们惧怕黑夜,在黑夜里我们会做噩梦,会干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蚊子正好和我们相反,蚊子惧怕光明,在光明中蚊子会做噩梦。背着光去做一些事情,总是不光彩的,提不到桌面上。蚊子可不这样认为,它们知道它们该做什么事情,它们在黑暗中做的事情就如同我们在光明中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它们没有一点觉得自己是不齿的,所以它们唱着调子做这些事情。在它们眼里,我们跟一棵草,一根灌木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走动的时候,那只不过是被风吹的结果,只不过我们比草比灌木被风吹得更快一些。
下雨的夜晚,听到屋子里一团又一团的厮杀声,知道自己被蚊子重重包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牺牲,我抱着衣服以逃窜的方式冲出突围,在车上待一宿。车上也是有蚊子的,也就是那么几只,力量毕竟单薄了很多。我甚至怀疑,它们都是我上班的时候从城内带到这里的蚊子,它们斯文得很,宁愿饿着,也不愿吮吸我没有多少营养的血。它们最大的愿望是盼着我明天早点下班,早早地回到城市去,它们好早早地找到那些丰满的女人和孩子。
下班回去的时候,厂区的大草蚊趁我不注意,也会搭个顺风车到城里去。城里的蚊子面对大块头的蚊子,那一具蝼蛄的身材,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感慨。大块头的蚊子看到那么多行走着的,熟睡着的血肉,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变得诚惶诚恐呢?是不是也有一个乡下人第一次来到城市中的那种困窘呢?面对这么多食物,是不是茫然得不知从何下口?默默看了几日,总算摸索到一些城市生活的习性,最起码要体面一点,不再大嗓门唱歌,叮人也要含蓄一点。吃饱了,喝足了,抽空还要去自来水的地方洗个澡。等自己感觉自己更像城市蚊子的时候,那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谁家阴暗的角落里美美地睡上一觉。睡觉醒来,还可以找一个城市的蚊子侃侃大山,聊聊乡下蚊子的生活。大草蚊对我心存感激,同时也在一次一次的幻想着,我能把它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捎来,在城里安一个家。时间久了,大草蚊也思乡,城市毕竟是别人的城市,远没有故乡那么亲切。大草蚊也想飞回去看看生它养它的那片土地,但它太小了,它甚至不能翻过那块最小的山梁。
抓到一只还算壮实的大草蚊,装进透明的玻璃瓶带给儿子。每次我们吃饭的时候,儿子问我,给蚊子吃什么。我一脸茫然。想了想说,干脆把它放出来吧。儿子和妻子都反对。
和朋友说起厂区蚊子的事情,朋友坚持让我去买蚊香。我去了。生产蚊香的厂家还算老实,在纸盒的封面上写着四氟甲醚菊脂含量:0.02%。这应该是在国家标准范围内吧?这种化学制品,毕竟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于我是,对于蚊子更是。再次说起那眼镜蛇被人毒死的故事。如果蚊子进化到或者习惯到蚊香对它没有一点用,那点蚊香的我们是不是错误呢?对于蚊香,我是要放弃的。
朋友再次给我推荐了电蚊香,在商店看上一款,问了问,三十五块钱,够我一天工资了。准备付钱的时候,又想到一个小国家,国民的生活目前还是贫苦潦倒的状态,却不惜人民血汗,不惜重金购买某大国先进的武器,去攻打比自己还要小的国家,这肯定是不道德的。再说,让蚊子惨遭那样电烙的酷刑,也于心不忍。
每年秋天,当霜降到来的时候,蚊子再也找不到了,那些叮过我的蚊子,给我唱过歌的蚊子,喝过我血的蚊子,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寂寥夜晚的蚊子,它们都去了哪里?我很细心地翻过它们好像待过的地方,没有找到它们,也没有找到它们的尸体。也许,它们都被一场寒风吹走了,吹到一个我看不到的坟墓之中。没有人能改变冬天的到来,也没有人能改变苍老,况且是一只小小的蚊子。
〔责任编辑 阿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