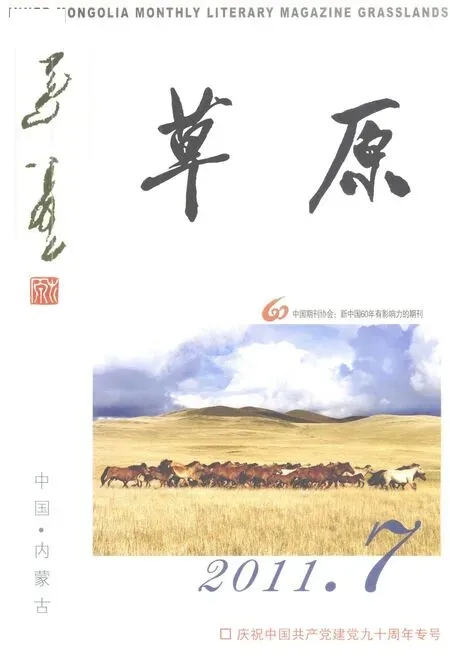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激情及其表达方式——评蒙古族作家布仁巴雅尔的报告文学集《创业史诗》
□娜弥雅(蒙古族)
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激情及其表达方式
——评蒙古族作家布仁巴雅尔的报告文学集《创业史诗》
□娜弥雅(蒙古族)
在蒙古文学领域中,报告文学属“中间性”文体,或游离于文学与新闻之间,或栖息在散文的屋檐下,一直缺少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是,一些公正的文学史家,把这个文体以它模糊的身份写进了文学史。因为,一直有人热衷于这个文体,默默地耕耘着这片热土。布仁巴雅尔,一个用母语写作的蒙古族报告文学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创作,至今已经出版了八部报告文学集。这个数字令人惊叹,也让人情不自禁地思索:是什么样的心灵承载让他倾注如此沉重的偏爱,使这个“中间性”文体走向心灵的指归。
一、“五十年代”的激情
生机勃勃的生活永远都散发着朝气方新的热情,而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奋不顾身地投入到生活,用真情拥抱生活,创造了一个时代。然而,经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洗劫之后,人们那种纯真的热情与信念。开始动摇,表现出一种迷茫和困惑。尤其,被市场经济的大浪冲刷之后,那种天真浪漫、积极向上、虔心向学的精神开始低落。这种状况反映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揭露意识稍强而赞美激情不足,感伤情怀高而浪漫气氛不足。而且这种情况更趋普遍化。然而,同一时代的布仁巴雅尔的报告文学就有所不同,他从正面歌颂生活,反映生活中的真、善、美,用饱满的激情讴歌了和谐社会、英雄人物、事业成就等富有政治色彩的重大主题。这种充满浪漫激情的报告文学作品与富有悲剧精神的诗歌、小说,一同奏响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交响乐。
布仁巴雅尔的情感世界,应属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但他的视角并非属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热情,充满了理想,富有超现实主义色彩,而布仁巴雅尔则立足于现实,从现实生活中选取题材,从时代精神中提炼主题,歌颂了真人、真事,有着浓厚的现实主义风格。
通常,纯文学创作者也为新的创作素材而兴奋、冲动。但他们的冲动一般都隐藏在内心,不会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中。可是报告文学家就不同,当他们得到某种创作信息时,他们立刻把冲动化为实际行动,会投入到采访与实证调研的活动中。布仁巴雅尔为了写出他的八部作品集,经历过多少次的采访活动,旁人无法得知,就连他自己恐怕也无法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他所写的具体的人和事情以及与这些人和事件相关的时间、地点、名词、数据等使人不得不惊叹他那种新闻工作者身上独有的创作激情、专业知识和辛勤的劳动。从收入《创业史诗》里的二十四篇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为搜集材料,走遍了科尔沁的库伦旗、奈曼旗、扎鲁特旗等诸多旗县,足迹遍布霍林河、呼和浩特、北京等城市。从他作品的字里行间,也能感受到采访工作的艰辛。例如,他为了采访草原研究专家——温都苏,不停地打电话,打了三天才联系到对方。为了采访特木尔经理,等了半年之久,最终才见到“日夜思念”的对方,并写出了《天骄经理》。这种态度,只有在新闻工作者身上才能感受到;这种创作过程,也是一般的文学写作者无法体验到的。
布仁巴雅尔作品中的人物,正如作者本人一样,也充满了生活的热情和生命的激情。可以说作者的激情渗透于作品中的每个英雄人物,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也投射着作者的激情,在他们相互激励的过程中共同谱写了新时代的赞歌。
二、蒙古精神
《创业史诗》由二十四篇报告文学组成,长达三百五十六页。作者把这样一个长篇大作刊布于世,试图表达什么样的精神,树立什么样的形象呢?根据本人的观察,其作品集中表现了一种蒙古精神,树立了新时代的蒙古英雄。也正是这种蒙古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英雄形象,成为这部作品的“生命之韵”(诗人阿尔泰之语)。
蒙古诗歌和小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解冻”以来就开始表现 “腾格里崇拜意识”,进入了一个怀念成吉思汗、寻找血统的虚无的年代。这里所说的虚无是那种“无英雄时代”的彷徨和焦虑的心情。但是,在报告文学家笔下的生活依然充满了阳光,英雄人物接踵而至,这也算是对读者的一种安慰吧。布仁巴雅尔,以报告文学家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生活中许多绚烂的事件,以一种永不泯灭的信念和非凡的激情发现了众多鲜活的英雄人物,塑造了“无英雄时代”的英雄形象,把传统文学的英雄主义精神延伸到我们这个时代。
1.崇尚荣誉精神
在黑格尔看来,荣誉主要是指“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因此,“荣誉的标准不是主体实际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他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由于,黑格尔认为荣誉主要是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无关,为此,他说 “荣誉这个母题在希腊古典艺术里是见不到”,只有到了浪漫主义时代才有了荣誉观。
与西方文学不同,在蒙古文学中很早就有了对荣誉的看法,而且已成为影响文学人物性格和行动的构成因素。《蒙古秘史》中曾记载,乃蛮部落的塔阳罕向成吉思汗挑战,说要夺取他的弓箭时,别勒古台那颜说道:“身为七尺蒙古汉/当视弓箭如生命/如让他人夺之去/活在人世有何用?双手紧握弓和箭/头下枕着弓箭包/身尸傲骨抛原野/热血男儿何所惧”(阿斯钢、特·官布扎布译)。别勒古台那颜的一番话,体现了蒙古人宁可战死、不可受辱的精神。《江格尔》中力气无比的萨布尔将士离开江格尔那颜并不是为了实际的利益,而是他的自尊心和荣誉受到了伤害。《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中,两匹骏马也是感到自己被可汗失宠而奔他乡而去。
不仅在文学里,在蒙古人的俗语、谚语里就流传下来许多有关荣誉方面的词语。比如,“宁可断骨不可败名”、“雁飞出声,人活留名”、“名字父母给,名誉自己获”等等。这些言语非常简练地表达了蒙古人极其珍惜和推崇荣誉的心理。
布仁巴雅尔的《创业史诗》报告文学集里塑造的英雄主人公,都有着“荣誉高于一切”的价值取向,而且,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内在动力。《虔心奋斗》中的农乃扎布,就是一个崇尚荣誉的人,作者写道:“超负荷的艰辛研究,使他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让那些有愧于男儿之名的人望而却步。然而,内心深处铭刻着振兴民族事业的他,依然为搜集标本、为科研工作马不停蹄地勇往直前……”农乃扎布不怕艰辛,但他怕玷污名誉。当他出国回来后,听到别人诋毁他“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论文,被批得一塌糊涂”时,内心深处翻起了波浪,“仿佛失去了什么珍贵的东西,忐忑不安地度过了好几天”。作者笔下的其他主人公都像农乃扎布,把荣誉当做自己的生命。从这里看到,作者也非常注重荣誉,将其作为衡量一个英雄人物的标准。例如,作者对《胡尔(琴)神》中的吴云龙的评价是“吴云龙的大名传遍世界,吴云龙的胡尔流芳五洲”。布仁巴雅尔这种把崇尚荣誉的思想当做选择主人公、评价主人公的标准,也可以说是蒙古人的心理特点、民族特点。
2.“虔心”或忠贞精神
主体的荣誉感可变成一种动力,但将其变为现实,必须要“虔心奋斗”。这里所说的虔心,可理解为黑格尔《美学》中的“忠贞”。当然,黑格尔所说的忠贞,含义明确,是对主子的服役。但黑格尔对“忠贞”的解释,给我们以启发,而且,他对“忠贞”的理解,符合蒙古人传统意识里“善良”、“忠诚”的价值观。甚至,我们把其他民族对蒙古人的一种特殊称呼—— “老蒙古”,也可以看作是对蒙古人的善良、忠厚、朴实品德的一种反面的肯定。
生活中的善良和忠厚,自然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对事业的虔诚心,也可以包括在“忠贞”的概念中。布仁巴雅尔所选择的主人公,有着共同的心理特点,也就是都有着一颗虔心。《胡尔神》中的吴云龙,在常人眼里表现得疯疯癫癫,有些不正常。但他的疯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疯癫,是对事业绝对忠贞的表现,是一种极端的陶醉状态,是一种虔诚心的外露。
黑格尔认为,主体在服役时间的长短上有选择的权利。但布仁巴雅尔笔下的主人公,好像对事业的服役时间是无限的。他们的虔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是减弱而是增强;遇到了艰难,不是摇摆而是更加从容、坚强。这是人们所向往的忠贞精神,也是《创业史诗》里英雄们的心理特点。布仁巴雅尔的报告文学里充满了这种精神,这也正是本作品集的与众不同之处。
3.艺术视角
报告文学不仅属于新闻,同时也属于文学。因此,报告文学要求作家对客观材料进行艺术性处理。通读布仁巴雅尔《创业史诗》,发现作者不但看重采访和搜集材料的过程,也非常注意艺术加工的过程。作者在一篇作品里交代了他的写作过程:“一年半,五百五十多天,他的形象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一天也没离开过。但从庚午年春到辛未年秋,我都没有动过笔,甚至怕动笔。”如果说报告文学仅仅是对事实的报道,对材料的整理,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用“五百五十多天”去思索。
报告文学,正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而是文学化的报道,所以,比起一般的报道有更高的艺术标准。
(1)时间的艺术化
对于报告文学来讲,时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报告文学可以说是事件的记录,而事件是在特定时间内展开和延伸的。所以,时间的安排对于报告文学至关重要。但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只有一个方向,即从开始到发展,再到高潮,结束。事件所占用的时间也是固定的。与之相比,艺术的时间和叙述的时间是全方位的,有选择性的,而且伸缩自如。因此,这里的时间是艺术的、是属于“第二自然”的。报告文学的任务,不仅是对事实进行报道,还要把事实进行艺术化。所以不能照搬事实,而是艺术地安排行为和事件,将这些因素升华到情节的高度。《创业史诗》,一方面,严格遵守新闻的真实性、时间的不可改变性,体现了新闻文体的特点;另一方面,作者也没有忘记报告文学的文学使命。例如,《闯过鬼门关的人》里,写乌塔白拉做手术时,作者没有选择做手术的 “九月二十五日”,而是选择和强调了“九月五日”、“九月二十四日晚”、“七天后”等时间点,延长了主人公心理活动的时间以及情节变化的时间,把主人公描写成既是生活的、又是艺术的“英雄”,通过作者的深层加工,增强了艺术效果。《主人的权利》一文中,作者也赋予某些时间以特殊的意义,通过对“清晨”、“北京时间七点半”、“三更”、“鸡鸣”等时间的延长和强调,艺术地表现了情节的转折点、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
(2)场景的情感化
报告文学,以事实为第一性,因此,它留给作者的艺术空间是有限的。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如何构建艺术空间和情感空间,如何达到事实性和艺术性兼顾的高度,这将是一种考验报告文学家艺术内力的尺码。布仁巴雅尔,通常用强化批评、渲染场景、重构时间等方法来表现文学性。其中,借用电影和小说中的场景描写法,生动地表现人物和事件,是一种有效的尝试和大胆探求。
所谓场景,指的是一个或多个人在特定的时间里,占用特定的空间进行的活动。场景是再现事件、展开矛盾、塑造人物的重要舞台,因此,对文学作品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布仁巴雅尔的报告文学中我们很容易察觉到,作者利用场景的表现力,为报告文学增添了艺术的光彩。例如,描写乌塔白拉(《闯过鬼门关的人》)书记时,首先从主人公做完手术返回家乡的场景开始,然后自然地转换到主人公从家乡出来时的情景,缓缓拉开记忆的帷幕。这时、现在和过去相交错,场景和情感相交融,开始发挥艺术的感染力。当主人公回忆手术时的情景,作者没有安排手术中的痛苦场面,而是着力描写了主人公对亲人交代遗嘱的缠绵画面。这种安排不仅具有揭示主人公内心世界,塑造人物性格的功效,更有感染读者心灵的动力。等到主人公从回忆中回到现实生活时,作者又安排了一场感人的场面,仔细描写了全村男女老少,来迎接乌塔白拉书记的场面。此时,作者自身也融入到作品之中,情不自禁地喊出:“看啊!进入村子的岔路口,站满了迎接的人群。”表露了他当时的惊讶心理。接下来的场面里,泪水和言语相交融,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情感化场面”,即刻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正因为作者如此地将一个一个场景,细腻地串联起来,诱发读者的好奇心,才达到了用直叙、直议手法无法实现的艺术高度。
在稍后的段落中,作者还精心描写了乌塔白拉伺候患病母亲的细节,生动地再现了为了给学校买砖时用摩托车去辽宁,碰到大雨“连坏带爆,连滑带倒,连推带拉,拼命地前进”的情景,也特意描写了被村中误解他的人打烂玻璃的尴尬的局面和跟老婆闹别扭的戏剧化的事件,用特写镜头记录了一九九八年的抗洪抢险斗争中用身体挡住洪水的感人故事。这些活生生的生活场面,身临其境的画面,与空洞的事件重述,扁平的先进人物形象有着本质的区别。尤其,用场景描写法把乌塔白拉的人格魅力和平常心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展现了报告文学既能表现政治性、也能表现人性和文学性、新闻和文学相交融的文体特征。布仁巴雅尔作品中这种人性化、情感化的场景很多,它告诉我们每一位读者,所谓的创业者、英雄人物也是凡夫俗子,也是我们尘世里的一员。这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一个亮点,也是布仁巴雅尔报告文学的魅力之所在。他的这种人道主义关怀,人性化的思维方式,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温柔的感情色彩。例如,当描写日本孤儿乌云的感人事迹时,作者抓住了养育人的“良心”和不忘养育之恩的“良心”,对他们这种平常人的平常心理进行了剖析,赞美了这种高尚美德。而徐福铎的《他的中国心》,则从政治的立场,将这个题材提高到思想的高度,热情歌颂了乌云的爱国之心。
4.感悟性议论与暧昧的批评
议论是报告文学的特色之一。读者从题目开始,一字一句地仔细阅读报告文学,是想知道作家在字里行间、情节安排,人物刻画时所抒发、流露出的独特观点和立场以及作者的思想锋芒和论战能力。人们无法忘怀夏衍的《包身工》,是因为它揭露了现象背后的真相,并鞭挞了殖民者的残暴和恶劣的行为。即使是相隔数十年,读来仍有痛快淋漓之感。
布仁巴雅尔的报告文学也不乏议论和政论 ,说明作者深明报告文学的写作规范。例如,在《闯过鬼门关的人》里,描写乌塔白拉背着他的养母,四处寻医时,作者发出了“是啊,只有爱母亲的人才会爱故乡,只有爱自己的故乡才会爱民族,只有爱自己民族的人才会爱祖国,只有爱自己的祖国才会爱事业,选择这样的领导,村子和嘎查能不富裕吗?”的感慨和议论。当然,这可能不是布仁巴雅尔所创造的名言,但布仁巴雅尔不仅很好地利用了它、拓展了它,更主要的是将它引用到作品中之后,达到了比较理想的艺术效果。《胡尔神》中,作者在记叙吴云龙事迹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表达自己的感悟:“人的价值并不在于从社会索取到什么,而是在于给社会、国家和民族创造和增添了什么。”作者从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感悟到了人生的哲理,把它提炼成评论的语言,与叙述融会在一起,献给了读者。美中不足的是,布仁巴雅尔的评论略显片面和单调。一味地歌颂英雄、肯定业绩,这样,会使读者对作品产生疑虑,也使英雄人物显得有些扁平。《创业史诗》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是坚定不移,视时间如命,爱民族、爱国家、品德高尚的优秀人士。相比之下,作品中轻视了人物性格特点以及只有他(她)才有的个性化的一面。作者的议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起到了加强主人公的社会化、模式化特点的作用,从而削弱了英雄人物复杂、丰富的性格特征。也许从读者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可能略显突出。
当然,我们正处在英雄辈出、激情演绎的年代,所以,尽情歌颂是报告文学的时代使命。同时我们也处在社会转型、思想急变的时期,因此,介入生活的矛盾,发现社会的复杂性,揭露各种社会问题,启迪读者也是今日报告文学的历史使命。布仁巴雅尔的作品中自然也有否定,但比起大胆的歌颂,有些暧昧和犹豫不决。因为在他的作品里那些反面人物既没有姓名,也没有可辨认的特征,只是以“某些人”、“有的人”的面貌出现,因此,很难把它看成是报告文学所要表达的事实。
〔责任编辑 阿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