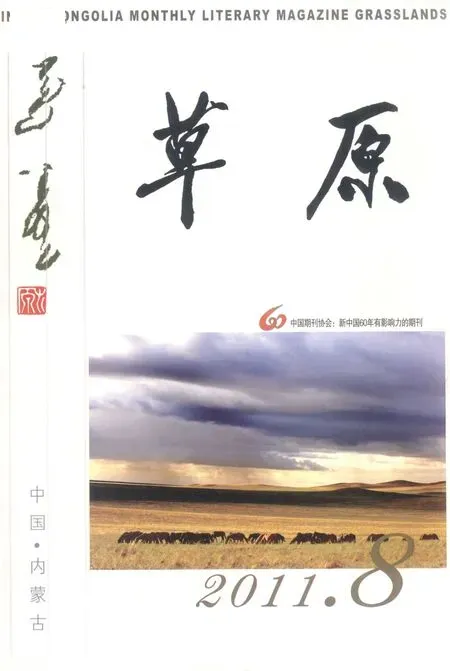骨头里的灯盏
石榴石
身体里的水,是用来洗涤品行和思想的。
从一座山的胎釉,透彻出你士为知己者而裸的词藻和胸襟;从一株铁树捧出鹅黄,倒卵出你的一瓢豆捞在磨盘里涌出乳汁,一串烟花在月夜盛开蒲葵和崩裂。
从一只壶的煎熬和沸声,交出一杯新茶浸润的包裹体和色散,从一棵枣树把血液输送到枝头和叶下,交出一颗荔枝的白和爽滑,交出一粒核桃种子的弯曲和蜗居。
从变质岩的激情,交出油脂、青瓷、酒糟和一呼百应的悬崖绝壁,交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交出蚕的丝和籽粒,小草的露珠和浆果,交出春燕的衔泥以及九曲回肠的纯度和折光率。
从铁、铝、锰、铬的剁椒里,交出菱形十二面的微辣,四角三八面的麦芒,从一月诞生石涵盖的整个光谱,交出一组方块字的影印,一本线装书的直抵内心,交出纸张背后的针眼,笔尖头顶的碳泉。
从历史的盅处,交出天光和肌肤相亲,交出冲积砂矿里一寸一寸的海拔和不会喊疼的螺痕,交出子夜星辰闪烁和没有杂质的体贴入微,交出一条干河床的饱经空满,一朵蒲公英在风口寻找故乡,一坛陈酿涨红着脸捂紧生活的瓦盖。
从载舟覆舟的龙船和排浪,从窗玻璃的挡风亮骨和等轴晶系,交出一支残烛隐秘的浓和流,一队候鸟和季风消失在云端,交出前一秒还穿在身上的蝉衣和蛙鼓,交出蛛网最后一分钟的疲惫和捐躯。
是的,无论厄运、磨难与多舛,而那些储存在事物内部的自强不息,至始至终都主宰着自己的信念和林莽。
蛋白石
一滴油的水面,红、橙、蓝、绿变彩成浮在涟漪之上的豆蔻莼叶;一枚蛋的锦葵,像树脂的冻涂满珐琅,像粘稠的液釉入瓷质。
要需要多少点滴,钟乳石才能在山的体内长成一只笋,一根华表,一尊聚沙成塔的塑像;要动用多少湿,你的桃花才通体透亮,红杏出浴。
一股股乳汁,在最柔软时吮入婴唇;一抹抹荧光,用无数个瞬间将闪电的胚芽和月影流苏植入胸怀。
想起,风生水起中收紧骨头的礁石和帆,深埋于泥层之下的铜鼎和带红土的皮子,想起火山岩夹缝里吸附的矿胍和根茎,想起那些用一生的累来填充生活的人和贝。
想起块状的白,多孔的黑,球粒的褐,结核的黄,想起雕刻的矽,研磨的硅,水合物的凝胶和茧纹,想起五百万年前的目光和波长,脱水后变为石髓的色游,想起雨停时升腾的虹,晴夜里镂空天纸的流星。
想起干涸土地上龟裂的渴,容易受伤的嫩和彤,想起一颗钻石切割的剪影人生,一张马赛克掩盖的涉世沧桑,一炉煤,在火焰中剥脱身上的黑与黎明共拂晓。
内心充满水分的人,在天穹是一朵云的风景,在池底做一只藕的躬耕,在架下,一串串熟葡萄诱惑舌尖上的鲜甜与唾盐,在晒场,谷物和籽粒挤出身体里所有的晨钟暮鼓,排列成多层次的温柔和丰满。
允诺说:夹阴在岁月深处的非晶光束,只是为了在下一个季节,与你凝视和志同道远。
紫金石
一块烧红的铁,一叶呈现酱色的肝和肺腑,一只蛹用朱砂体液染透那一排架下的葡萄和藤萝花瓣。
血,凝结的檀处,有钙的叩之有声;紫,咬唇的境界,物我两忘嚼字日月昭华和淮水灵气。
一些相识的月白,花斑,鱼子红和蟹壳青,绷紧岁月的浓,淡,干,湿;一些情愫的金黄,碧玉和黑子,像蚕纹在飘渺,在虚若,如日晕在痴迷,在行云流水。
裸露一朵石芙蓉的出水要用去七千万年光景,一方鸡血石的怀胎需要百吨的暗红和聚而不散;裸露一千株玫瑰才能领悟一片叶的枫红和赭重,一万句的誓言不及一颗赤诚之心溢出的罂粟和熔烛。
裸露那些天成的石筋和格,圆眼和瞳子,是他们荟萃了形神兼备的髓滴和含情的砚,是他们让人忘却了尘世的纷争和烦恼,重新找回了灵魂的静和切肤之亲。
裸露那些无杂质的近和动感,那些不用打磨也会发光发亮的包青,蒸粒黄,火捺和满堂彩;裸露海相沉积,山体塌裂时握紧双手,辅车相将;裸露天然去雕饰,厚重存精粹。
一块石,一块苍鹰留下的关节,一块有啼音的碎鼎,一块存封在咽喉将要探出枝叶的莲藕,一块手拭如膏,绘墨如油的羊脂;一块石,一块被挤压被鞭策的脆,一块可以触摸的情感水润,一块贯通生命的意蕴和印痕。
紫砂壶说:喘息在身子里的紫,只是为了给你的沏增加一些暖你的时间,只是为了给你的品味多一些清醇和不同凡响。
陨 石
天庭溪,宇宙脉,生命源,灵魂的家书和蝌蚪,每一寸肌肤都扣满千帆百舸和义无反顾,每一次走近都付诸生死琴弦和三千丈白发。
回家,那个游子要回家,即使日子全部漆黑,也要点燃身躯,照亮云雀飞翔,即使路途极度遥远,也要在一条闪电之前抵达。
回家,在路的尽头,时光的沙漏,在竭尽全力后裸露一颗给你的胆识和滚烫心灵,在倾泻一切顾虑后,掷下一节力透纸背的椎骨和诗韵。
回家,带着天成的精诚所至和日积月累的褐,带着被火焰追赶的风筝和磷,带着一队候鸟每秒二十公里的天穹,一盏灯几千度的乾坤,带着一块铁捧出体液,一支镍汗颜髓汁和归心似箭,带着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和一窝采满花粉的蜜蜂,带着思念的重量、图解和标本,带着磨掉梭角,触景升腾的绸缪和天马行空。
回家,情愿淹没在你的湖泊、雪地和海洋,情愿将我的森林化为灰烬和天坑,情愿有浑圆的熔壳,皲裂的熔沟和不留遗憾的气印,情愿丢弃所有行囊,只剩下球粒的落地铿锵,脚踝的深浅凹陷和古铜色的彻夜无眠。
一种超脱,一种核的下沉,有砝码的形,命锁的莲蓬和血痂;一种醒目,一种凝的固状,火柴用头颅擦亮瞬间,雨燕驮着钟摆穿越夜的地支和玄学。
当我们的家庭遭遇变故,健康步入疾病,当财产流失或意外灾祸,我们是否会学习那些破碎了身子,还在努力飞行的陨石?我们是否会比照那些远离故土,还在异乡默默深埋,承受辛劳的打工者?
黎明说:记住那些划破黑暗的荧和鱼肚白,是他们付出了一生的闪烁和夸父逐日,是他们心存硅,酸,盐和温暖,让我们的早晨充满阳光和物质,充满进化和依恋。
东陵石
苏醒的葳蕤,精神的荷,洗去尘埃的切肤之感,会说话的如数家珍和体悟。
一抹绿,风吹草低中染色一片相互融洽的安抚和共勉;一抹蓝,鸽哨带着五月的飘云按时回家;一抹紫,一支笋脱去胎衣,一只蚕作茧自缚,一树枫撑开所有肺腑和身体里的酒。
在热液充填中,一些婵娟的一言一行,定向排列成欣欣向荣和不会退色的翠;一些铬云母的纤维,裸露出黄铁的凝炼和约定的润。
石头里的桑椹,用肉体长出嫩和闪闪发亮的砂金,长出矿床里的北斗七星和千年不熄的焰,长出怀春水湄,寸步相守的潮汐和浪尖上的雷鸣,长出可遇又可求的晶质和脱胎换骨的砥砺。
是的,蓄满风霜的苔藓,即使在季节的沟壑和缝隙,还会在岁月的坚硬处,留下生活的补丁和厚,留下指尖的爬痕和由近及远。
有谁能在时光的迁徙中守住一诺千金和把心都等透的一泓清泉;有谁让豌豆荚的蕾芯牵挂粘稠,一粒米的乳房收藏晨曦和月光;有谁在真诚冷却后还能用石英作纸,用色泽作笔墨,写下情有独钟,写下脆的诗歌和霓的杯水一滴。
为一片叶活着的人,心里一定镶嵌着阳光的鳞片和一个世纪的风起云涌;为一生而发亮的人,芦苇在滩涂排成方阵,碑站在路的尽头,傍晚的萤,点燃熔烛飞翔。
煤说:生命的深处,唯有一种对应心轮的暖可以留下,可以高贵不朽,可以弥久愈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