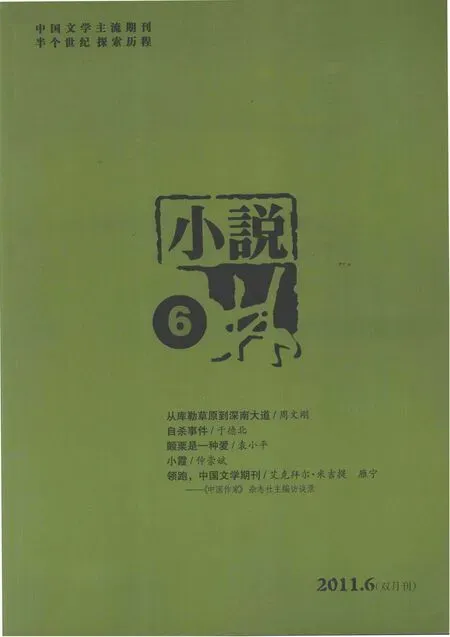分手在左岸
■陈 敏
丹江河畔,我们相约左岸。左岸是州城一家咖啡屋的名字,听上去有咖啡的味道,带着一股大洋彼岸的气息。
她就坐在我的对面,离我只有咫尺之距,沉默时,我就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可她口含珠似的嘴巴一直喋喋不休,一刻都没停过,让我只能把听觉和视觉都集中在她一张一合的嘴巴上,很难感觉到她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交融有时需要沉默。这个她不懂。她的声音很大,放肆地说着粗鲁的话,并夹杂着一些冰冷的医学术语,诸如“植入”、“支架”、男性功能委靡不举之根源,好像有意让咖啡桌上的气氛变得肮脏,这与她沉淀多年的文静与优雅成了反比。
我没有制止她,放任让她说,也佯装听着,一边努力地想着她的好。
曾几何时,她真的很生动。我对她所有的好感缘于她那张娇美的脸和魔鬼一般的身材。那一切与我的好色有关。我从小就很好色,襁褓中就喜欢身穿亮丽花色的女子,十五岁那年忽然有了感觉,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娶个最美的女子做我的新娘,也就从那时起,我的眼睛像台扫射器,无论走在镇子上还是某个巷子里,我从不错过身边走过的任何一位美女。她是唯一被我扫进眼中的女子,又是我的学姐,比我大一岁。她长得异常美丽,用得上惊艳逼人这个词来形容。我已经把她拥有了一次又一次,但是思想上的。至此,在她生日的那个夜晚,我徘徊到一个花店前,瞥了下四周,确认没有熟人的状态下,小偷一样溜进去,买下一束玫瑰,简直像光顾夫妻用品店一样心虚。
我把那朵玫瑰藏在内衣里,在她宿舍前徘徊了三圈儿,也没勇气喊她出来,直到她房间黑了下来,才像做贼一样把它别在她的门上。那朵玫瑰已被我胸部渗出的热汗折腾得失去了容颜。
也是奇怪,自那以后,我不找她,她也不理我了。我们俩的感情像那朵花,一夜过后就谢了。这让我大为懊恼,有种赔了夫人又折花的感觉。
约莫几年之后,她和我的交往开始由“冬眠”期转入“复苏”状态。她突然变天,邀我到州城她的老家和她见面。我犹豫了一刻钟之后,就做出了约会的决定。
美丽的女子就像绣花房里的花线一样,一开始可能会缠住你的腿,迷住你的心,等你怀揣一颗热腾腾的心,傻乎乎地走近她时,她又像孙猴子,抹脸一变,变成了一个凶巴巴的老婆子。隔山跨河前去赴约,被她玉指牵引去的约会地不是我预想的天仙台、十里长堤,而竟然是一片长满了松柏的墓园。我的心在一座墓碑前突然倒下、死了。她高扬的脸上洋溢出自以为是的得意:这是烈士墓地!没有鬼,有鬼,鬼也是红的鬼。
我没有再去听她更多的说教,跌跌撞撞跑下山岗,逃离一般离开了她以及那个让我本来就没有任何好感的州城。返回的汽车里,我在心中给她说了一百个“拜拜”。我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不可能有好的结局,即使有了,最终也必定会被她亲手送入墓地。
我怎么忘记她是学医的呢?学医的人基本属于无神论者,我是否得原谅她一回?
墓地之约过后,我们的交往进入“半胶着”状态。
她活在虚幻的观念世界中,几乎不知人间烟火,她对贫困和落后丝毫没有觉察,也不知道同情和怜悯为何物,仅对枯燥的医学概念感兴趣。她热衷前来拜访她的人,向他们讲解宣判死刑的癌症是怎样形成的。她炫耀地说她讲起癌症的起因和结局时能让健康人的脸色变绿,能把患有病的人吓个半死。
我和她的争吵亦缘于她白衣下面裹着的那颗冰冻的心,她唇线分明的嘴巴始终不曾停止。说起病理头头是道,诸如人体疾病发生原因、发生机制、发展规律、功能代谢变化和病变转归等。她说生殖器、癌症、手术刀在他们眼里就是玩具。
她霸道的显微镜下一切都是物质的,世界上从来没有消亡的细胞,我吞进肠胃的咖啡在她的话语里显得异常嚣张。我强硬地做了暂停手势,并且颇绅士地冒出一句英语:B e s i l e n t!(安静)。我说我有一种天生的对疾病的恐惧与敏感,只要听谁说谁患上了某种病,我就立马感觉自己也得上了,而且尤为严重。她脸上的表情扭曲成了一张弓。我感觉到自己像躺在一架手术台上,被她语言的“手术刀”一点儿点儿地切割着。
换杯乌龙茶吧,我对噤若寒蝉的服务生说,我不想再喝西方人的习惯。桌上那杯黝黑的咖啡被我拒绝了加糖,苦得如同我此刻的情绪。
州城左岸咖啡屋里,我忘记了我曾经是爱过她的人。于是,我大声与她争吵:我不是病人。我的心里一直很健康。我怎么敢病?我还琢磨着策划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的主人公可以是名外表儒雅却“敢动刀子”的医生。病是闲人的事,你看,我一刻也没闲着。
看来你病得不轻,她说,欲望属于精神层面,医学无能为力。病理分析须从病人身体获取点儿什么,譬如:一滴血,一片肉等等。精神放不到显微镜下。接着她又说,但是我愿意断定,你病了。你的生活有毒。
中间我去了两趟厕所,我重复着天昏地暗的呕吐。
第二天,我收到她寄来的一份病相报告:
结果:患者精神心理呈现明显异常。结论:虽有济世之志,救人于水火之心,无奈此患者先天不足,后天亏损,已到无以挽回之地步。叹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