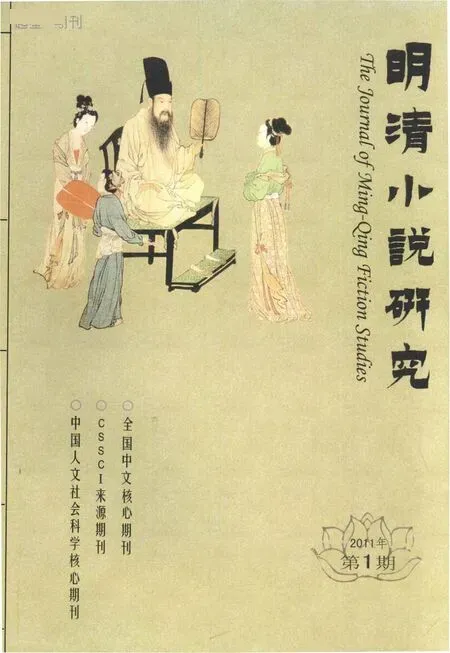鲁迅与明清小说研究
·吴金梅·
鲁迅与明清小说研究
·吴金梅·
鲁迅与明清小说的关系研究是一个涉及层面极为广泛的论题。本文拟从鲁迅对明清小说的学术研究,鲁迅小说对明清小说思想及艺术的批判继承与发展突破,以及鲁迅运用明清小说作为资源应用于其“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诸方面,对二者的关系作一梳理与探讨,并将此置于当下的文学与文化语境中,探寻其间的承继与延展,以期对当今的文化批评和建构有所裨益和借鉴。
鲁迅明清小说关系
鲁迅对明清小说的研究深刻透彻,其小说创作也或隐或显地显示出与明清小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鲁迅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中更不乏明清小说资源的运用。本文拟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当代语境下,对此重作观照,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种种联系,发掘鲁迅小说和明清小说包涵的丰厚文化意蕴,希图能对当代社会人文环境的重建有所助益。
一、系统、深刻、翔实——鲁迅的明清小说研究
鲁迅先生对于明清小说的研究成就,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小说旧闻钞》三种学术著作中。前两种是对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系统勾勒,其中对明清小说的渊流、作者、版本、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富含学理、充满睿智的梳理与论断,每每为后人赞叹以至不断援引;而《小说旧闻钞》则为明清小说的研究提供了较为翔实的文献资料,功莫大焉。这些著作不仅是鲁迅深邃学术识见与思想的集中展现,也提供了多种学术方法与理念,有待我们进一步去发掘其丰富的可资借鉴之处,如其以下特点即是学术研究的有益借鉴。
1.分门别类,系统探源
众所周知,明清小说内容庞杂,种类繁多,不易归纳。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先按小说的题材内容分门别类,将明代的小说分为元明传来之讲史、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等几类;将清代小说分为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讽刺小说、人情小说、以小说见才学者、狭邪小说、侠义小说及公案和清末谴责小说等数类。然后再按类分章,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在各章的论述中,首先是探源溯流,追寻发展的踪迹。如对以《三国志演义》为代表的“讲史”类小说,从宋说话梳理至金元杂剧,最终归至“其在小说,乃因有罗贯中本而名益显”①。另外又对其后的《隋唐演义》、《平妖传》以及《水浒传》和续书等其他讲史小说的流变,作了勾勒,并下延至清代。这虽与现在更为细致的归类——“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略有区别,但鲁迅先生的分类,更注重的是它们来自“讲史”的源头。换言之,不论“历史演义”抑或“英雄传奇”,皆从说话中的“讲史”一科演变而来,都有程度不同的历史根据。又如将《西游记》一类小说命名为“神魔小说”,将《金瓶梅》一类小说命名为“人情小说”,这是从题材上对此类小说最为精当的概括,一直沿用至今。就《金瓶梅》而言,不但指出该小说为诸“世情书”中“最有名”者,而且对其流变者如《肉蒲团》、《玉娇李》及《续金瓶梅》等,也各有言简意赅的论述评断。至清代,更以《红楼梦》为人情小说之最,并对其续书作了批评性的论述。如此种种,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明清小说分类系统,并清晰地勾画出各类小说的源流演变史。
2.联系时代,深刻理解
对于明清小说的思想内容,鲁迅先生能紧密联系时代特征,作出符合实际的评述,诸多论断至今仍被学界奉为圭臬。如对于明之神魔小说的产生、命名与源流,联系明中叶社会中佛道复极显赫的社会现状,“妖妄之说自盛,而影响且及于文章。且历来三教之争……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其在小说,则明初之《平妖传》已开其先,而继起之作尤多,凡所铺叙……但为人民闾巷间意,虽芜杂浅陋,率无客观。然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又或有文人起而结集润色之,则亦为鸿篇巨制之胚胎也”②。鲁迅对于神魔小说的梳理以《平妖传》开始,至明代《四游记》,最后重点探讨了其代表作《西游记》的思想内容,并将其归结到谢肇淛(《五杂俎》十五)的观点上来:“《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③。不但自己善于总结梳理,且善于引用前人的相关论述,显得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又如谈到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时,认为传奇风韵明末弥漫天下,易代不改,并选取代表性的《聊斋志异》进行探讨,认为其“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④,抓住了其形象塑造的主要特点。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3.辨析精核,考证不苟
鲁迅先生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史料的限制,但大致来说,其对明清小说的著者、版本、创作主旨等的诸多考证,谨严细致,能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如关于讲史小说《水浒传》的版本,对其当时现存的六种版本的“最要者四”逐一辨析,对各种版本的渊源、特点及刊行时间等问题进行了严密的梳理。又如关于《西游记》作者,历来未详,经鲁迅和胡适的考证,最终确定其为吴承恩。尽管目前尚有争议,但他们为这部小说寻找作者的苦心和功劳,不可抹杀。而《小说旧闻钞》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撰写过程中的所搜集资料的汇编,其严谨的学风和认真的态度,藉此可见一斑。
4.观念新颖,视角多变
《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以崭新的小说观念,综合的研究方法,充分顾及中国小说的历史传统为小说做史,清楚地梳理出中国小说的发展概况,并在辑轶、校勘和考证辨伪等传统的治学方法以外,又大量采用诸如社会学、心理学、比较文学、实证等新方法,挖掘小说潜藏的深刻内涵。如其指出《金瓶梅》中的色情描写背景在于当时皇帝荒淫,方士得势,“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⑤,不仅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金瓶梅》色情描写的原因,而且从文学的角度肯定了该书的艺术成就,评价中允而客观。鲁迅对比较方法的运用,十分娴熟。如对明清“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比较,通过对比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⑥,从“史”的角度来观照《儒林外史》的独特贡献,以“慼而能谐,婉而多讽”极为精炼地概括出了该小说讽刺艺术的主要特征。而谴责小说则“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⑦。寥寥数语,二者优劣自现。
总之,鲁迅先生对每部小说的论述,都有独到之见,以至成为小说研究中的经典看法。而正因研究方法的丰富科学,资料搜集的辛勤审慎,学术识见的敏锐深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学研究在史料辨析、作品评论、流派分类、时代概貌及发展规律等诸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正因如此深厚的小说史学养和背景,鲁迅的文学创作自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其中既有对明清小说的继承,又有超越。
二、鲁迅小说对明清小说的继承和超越
鲁迅小说与明清小说关系十分紧密。如周作人就曾提到《阿Q正传》的讽刺与《镜花缘》、《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和《怪现状》有相似与相异之处⑧。但我们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更要看到鲁迅的超越与突破。下面试分述之。
1.思想内容的包罗万象至深刻凝重
明清小说的题材包罗万象,其表现社会、反映民情风俗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如《三国志演义》对历史的重塑,《水浒传》对英雄传奇的谱写,《西游记》对神魔世界的构建,《金瓶梅》对“世情”的揭示,“三言二拍一型”等白话短篇小说对市井风情的摹绘等,奠定了它们在小说史上的“经典”地位。降至清代,“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聊斋志异》,“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闲斋老人序)的《儒林外史》,展现“悲剧中之悲剧”(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红楼梦》以及寄寓理想、讽刺现实、炫鬻才艺的《镜花缘》等,更将中国古代小说推向了顶峰。而鲁迅小说与之相较,题材上则表现出一种深度的灵魂开掘,并贯穿着深沉的自醒意识。鲁迅小说题材常概括为主要对国民性的深刻展示与批判,对知识者思想灵魂的深度开掘,这是鲁迅小说的两个重要向度。鲁迅指出:“古之小说,主角是勇将策士,侠盗赃官,妖怪神仙,佳人才子,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五四’以后的短篇里却大抵是新的智识者登了场”⑨。正因取材不同,所以才呈现出不同的面向。鲁迅曾说自己的创作宗旨是:“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⑩。心怀如此“启蒙”的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主题。他始终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知识者与农民)的精神“病苦”,关注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而如此深切的精神关怀使其小说具有一种内爆力,意欲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其小说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性的卑污。因此,鲁迅小说实质上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与知识者)灵魂的伟大拷问,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⑪。而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更是为了揭露其社会病根: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并“咀嚼人的灵魂”(见《阿Q正传》最后的描写)的本质。这里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鲁迅小说虽然残酷鞭打人的灵魂,却不以拷问和鉴赏他人的精神痛苦为目的,而是最终指向“绝望的反抗”:对社会,更对自身。鲁迅小说从题材到主题的如此变化,使其较之明清小说具有了更为现实的社会关切、更深层次的内向开掘与更高层的人文思考。因此可以说,鲁迅不仅选取了更能展示和代表时代社会生存状态与精神思想风貌的农民与知识者为关注对象,而且有更深刻的思想心理揭示与社会根源剖析。如果说明清小说是对于社会与人事的描摹,是对人情世态的叙述,且大多是一种向外的较为表层的再现,鲁迅小说则是对人类心灵和精神的深层探求与叩问,是一种向内的开掘与追问,从而使其小说内涵意蕴更为深刻厚重,这也正是鲁迅小说现代性的深刻体现。
2.叙事结构的丰富变幻到“看”与“走”的独特叙说
小说至明清,其叙事结构丰富多样而趋于成熟。其中如《三国演义》的以时间为序的线性流程,《水浒传》的连环勾锁、百川入海,《西游记》的以取经故事环环相串,《金瓶梅》的网状结构,“三言二拍”的复线结构、板块结构与视角变换,《红楼梦》混融一体的网状结构等等,成就了明清小说叙事结构艺术的典范性,而鲁迅小说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开端与成熟的标志,其叙事结构的最为独特之处,是将其深沉的精神痛苦展示与深度的灵魂鞭打拷问,及其对于社会与自身“绝望反抗”的最终指向,在小说中演化为“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结构叙述模式。前者如《示众》中唯一的动作与情节——“看”,以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氛围、情节,使文本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并由此而生发展开。其中,一类“好奇”看客“看”(被欣赏)被看者的同时,常还有一位隐含作者⑫的“看”:着意反讽,悲悯、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另一类二元对立的先驱者与群众之间的“看/被看”则把质疑最终指向作者自身,渗透着作者的生命体验。而在《故乡》、《祝福》和《孤独者》中,叙述者讲述他人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一个二十年间“不得不”“逃异地”而归乡的人,经历了一个由希望而绝望的再度远走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生循环。无论是《故乡》中失去精神家园的乡愁,《祝福》对家乡生存困境的逃避,抑或《在酒楼上》漂浮的无家可归、无可依附的漂泊流浪感,中国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的生存困境,都隐藏着作者内心的绝望与苍凉。但鲁迅以“走”来抗衡世界与自我的双重绝望,再以结构上的“顶点”——绝望后的挑战戛然而止来展现其“反抗绝望”的哲学与生命体验。如此的叙述方式和结构特点,已不同于明清小说,而具有一种现代性的、内涵深刻且精致新颖的叙事特点。这也与鲁迅小说多以短篇的形式反映人文社会内涵的文体选择有关,达到形式与内容的浑然天成。
3.艺术形式的丰富多样及至尝试创新
明清小说艺术形式丰富多样,其章回体长篇宏阔舒展,叙事变换多姿,尺幅间描摹历史,饱览英雄,而白话短篇则精巧绵密,情节曲折,人物栩栩,笔参造化,描摹如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斑斓多姿的小说艺术世界,而鲁迅小说则在对此有所借鉴与继承的基础上,以开拓者的先锋姿态,与其深沉的关切相适应,在形式上也进行了多方的尝试与探索,因而被称为“创造‘新形式’的先锋”⑬。
如《狂人日记》作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以不标年月的日记体,按照狂人的心理流动来组织小说,通过主人公的自由联想和奇异梦幻,直接剖露心理,且其所有叙述描写都带有主人公的感情色彩。而其白话“日记本文”和文言“小序”,则在语言上形成两个对立的叙述者和两重不同的叙事视点,从而使文本具有一种对立、颠覆的分裂性而构成反讽。其《孔乙己》在多重“看/被看”的视角转换下,叙述者、隐含的作者和读者在复杂的叙述网络中,交互作用,呈现出动态的叙事结构,在由全知视角向限知视角的转换中,拉近了作者、读者与故事人物间的距离,最终达到三者心理体验的互相融合。《伤逝》中的涓生,对于“爱情已不存在”真相对子君的“说”与“不说”,都是空虚与绝望的“两难”,而这也正是作者人生困境的深刻再现,诗化的倾向十分浓郁。《在酒楼上》、《孤独者》中,“我”与小说人物(吕纬甫与魏连殳)是“自我”的两个侧面,使得小说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这种对“灵魂的深”的开掘,构成了鲁迅小说诗性的丰富内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各个方面展示了鲁迅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现代特征。另一方面,如果说《呐喊》、《彷徨》对于“日记体小说”、“诗化小说”、“散文体小说”、“戏剧体小说”等诸多文体交互融汇的创作实践,是一种“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的统一,其《故事新编》则是以“起死”的方式激活古人,并把英雄还原于常人。其中或展示精神苦闷(如《补天》),或对英雄的祛魅(如《奔月》)等等,都渗透着鲁迅自身的生命体验。艺术上打破时空,古今杂糅,又常常掺入戏谑的杂文手法,让人耳目一新,并形成“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的互相补充和消解,展示了鲁迅在生命最后时刻的从容、幽默与洒脱。尤其穿插其中的“游戏笔墨”,更突出地展示出先生骨子里的悲凉。
除此整体结构、叙事方式和诗性化风格的尝试之外,鲁迅小说在表达的含蓄有度、语言的凝练简约、人物的传神写照及景物的描绘点缀,同样堪称典范。这些艺术尝试与明清小说相较,无不令人耳目一新,具有突破传统的格致与风范,体现了鲁迅小说思想与艺术的某种超前性及其浓厚的“试验性”色彩,也因此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了不同于明清小说的地位与意义。
三、鲁迅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中的明清小说资源
鲁迅对病态社会(主要是“黑色染缸”和“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评极其深刻,并将“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紧密结合,无情地“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其批评矛头既对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又能深入揭示其思想和历史根源,并无情地剖开人的灵魂,表达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沉情感。在这些多重指向的批评中,不乏对明清小说资源的借鉴,这是目前学术界尚少提及的重要方面,而这对于当下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也不无裨益。本文在此试举数例略加说明。
1.分析形象,批评深刻
鲁迅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对明清小说资源的借鉴和利用,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借助人物形象的分析,就是他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他对明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分析,不是就人物论人物,而是以此为缘由,扩而大之,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立论,刨根究底,作深度批判。如下列两段评语就颇具代表性: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⑭
其中以明代《水浒传》小说中的李逵和清代公案侠义小说中的侠客为例,不但简明地勾勒出由“侠”而“盗”终至为“流氓”的历史变迁,而且极为深刻地批判了他们身上具有的“奴性”。就一般而言,“替天行道”的纲领自有它的价值所在,在《水浒传》的研究中,一再受到高度关注和正面肯定。但鲁迅先生却独具慧眼,能窥察出其中隐含的“招安”因素和“自残”指向(打别的强盗),并将笔触深入到对国民性观照上,可谓精彩独到,鞭辟入里。就李逵而言,从金圣叹到今天,一直是高度赞扬的英雄形象,天性烂漫,敢做敢为。但鲁迅先生却发现,在他的行为中实际隐含着一种非理性的冲动,乃至不分皂白,滥杀无辜。更重要的是先生能将之置于“侠”的流变中加以观照,指出这是侠气的堕落,可谓一针见血。他所举到的《三侠五义》之类的侠义公案小说,其实受《水浒传》影响很深,将这两段论述对照起来读,更能了解“侠”演变及其深含的劣根性,批评尤为深刻。
2.巧借故事,生发批评
由于鲁迅先生对古代小说尤其是明清小说有着精深的研究,因而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往往由此而生发批评,顺手拈来,涉笔成趣,见解深刻,意味盎然。如在对热血青年以笔为武器进行斗争的安危关照中,鲁迅曾言:
您记得《三国志演义》上的许褚赤膊上阵么?中了好几箭。金圣叹批道:谁叫你赤膊?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⑮
又如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他特别举到:
《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唯一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⑯
这两段文字,一论文坛,一针对社会现实。二者均是险恶之境,一个“鬼魅多得很”,一个“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于是,鲁迅劝说一腔热血的后辈青年不要作战毫无掩护或不讲策略,要提防“鬼魅”,并以自我调侃的方式,用“逃走”来表达自己的无奈。此处借用“赤膊”与“坐化”两个小说故事,将问题说得明白显豁,看似不动声色,却造成一种强烈的反讽效果。但说到底,他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忘却左联五烈士惨烈的遭际:“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呐喊:“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其深沉悲愤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3.汲纳艺术,理论升华
鲁迅杂文犀利尖锐却又诙谐幽默,让你笑中含泪。这种讽刺技巧和幽默风格,显然来自对明清小说同类艺术的充分吸纳和借鉴,并在理论上作了高度的升华。如其对幽默、讽刺的论述:
最有名的金圣叹,“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虽然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谣言。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和“幽默”是并无什么瓜葛的。⑰
又:
例如在中国,则《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还有《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⑱
作为两种重要的文学表现手法,鲁迅认为幽默的特征是“借着笑的幌子”⑲传达着某一种思想感情,其语言或有趣或可笑,而意味却深长。关于讽刺,鲁迅则指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既不是‘捏造’,也不是‘污蔑’;既不是‘揭发隐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讽刺作者……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是希望他们改善”⑳。从上可见,鲁迅对幽默与讽刺的论述,既来自明清小说,又来自自己的写作实践。也就是说,既是对明清小说艺术资源的充分借鉴,又有对之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并且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有所提升与创新。由此也可以充分窥见鲁迅与明清小说的深厚关系。
4.发掘内涵,显微知著
明清小说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是鲁迅在社会与文明批评中经常借鉴的重要资源,从而使其批评更见说服力和穿透力。如: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海克尔)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㉑
又如:
看《红楼梦》,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份,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㉒
再如: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㉓
首段文字以《红楼梦》结局为论述对象,指出其续改者“生旦当场团圆”,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的缘故。对于中国文人这种“闭了眼睛的补救”和不敢正视现实的“瞒”、“骗”行为,作了无情的抨击,并指出在这条“逃路”上印证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正如对于奴性的深恶痛绝一样,对于自欺欺人,鲁迅同样绝不姑息,并指出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第二段鲁迅以《红楼梦》中焦大的遭遇讨论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从主奴关系,国民关系来切入,指出奴才实际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并把焦大与屈原类比,影射当时扼杀言论、不存在言论自由的社会现状。第三段文字是对上海文艺现状讨论中的一段,鲁迅在此把读书人分成“才子”和“君子”两类,并通过他们阅读《红楼梦》时的不同表现,揭穿了“君子”的伪装。尽管鲁迅说,“我无从知道”这些谦谦君子是否也看《红楼梦》,但答案却不言而喻。
如上种种,均借助明清小说资源来立论。或由其中一人,其中一事,或由其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的某一处、某一点生发开去,形象生动,富于趣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并在不动声色的高超艺术中,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与抨击,表达了作者深切的爱与痛切的恨。
注:
①②③④⑤⑥⑦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160、172、216、190、228、291页。
⑧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转引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页。
⑨⑩⑭⑯⑰㉓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526、159—160、499、582、298页。
⑪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⑫“隐含作者(impliedauthor)”是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小说修辞学》(1961)中提出的概念,用来指称一种人格或意识,这种人格或意识在叙事文本的最终形态中体现出来。换句话说,某一个叙事文本之所以是其呈现出来的形态,正由于隐含作者有意地或无意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审美趣味等注入其中。也有人用隐指作者翻译这个概念。
⑬雁冰《读〈呐喊〉》,《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3年10月8日。
⑮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页。
⑱⑳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287、340 -341页。
⑲㉒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22页。
㉑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大连大学人员交流中心
责任编辑:王学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