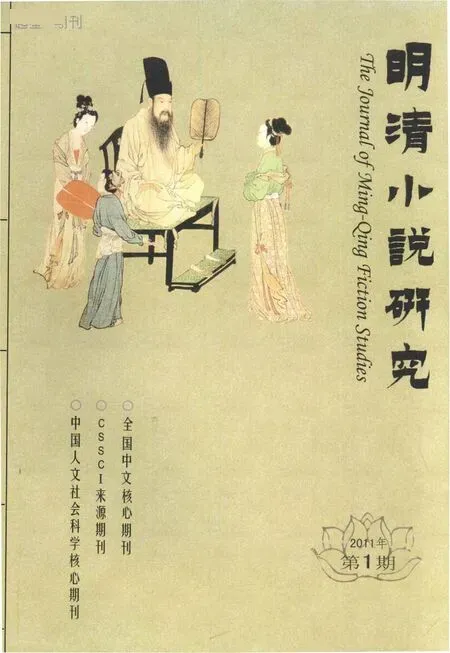三现身故事之流变及其影响
·林嵩·
三现身故事之流变及其影响
·林嵩·
《三现身》尽管违背了后世侦探悬疑小说的一些通则,但仍有可圈点之处。相比之下,在情节上脱胎于《三现身》的《清风闸》却显得乏善可陈。清代文言小说领域中出现了《三现身》故事的仿作与改作,从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折狱小说与刑名案例之间的互动关系。至近代,高罗佩又将此故事组织成结构精巧且有一定内涵与容量的作品。而这一系列故事在情节上均承自“三言”,这一故事情节本身足以代表“三言”的成就与高度。
折狱故事叙述性诡计案例互动情节驱动型
在南宋人罗烨《醉翁谈录》所开列的“公案”类话本中,有《三现身》之名目。一般认为,它是《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以下简称《三现身》)故事的前身①。《三现身》说的是术士李杰在兖州府奉符县设肆卖卜。一日,县衙押司官孙文闲往买卦,卜得当日当夜三更死。孙文归家与妻共议避祸,其妻设酒与饮。三更时分,其妻及婢女迎儿见孙文猛然夺门而出,自投奉符县河而死。孙文死后,其妻再适另一孙姓押司(是为小孙押司),复将婢女迎儿许配浑汉王兴。此后,孙文三度显魂央迎儿代其申冤。次年,包拯出任奉符县,得梦兆之助,为孙文昭雪冤情。盖孙妻与小孙押司早有私情,是日闻听“当日当夜三更死”之语,趁机用酒将孙文灌醉后勒毙,尸身撺入井中;小孙押司假扮孙文掩面逃出,投石河中,伪称孙文溺水而亡。
马幼垣是较早注意到《三现身》故事流变的学者。他在《三现身故事与清风闸》一文中指出:
近年比较文学兴盛,大家开始在“主题研究”(Thematic studies)上下工功夫。在中国文学内,此种课题甚多,包公自然是其中显著之例,其他如孟姜女、王昭君、董永、八仙、目莲、刘知远、杨家将、呼家将、狄青、岳飞、白蛇等,都是极繁绕的问题,牵涉长时期的演化和好几种不同的文体,而且往往还需要借重西方学者对西方同类文学作品的研究,以资启发参证。由于此等问题的异常复杂,对研究者来说,挑衅性也增加。在这里讨论《三现身》故事和《清风闸》、《三侠五义》的关系,是希望借以唤起大家对这种课题的注意,如果多几位学长,像王桂秋(剑桥大学)的研治孟姜女,许文宏(台湾大学)的考究白蛇传说,风气一开,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是可以另开一新纪元的。②
受这一研究思路启发,我们留意搜集了明清以来在《三现身》影响下产生的几种不同体裁的作品,希望通过对它们各自特点的比较,探讨与“公案”小说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
“公案”小说所涵盖的内容是比较宽泛的。早期的“公案”话本,如《醉翁谈录》所著录的,还包括了《姜女寻夫》这样的故事;后代如《龙图公案》之类的作品则往往又涉及忠奸斗争与绿林侠义等内容。相比之下,《三现身》算是比较纯粹的断案题材(为严密起见,我们可以称其为“折狱故事”),因此许多学者喜欢拿它和西方的侦探悬疑小说相比。可是认真分析之下,不难发现,《三现身》对于断案过程的着墨并不很多,作品极力铺陈的是孙文冤魂的三次现身(作品的题目也说明了这一点)。故事中的包拯在得到梦兆与隐语的指示之后,不费吹灰之力便揭破了真相:
“大女子,小女子”,女之子,乃外孙;是说外郎姓孙,分明是大孙押司,小孙押司;“前人耕来后人饵”,饵者食也,是说你白得他老婆,享用他的家业;“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大孙押司,死于三更时分;要知死的根由,“掇开火下之水”,那迎儿见家长在灶下,披发吐舌,眼中流血,此乃勒死之状。头上套着井栏。井者水也,灶者火也,水在火下,你家灶必砌在井上,死者之尸,必在井中。“来年二三月”,正是今日。“句已当解此”,“句已”两字,合来乃是个包字。是说我包某今日到此
为官,解其语意,与他雪冤。③
看来包拯破案并不是凭推理,而是靠猜诗谜。更重要的是,《三现身》故事违反了后世所公认的破案小说的一些通则:
第一是断案凭借了超自然的力量。如果不是孙文的鬼魂三次现身,如果包拯没有得到梦境与隐语的指示,疑案便不可能告破。
第二是最重要的一位犯罪人小孙押司未能尽早引出。小孙押司原是大雪里冻倒的人,被孙文救活,不想他忘恩负义,反私通孙文之妻谋死孙文。这样一个重大的犯罪嫌疑人,却直到孙文死后才出场,而他与孙家的渊源关系更是直到故事最后才被披露。
第三是对读者隐藏了一些不当隐藏的事实。孙文遇害当天,小孙押司也在案发现场,但由于作者没有尽早让小孙押司出场,导致这一重要事实被隐藏。孙文死后,尸身被撺入井中。孙妻为了毁尸灭迹,又在井上设灶,这一反常的举动也没有告诉读者,只是通过孙文的冤魂“脖项上套着井栏”与“掇开火下水”的隐语做了暗示。对这样的隐语,读者只会感到莫名其妙,除非是像包拯一样得到神助④。
众所周知,大多数的侦探悬疑小说总是会安排一些“叙述性诡计”——即通过隐藏一部分有效信息,或增设部分干扰信息来迷惑读者,从而给读者造成一些主观上的先入之见——以使结局更加出人意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阅读小说的过程,实际上也在与作者做智力的角斗;只有那些看透“叙述性诡计”的读者,才能揭破故事的迷局(这也是破案悬疑小说所独有的魅力)。但具体到“三现身”这一故事,由于隐藏的事实过多,读者实际上失去了猜破“诡计”的机会;这不仅使阅读的乐趣大为减少,甚至还会令人有愤而摔书的冲动。
在《三现身》中,最重要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叙述性诡计”便是案发当夜冲出房门、堕河而死的并不是苦主本人(苦主已在屋中被害),冲出房门的是假扮苦主的凶手。故事中是这样叙述的:
只听得押司从床上跳将下来,兀底中门响。押司娘急忙叫醒迎儿,点灯看时,只听得大门响。迎儿和押司娘点灯去赶,只见一个着白的人,一手掩着面,走出去,扑通地跳入奉符县河里去了。⑤
《三现身》之所以还有可圈点之处(尽管它违反了那么多的通则),就在于这一处“诡计”的设置确实是出众的。但如果细加分析,这一处文字也还是有不到之处。“只见一个着白的人,一手掩着面,走出去”,这个人其实不是孙押司,因为迎儿当时犯瞌睡,追出门去后并没有看清此人的面目——这是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但是就在前一句,作者却又明确地说“只听得押司从床上跳将下来”;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叙事逻辑,后面这个“着白的人”就应该是孙押司本人。“叙述性诡计”允许设置一些文字上的“陷阱”来干扰读者,但却不能容忍用错误的叙述来误导或欺瞒读者。而这一处“诡计”多少便有“欺瞒”之嫌。这其中的主要问题出在,文中前后两句话的叙述视角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着白的人”是迎儿的视角,而整篇故事的叙述者却是“全知型”的作者。如果不说“只听得押司从床上跳将下来”,那么只能说“只听得有人从床上跳将下来”;这样的话,西洋镜马上就会被眼明的读者拆穿。因此,此处最好的处理方式也许是干脆删掉“押司从床上跳将下来”这多余的一句,保留“只听得兀底中门响”,这样视角便可以统一起来。许多侦探悬疑小说往往采用由第三者口述的叙事模式,如《福尔摩斯探案》的叙述者便是助手华生,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种视角便于作者施展“叙述性诡计”。
尽管在“叙述性诡计”的使用方面还不能做到完美无瑕,《三现身》毕竟还是设法制造了一些陷阱与悬念。而在情节上直承“三现身”的《清风闸》在这一方面则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它完全是平铺直叙,干脆让读者亲眼目睹了行凶的过程;这一点马幼垣的文章中已经论及。如果作为折狱故事来加以考量,《清风闸》简直很难及格。它就像街头小报上登载的那些不入流的“法制文学”作品,总是津津乐道于血淋淋的罪案本身,并热衷于对作案手法或男盗女娼的犯罪事实进行详尽的描写,相反对侦缉过程并不一定十分在意。它带给读者的纯是感官上的刺激,而不能引起人们探知真相的兴趣或是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清风闸》相传是乾隆年间扬州著名评话艺人浦琳最擅说的书。不过浦琳所说的《清风闸》并没有话本流传下来,今存的嘉庆刊本《清风闸》四卷三十二回,署题梅溪主人,已不是浦琳说书的忠实记录,但在故事情节方面应与浦琳的评话相去不远。浦琳的成就,肯定是在“口舌之妙”这一方面;而今本《清风闸》的长处也正在于它对于市井生活的描摹,它的主线之一是皮五的发迹变泰,包公破案只不过是一条副线⑥。因此如果要对《清风闸》进行题材上的归类,与其把它归入“公案小说”,倒不如把它看作是“市民文学”。它的故事虽然脱胎于《三现身》,但是它并没有在“折狱”这一方面踵事增华,而是别出心裁地往描摹世情的方向发展。因为说书人的强项是纵横捭阖的宏大叙述与对细民生活的细致描摹;而侦探悬疑小说却是一种相当精巧的文学样式,它所要求的“叙述性诡计”很难与评话这样的艺术形式相结合。
二
“三言”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取材于唐宋元明的野史与笔记,是把文言笔记改成白话小说;而明清两代的一些文言小说,也从“三言”中汲取了素材,反过来又把白话小说用文言铺陈出来。《三现身》也拥有为数不少的改作与仿作。清代不知名者所作《隐吏闲谈》中的《星士埋奸》一则,便是一篇明显的仿作:
国朝浙江山阴县陶某幼依其戚习幕淮安。戚死流寓不能归,充某邑刑胥,买幼婢执炊,相依如父女。数年少有所蓄,遂于本邑娶妻。无何,婢已及笄,妻欲鬻之,陶不忍,略备奁具,嫁一民壮为室,然贫甚,恒周恤之。越年余,邑中来一星士,推测多奇验。陶令推算,星士决其立冬日必死,陶为之忧疑不释,妻劝慰之。迨秋杪,陶虽无疾而怏悒日甚。妻曰:“或恐有无妄灾。盍乞假闭门,邀一二知交,相聚排遣何如?”陶从之。招友畅饮,留连晨夕。至立冬日,竟无恙。更余,客皆半酣,入内少憩。忽闻室中轰如雷,众趋视,见陶面血披发,找户出,行甚驶。众挽之,遽投河,没数日尸亦无踪。莫不谓星士如神,陶负宿孽矣。妻无所依,醮某甲去。独所嫁婢悲痛如丧父,每于梦中见陶浴血相向,责其不为申雪,夫妇异之。时陶屋尚扃闭,而宰斯土者为少年科目,有治才。民壮遂以夫妇所见密陈。官令导往发扃周视。见壁角有血痕,房后土地亦微有迹。掘之,陶尸俨然。拘妇刑询,乃知所醮某甲,素善泅,自幼有私,预赂星士,惑以生死,至日先伏某甲室中。陶入,杀之掩埋。而甲诈为陶中恶状,夺门投河。先期设宴,欲令客左证其事,使人不疑也。得实并置诸法。
假星士而示死期,假知交而为坐证,假奸夫而灭踪迹。埋奸伏毒,
巧且密矣,不料遇此贤令尹,卒伸其冤。可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⑦
这则故事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及其相互关系几乎与《三现身》完全相同:受害人是县衙里的胥吏,其妻不守妇道而与人有私,家中收养的婢女有情有义并替家主申冤,两个故事中又都出现了算卦的术士。尽管因袭的成分很重,《星士埋奸》却仍不失为一篇高明的仿作。作者仅用了寥寥数百字便把一桩离奇的疑案叙述得简净明白;更重要的是,故事对于“叙述性诡计”的使用十分纯熟,并弥补了原作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原作中的术士李杰是阴阳有准的“神算子”,他本人与罪案无涉。《三现身》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目的之一是为了说明“死生在天”,不论人们怎么挣扎,也无法逃避“天数”的安排。在《星士埋奸》中,星士成为共同犯罪人,他诡为预言,迫使陶某惊惧不定,任凭恶妻摆布,最后自入网罗。这样的安排减少了“天命”色彩,也使故事中所有出场人物都与案情密切相关。原作中小孙押司投石河中,造成孙文溺水假象,这不是特别合乎情理;仿作中改成罪犯某甲善泅水,因此能假装投河而不死。尽管这篇仿作仍然保留了冤魂显灵的内容,但是断案的县令是通过勘察现场而发现的疑点;冤魂显灵只是促使婢女上告,真正的断案过程中并没有借助神鬼的力量。
《三现身》的改作则如清代吴炽昌《客窗闲话续集》卷二中的《粤东狱》。这一篇文字稍长,有千余字,为便行文,现择要迻录于下:
粤东某生聘某氏女,国色也。偶出观剧,被为富不仁者所见,重贿女母私之。往来甚密。恐旁人执奸,乃于女卧榻下穿一地道通后院空室中。倘有恶耗为潜避计。未几某生入泮,使媒来订婚期。富室与其母女谋,使生入赘而毙之。母女皆诺,告媒曰:“婿家无父母,老妇亦无夫无子,两无依倚。如肯入赘,两得其便。否则姑缓,俾女待我卒也而后于归。”媒复之,生欣然愿赘,期于清和之吉完姻。时男女亲朋集贺者数十人同观花烛。无不啧啧羡新妇美者。生喜甚,送客入席,即归新房与妇对酌。时无一女客,生得畅意为欢。新妇不作恒常羞涩状,竟执爵相酬饮。生入醉乡。时外客闻内宅惨呼一声,共骇愕间,见新郎衣履如故,散发覆面,狂跃而出。群欲询之,已疾奔出外。客皆追随。行里许,遇大河即跃入水而没。客呼鱼舟捞救,经日夜不知尸所在。……
未几,易一令,有明察声。……变服为星卜之流,访诸其邻。邻人曰:“有某富室,素与妇女无亲故,忽往来甚密。我侪亦疑有故,但是日新郎发狂投河,众目共睹,岂有他哉?”令曰:“汝见之否?”对曰:“我亦在座。”令曰:“汝视新郎貌作何变色?”对曰:“披发覆面不及见。”令曰:“道在是矣!富室安在?”对曰:“今日犹见其入新妇家也。”令辞去,易服率健役百余突至妇家,围其前后户而搜之。……令入房,见铺陈精洁,皆常用什物,无可疑者。正踌躇间,俯视床下一男子履。回顾新妇,骇然失色。令呼众役入,移床而观。见地板有新垫者。命役举之,地道见。令乃带役入,穿出至一空室。室隅鲜衣少年伏焉。执之,推门至院落。见地有新挖状,命役启之。生尸在,经夏不变。喉间扼痕显然。遂出。聚案内人证一讯服辜,论如律。乃知生醉后,妇女与富室共扼其喉而毙,从地道舁入后院埋之。投水之人,系富室以重价觅善泅者为之也。
芗岸曰:人之阴谋诡计,惟图色为甚。然而天道昭彰,竟无不破之案。是以大盗亦戒采花。是案也,彼庸庸者流,竟谓新郎投河而死,众目观瞻,与妇女何尤?随成疑案。其有心者不过揣新郎之发狂也,或以药酒为之,疑女有故,然不能破其奸,敢讯诸乎?后令之勘访搜寻,可谓有胆有识。然使床下男履不露,何以发其覆乎?我故曰天道也。⑧
这个故事的情节显然也照搬了《三现身》,只是完全没有了冤鬼显魂等迷信内容。故事中又出现了占卜的星士,县令“变服为星卜之流”,这应是受了《三现身》原有人物元素的影响。在《星士埋奸》中,罪犯某甲仍被安排在陶某死后出场,某甲与陶妻有私的事实也是最后才向读者披露的;衡诸“嫌疑人应尽早引出”的侦破小说通则,仍然显得美中不足。《粤东狱》则将这一点完全改正。不过,《粤东狱》的起首交代的“于女卧榻下穿一地道通后院空室中”以及“使生入赘而毙之”等,又过于详尽,有“泄底”之虞(不过尽管读者预知某生系被谋杀,但其究竟如何被杀仍留有悬念)。总体上看来,这两篇仿作与改作,在继承原著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在叙事模式上各自进行了调整与提高,作为短篇折狱小说,应该说是差强人意的。
《粤东狱》的作者吴炽昌,人称他是“浙水名流,燕山游幕”⑨;《星士埋奸》选自《隐吏闲谈》,从书名可知,作者也是一位退隐的吏员:他们的身份是很接近的。这两篇故事的最末又都有一段作者的按语,这在格式上完全是模仿宋代郑克的《折狱龟鉴》。
县衙中的幕友、吏员们在日常工作中总会接触到大量的刑名案件,其中有些案件是他们经办的,但大多数可能是同业之间的耳食之谈,甚至不排除有些案子干脆是从勾栏瓦舍里听了来的。这些疑案或奇案,尽管只是吏员们茶余酒后或闲居漫笔时的谈资;但为幕作吏者在转述或记录这些奇案故事时,往往会从他们的职业习惯出发,对于故事加以整饬,特别是对其中一些不符合律例或常理的细节进行再加工。虽然在衙门中刑讯逼供乃是家常便饭,但吏员们显然要比缺乏法律知识的说书先生更加重视干证、物证以及讯案中的勘问技巧等;并且他们喜欢从刑案侦缉的高度对案件进行反思与总结,这两篇改作与仿作中的按语便体现了这一点。
于是在幕友与吏员们努力之下,这类折狱故事越来越具有了“经典”的色彩: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些仿作与改作的叙述手法更为巧妙,故事也更加惊心动魄,已经很接近现代西方的侦探悬疑小说;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真正发生过,而是源自于街谈巷议、稗官野史的小说家言,竟还被当作典型案例收录在案例集中以供治“刑名之学”者参考(例如《星士埋奸》便被《历朝折狱纂要》收录)。《三现身》故事的流变恰好就是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从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折狱小说与刑名案例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吴炽昌这样的幕友或书吏。
三
在《三现身》系列作品中,不论是白话系的《清风闸》,还是文言系的《星士埋奸》、《粤东狱》,都是属于短篇的范畴。《清风闸》虽然有三十二回的篇幅,可以算一个中篇的规模,但实际也只是把一个短篇的故事抻长了而已,而且我们认为它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折狱小说。
短篇小说的悬念设置不论怎么精巧,总是会很快地“图穷匕见”;因此,多数读者对中长篇的侦探故事会有更多的阅读期待。对《三现身》故事做进一步发展的当属荷兰的汉学家高罗佩。高罗佩小说的素材多数取自中国的旧小说或案例,但叙述上却完全采用了西洋侦探悬疑小说的路数。高罗佩在《四漆屏》一作中,用他常用的“案中案”的手法,把《三现身》的情节熔入故事中。由于篇幅的增加,作品的出场人物更多、相互关系更复杂,叙述性诡计的安排也更为隐蔽。可以说,高罗佩成功地使《三现身》故事成为一个布局精巧而又有一定内涵与容量的作品。不过,细按其源,其故事情节本身仍应追溯到“三言”。
“三言”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一个高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三言”中的一些典型人物形象及其所反映的市民思想与时代精神等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实际上,像《三现身》这样的“情节驱动型故事”,主题可能并不鲜明,人物形象也未必丰满,其吸引人之处全在于情节之波折。这些情节本身已足够精彩,它们的生命力如此之强,经过历代作者的翻新,同一情节可以通过不同面貌的故事呈现出来,并重复地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注:
①关于《三现身》的写作时代,胡士莹认为可断为南宋人作品。详见《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版,上册/第225页。
②马幼垣《三现身故事与清风闸》,《中国小说史集稿》,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11页(原载《联合报》1978年4月11、12日)。
③⑤[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十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版,上册/第187、178页。
④参[英]马丁·菲多(MartinFido、徐新等译)《福尔摩斯的世界》,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版,第197~198页;马幼垣《三现身故事与清风闸》,《中国小说史集稿》,第205~206页。
⑥关于《清风闸》的评述,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下册/第624~625页;刘光民《古代说唱辩体析篇》,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319页。
⑦[清]周尔吉《历朝折狱纂要》“辨伪”卷三,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3年版,第261~263页。
⑧[清]吴炽昌著、石继昌校点《正续客窗闲话》,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版,第177~178页。
⑨[清]性甫谢理《续客窗闲话序》,《正续客窗闲话》,第303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徐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