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今昔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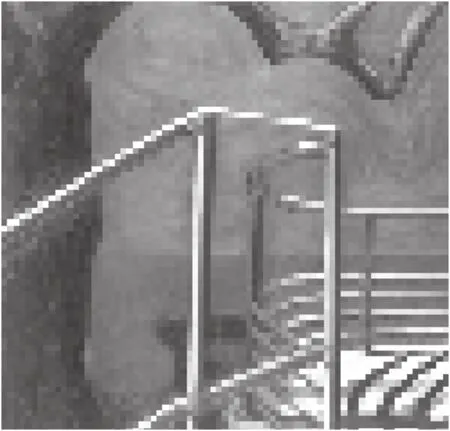
《贝壳》的由来
谈到过去,谈我们当年做学生的一些事情,好像就有了许多话要说。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学校内外的情况与今天差别很大,特别是文化环境的变化就更大了。说起三十年前我们校园的文学生活,跟今天对比一下可以看出许多不同。
当年求学的情景还在眼前。当时恢复高考不久,每一级的入学间隔时间还没有调整好,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学校交汇的时间很长。这就有了更多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人在一起,说话南腔北调,特别有意思。
当时热爱文学的同学比现在多,中文系差不多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上课谈文学谈语言,下课更是如此,大家常常就新读过的作品讨论争论起来。七十年代末国内各大学都成立文学社团,据说与文化大革命前的传统是一样的。我们学校中文系有两个文学社,后来合办了一个文学刊物,那就是《贝壳》了。
一开始由我们文学社的几个人拟了好几个名字,找系主任肖平老师决定,他看了看说,就叫这个吧,我们在大海边上,等于是拣回了一些美丽的贝壳。
第一期是手刻蜡板印出来的,这在我们眼里漂亮得不得了。后来才是打印的,那已经是更高级的东西了。
我们刻蜡板的同学有一手好仿宋体,设计封面和插图的人能写能画,总之人才很多。那时学生当中不完全是稚气的小脸,还有三四十岁的人,他们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那会儿即便是刚刚二十多岁的人,也觉得自己经历了很多事情,什么都懂,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所以现在一看到青年人的那份骄傲,总是十分熟悉和理解。人应该有这股劲头,这是冲劲。当年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天文地理无所不晓,而且能够迅速地阅读,牢牢地记忆,顽强地消化。在这种情形下进步肯定是很快的。
除了上课,再就是尝试写作。有的写诗,有的写小说和散文。小说一般被认为是最难的,篇幅长,还需要有人物和情节。过去说的“写书”,就是指写小说。怎样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物形象,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诱惑。要写出丰满动人的人物,教写作的老师不停地举例子、强调,所以反而让人有了神秘感。
初学写作,最难的就是写出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当时处心积虑地想个不停,主要是围绕“人物”。
我们有了刊物,就分别写稿,分开栏目,各自完成“主打作品”。那时好胜心极强,一心要超过其他院校寄来的社团刊物。当年铅印的院校刊物还不多,在今天看来都是很简陋的。不过当时并不这样看,只觉得寄来的所有刊物都香气逼人。这仿佛是一场较劲的比赛,既有趣又费力,四周吸引了很多的人。
同学们飞快传递彼此的一些阅读信息,总是非常兴奋。比如说一个人在阅览室里读了一篇刚刚发表的作品,就赶快告诉大家。什么刊物出了一个新的作者,哪一篇作品产生了影响,大家心里清楚极了。那时候没有网络,基本上也没有电视,就靠阅览室来满足我们。问一下,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那间大阅览室了。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多少欢乐的时光、产生过多少激动。
还记得第一次看二十多吋的彩色电视,是在中文系合堂教室里。看的第一个话剧是曹禺的《雷雨》,不久又看了德国作家席勒的《阴谋与爱情》。那种激动如在眼前:回到宿舍里已经很晚了,还要讨论剧情,多半夜都不愿睡觉。看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当年任何一个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或散文都不会被我们忽略。
由此来看我们热衷于办文学社和编刊物,也就容易理解了。
现在的标准
那时每年都有全国小说评奖,一次评出二十篇小说。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哪一个作品能够得奖。就像打赌似的,每个人列出一个二十篇作品的单子,只等新闻联播公布结果。可见那时的文学公信力之强。一连几年,大家猜中的都在十几篇以上。这与今天完全不同。如今不要说在校的大学生了,就是著名的专家也猜不出。原因就是现在的文学标准改变了,变得空前复杂了。
有人可能说现在的作品多了,出其不意的情况也就多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写作已经是五花八门,这就不好掌握统一的标准了。其实文学怎么会有其他的古怪标准?它只能是一个文学的标准,只能是坚持这个标准的问题。如果社会变得混乱无序了,没有是非了,文学的标准当然也不会有。
有人固执地说现在是一个没有标准的时代,因为随处什么东西都给“解构”了,说不清了,无论什么事物,说好说坏都可以。还有人认为“真理”也是不存在的,世上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这样的时代难道不是很可怕吗?因为到处都是这种“相对”,人们也就不再需要去追求真理了,因为凡事此一时彼一时,可以得过且过。生活在这样的人群里还能再谈文学、还值得再谈文学吗?不可能也不必要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追求真理的族群不可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关于写作,没有文学的标准,那就一定会有其他的标准来代替,比如商业的标准、对某种利益集团有用的一些标准。这都与文学无关——不,这只会对文学产生极其严重的伤害和扭曲。文学是人的心灵之业,对文学扭曲了,对人也就扭曲了,这个社会也就变得畸形了。
过去我们大致都知道什么作品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现在则不知道了。那时候我们还幼稚,只二十来岁,没有写出更多的书,也没有读到今天这么多高论,可是我们还算清楚地知道自己向往什么、什么能感动我们,怎样的作品能够引领我们的心灵走向更美更善。现在反而犹豫不决了,我们有可能变得更高深了,文化的文学的视野也比过去变得开阔了不知多少倍,结果也就变成这样的无所适从。降临到我们身上是真正的噩运:丧失了判断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法弄得清哪些是好的作品,哪些又是不太好甚至是很坏的作品了。
有时候我们刚刚被一部作品深深地感动过,比如说被它的语言、被它的故事和人物、被它蕴藏的某种东西给激发起来——可是我们一直信赖或比较信赖的专业朋友看了却很生气,说这分明是一部很坏的作品……类似的例子或正好相反的例子数不胜数。这样时间久了,我们就给弄糊涂了,不断地怀疑自己。最后,我们不得不试着放弃一直秉持的一些标准。
有人会说世上再也没有比艺术这种东西更难掌握的了,它有一万个标准、有千变万化的奇特因素。可是我们也知道,它尽管复杂,仍然还要我们去读、我们去感受吧,仍然还要落在我们的良知里,被我们的知性过滤和筛选一遍吧。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怪异,也并不等于没有标准了。
如今网络上滚动着无数的“文学”,书店和地摊上也摆放了无数的“文学”。各种读物像海洋一样涌过来,这一切在有标准的人那里哪怕稍稍予以停留,也会让人心烦意乱。这种捡选的工作量是巨大的,能把人累得崩溃。所以一个适时而至的办法,就是认同这个时代的无标准说。没有标准是最好的,最省心了,怎样都行。也许现代真的不再需要标准,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来到了一个重商主义时代、物质主义时代,人们不需要文学也能活得挺好。
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么这大约也就是非人的时代了。动物不需要精神生活,只要满足了口腹之欲,它们一定是很高兴的、欢欢乐乐的。
访师散记一
因为从很早起就向往写作,并且听信了一个说法,就是干任何事情要想成功就必须寻一个好老师。这个说法今天看也不能说就是错的,只不过文学方面更复杂一些罢了。
记得自己从很早起就在找这样的老师,这里不是指从书本上找,而是从活生生的人群当中找。我曾想象,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一定会按照严格的拜师礼去做。听说有的行当拜师需要一套繁琐的程序,比如磕头上香、穿特别的衣服之类。这一套我是很烦的,但为了有个像样的、令人钦佩的老师,我也会不打折扣地马上去做。
最大的问题是很难找到这样的老师。他们在那个年头里非常稀缺,这与现在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文学方面可以做老师的人多得不得了,每一座城市里都有一批,而且经常可以看到挂牌营业的人。那时则不同,文学爱好者很多,能做老师的人很少。有时候我们觉得某个人完全可以做老师了,但你一旦真的要拜他为师,他就会吓得赶紧走开。
我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这段时间里,游走的地方很多,虽然是为生活所迫,但其中还是少不了文学内容。我把交往文学朋友和寻找老师这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一听说哪里有老师就赶紧跑了去。这种访师寻友的传统可能主要是东方式的,翻翻我们过去的历史,其中有很流派师承这一类的故事,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样的说法。我对师傅和老师一直是非常尊敬的,比如说我永远不会对老师辈的人说出不恭之言,只不过为了“一日”而“终生为父”,似乎还做不到。
在东方,做一门艺术或一门手艺,没有师承就很成问题,一个专业人物出门混事,人们总会问起一个最基本的、自然而然的问题:你的老师是谁?这等于问你是不是出于正门、有没有专业上的渊源。没有一个名声很大的老师藏在身后,要从事专业会是格外不顺的。当然,我当年急于寻师绝没有想过这么多,而只是为了快些摸到入门的路径。在许多人眼里,文学写作是很神秘内在的一门学问,它尤其需要高人的指点。
从书本里学习是重要的,我当时所具有的一点写作能力,可能绝大部分还是来自书本。我看了好的作品就模仿,就是这样开始的。可是我还是有点心虚,因为没有老师而忐忑不安,就怕有人猛地问我一句:你是跟谁学的?你的老师是谁?所以我一方面因为进步和开窍太慢,恨不得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另一方面也深受中国从师传统的影响,极想投到一位老师门下。
在初中读书时,我不知听谁说到有一个很大的作家,这人就住在南部山区的一个洞里,于是就趁假期和一个同学去找他了。当年我们的学校就在海边,认为这里偏僻得像天涯海角差不多;而南部山区看上去只是深蓝色的一溜影子,完全是遥远的另一个世界。我们真的要闯一闯大山了,并且是去找一位住在山洞里的高人,只一想就激动不已。
记得我们两人骑了自行车,带了水壶,蹬了快一天的车子,这才来到了山里的那个小村——它原来不过是村名里有一个“洞”字,高人本人并不住在山洞里。这使我们多少有点失望。同样失望的还有大山,它也不是从远处看到的那种深蓝色,而是土石相嵌粗粝粝的,树木也不太茂密。
急急地打听那个老师,有人最后把我们带到了一间水气缭绕的粉丝房里,指了一下蹲在炕上抽旱烟的中年男子。他的个子可真高,双眼明亮,手脚很大。我和伙伴吞吞吐吐说出了求师的事情、我们心里的迫切。他一直听着,面容严肃。这样呆了一会儿,说那走吧,跟身旁的人打个招呼,就领我们离开了。
原来他要领我们回自己的家,那是一间不大的瓦房。进屋后他就脱鞋上了炕,也让我们这样做。大家在炕上盘腿而坐,他这才开始谈文学——从那以后只要谈文学,我觉得最正规最庄重的,就是脱了鞋子上炕,是盘着腿谈。这可能是第一次拜师养成的习惯。
他仔细询问了我们练习写作的一些情形,然后拿出了自己的稿子:一叠字迹密密、涂了许多红色墨水的方格稿纸。它们装在炕上的一个小柜子里,我们探头看了看,有许多。可是发表在报刊上的并不多,他订成的一个本子里,大致是篇幅极小的剪报。我和伙伴激动得脸色彤红。这是一些通讯报道。
老师一个人生活,老婆不孝顺爹娘,被他赶跑了。他与我们交谈中,主要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自己要孝顺,将来找个女人也要孝顺;二是写作要多用方言土语,这才是最重要的。
访师散记二
第一次拜师的经历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和伙伴从南山骑车回来,一路上都兴冲冲的,一点都不觉得累。我们最高兴的,是从今以后终于有了一位老师,这不仅是我们文学上能够得以飞快进步的重要的条件,而且还让我们有了一个不会轻易宣称的秘密。我们可能告诉别人在写作这方面已经有了师傅,却不会说出他的名字来。
本来事情是非常顺利的,但最美好的事物往往是格外要费些周折的。大约是从南山回来的第一个学期,我因事出了一趟远门,回来正准备再次去看望老师,就听到了一个噩耗:老师因为脑中风突发去世了!这是伙伴告诉我的,绝对没有错。望着伙伴的两道长泪,我紧张得一时说不出话,一会儿也哭了。
在没有老师的日子里,我们努力实践着他的教导,一方面在家里对长辈顺从,尽可能忍住不顶撞他们;再就是在文章里使用了很多方言土语。后者让学校的语文老师很不耐烦,但我们仍然坚持下来。
不久我们又听到了邻近一个村子里有一位代课老师,这人也是一位作家,就急急赶了过去。原来这人只有二十多岁,父亲是本村的村头,留了分头,鼻子很尖。尽管看上去有点别扭,我们对他还是诚惶诚恐的。他十分傲慢,根本就不正眼看人,只把我们领到一间屋里。一进屋就吃了一惊:整整一面墙都用红笔描画出光芒四射的图案,而放射光芒的最中间是比巴掌还小的一个红方框,里面粘贴了一小块剪报。那当然是他发表的作品。
因为他极其严肃,我们都不敢开口。可是沉默了一会儿,他开始询问:家庭出身?年龄?所在学校?我们结结巴巴的,他就训诉起来……我和伙伴不知怎么就踉跄着出来了,头也不敢回一下。
这样一直到了半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知道城里来了一位真正的作家。这人要为本地一个先进人物写文章,所以就要呆上一段时间。我和朋友最终还是设法敲开了他住处的门,恳切地表达了拜师的愿望。这人长得比住在大山里的第一位师傅差多了:矮个子,圆脸,花白的头发很长,多少有点像老太太的模样。他戴了一块表壳发黄的手表,我们以为是传说中的金表,极好奇又不敢多看。他非常慈祥。交谈中,他主要谈了文章中要多多描写景物,并且一定要与人物的心情配合起来,并举例说:文章中的人如果烦恼,就可以描写天上乌云翻滚;反之则是万里无云。
我们回来试了一下,觉得并不难做,而且收效显著。
正在我们为即将拥有一位新的文学师傅而庆幸的时候,巨大的打击来临了。那是第三次去找他的时候——老师已经结束本地写作回到了他的城市,我们就坐长途汽车奔去了。按照地址登上一座楼,惊喜地见到了师母。她说老师正在里屋休息,让我们过两个小时再来。我们按规定时间去时,却发现门上有一把大锁。我们先是在门口等,然后到街上转,回来看还是那把大锁。最后一次大锁没有了,敲门,门却再也没有打开。
为了能弄清原因,我们回到了本地小城,找到当时接待老师的一位干部。想不到他见了我们面孔一直板着,特别是看我的时候,目光里有十分厌恶的样子。这样呆了一会儿他总算说话了:“你们再不要去缠他了,那样身份的人能收你们做学生?家庭严重历史问题……”
我觉得头皮有一种悚悚的感觉,什么话也没有说,扯扯伙伴的手就出来了。
这之后就只能从书本上学习了。这当然是最有效最可靠、且不会遭到拒绝和喝斥的。但还是有一种投师无门的痛苦,隐隐地鲠在了心底。随着时间的延续,日子长了,我觉得没有老师还是不行,甚至觉得这是很糟糕以至于很不祥的。
那时我多少把文学写作当成了一门手艺,后来才知道,这种认识虽然有些偏颇,但其中纯粹工艺的部分也还是有的。让师傅“传帮带”,这是任何行当手艺传承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
就这样,直到我初中毕业,不得不一个人到南部山区游走的时候,还是没有找到师傅。我在山地走走停停,做过不少活计,生活自由而辛苦,是最难忘的一段日子。这段时间里还是爱着文学,除了不断地找一些同好的朋友互相学习和取暖,还要忍住一个念头时不时地就要从心底萌发:找一个文学师傅。
只要听到了哪个地方有个年纪稍大的、有过一些文学经历的,我就要跑去看一看,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提出拜师的请求。曾经有过一两次差不多眼看就要成了,只因为两次拜师所遭受的打击,最终还是没有开口提出。除了这个原因,另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我对他们能否长期当成师傅还多少有点怀疑。首先是长相:我印象中师傅的概念是由第一次求师的经历形成的,即这个人要体体面面像个老师的样子才行。第三次拜师不成的那一位虽然并不高大,像个老太太似的,但样子总算和蔼可亲。而后遇到的都不尽如人意,有的油胖胖的有的举止粗鲁,反正都不太合乎老师的概念。
有一个很大的机会说来就来了,这一次真是上天对我的恩赐:有一天我正在一个村里的朋友家玩,突然听说这里来了一位百年不遇的人物,他是一户人家的亲戚,以前是在某大出版社工作的,如今因为思想问题而离职了。那户人家正在招待他,这会儿正在炕上喝酒——照理说我应该在人家酒席结束的时候再去拜访,可因为实在等不得,就让人领着进了门。
那人真的是与常人大不一样:穿了灰色中式衣服,戴了黑色宽边眼镜,面庞白细,文雅无比。他吸烟,使用透明的长杆烟嘴。我把一叠稿子捧上去。他放下筷子,耐着性子当场读了几篇,很快对旁边的人、也是对我,说出了一句永远令人难忘的话:“有才。不过真要成熟,还要十年。”
他怎么就不说九年?或者再短一点,八年不行吗?十年,这是多么漫长的一段日子啊!
那天我兴奋不安地呆在他身边许久,直到他的离去。自然没敢提出“拜师”二字。他走了,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一直到上大学之前,我始终没能拜上一位文学师傅。但是上了中文系,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老师。这真是我的幸运。
大地上的文友
我上大学之前没能成功地拜师,却得益于形形色色的文友。这是一想起来就要激动的经历。那时我在山区和平原四处乱跑,吃饭大致上是马马乎乎,有时居无定所,但最专心的是找到文学同行。我在初中的文学伙伴离我很远了,并且他渐渐知难而退,常常是有心无力了。一说到写作这回事,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的人,他们都叫成“写书”,或者叫成“写家”,说:“你是找写书的人哪,有的,这样的人有的。”接着就会伸手指一下,说哪里有这样的人。
我在县城和乡村都先后遇到过一些“写家”,这些人有的只是当地的通讯报导员,有的是写家谱的人,还有的是一个村子里为数极少的能拿起笔杆的人。真正的文学创作者也有,但大多停留在起步阶段,就是说一般的爱好者。他们年龄最小的十几岁,最大的八十多岁。
不论这样的人住在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只要听说了,就一定会去找他。有一次我知道了一个真正厉害的“写家”,他住在一座大山的另一面,就起早背上吃的喝的翻山去找了。原来这是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白发白须,不太愿意说话。他年轻的时候在城里呆过,所以算是经多见广的人。村里人都说他“文化太大,不爱说话”。他仔细问了我的前前后后,又翻翻我的“作品”,这才多少接纳了我。
原来他正在写的书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是“三部曲”。他将其中的“一曲”给我看了,我发现是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的,主要记载了一生的经历,夹叙夹议。他说这叫“自传体”。其中我记得最有趣的是写当学徒的一段:东家女儿看上了他,他至死不从,以至于半夜逃离……“这闺女原是很美的,”他在一边解释说。
我照例坐下来读了自己的作品。他闭着眼睛听下来,像吃东西一样咀嚼着,又吞咽下去。这样半晌他才睁开眼,说:“你好歹毒啊!”
我吓了一跳。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是在表达一种极度的赞扬。他伸手抚摸自己摊在炕上的作品,说:“你看,我写得多歹毒啊!”
那些年我发现散布在山区和平原的各种“写家”可真多,他们有的富庶有的贫穷,有的年纪大有的年纪小,但一律酷爱自己的文学:写诗、散文和小说;有的还写戏剧,写好之后就在自己的车间或村子里演——看他们自编的戏剧简直有趣极了,那些特别的情节和场景永远都忘不了。有一次我被一位山村里的黑瘦青年邀请,说今夜村里就上演他编的一部大戏。
那出戏的演出离现在几十年了,记忆中内容大致是与村里坏人斗争、群众取得了胜利之类。记得最清的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手拿一个大红苹果从台子一侧上来,而另一边是一对青年男女亲热地上场。“二流子”斜眼看着那边的两个人唱道:“我手拿大苹果,她爱他不爱我……”那婉转悲切的唱腔让我一直不忘。我无比同情那个失恋的“二流子”。
还有一次我住在一个小村里,房东的女儿恰巧就是一个“写家”。她刚十七八岁,公社广播站就已经播发了好几篇稿子了。她胖胖的,穿了大花衣服,平时爱说爱笑,只是一写起来就伏在桌上,谁也不理,一边写一边流泪。我们交换作品,她喜不自禁,一边看我抄得整整齐齐的稿子一边红脸掩面,说:“哎呀哎呀,你可真敢写啊!”我知道她看到了什么:那是写青年男女刚刚萌发的、若有若无的情感,是这样一些段落。
我所经历的最大的一个“写家”是在半岛平原地区。记得我知道了有这样一个人就不顾一切地赶了去,最后在一个空荡荡的青砖瓦房中找到了他。他几乎没怎么询问就把我拖到了炕上,幸福无比的样子,让人有一种“天下写家是一家”的感觉。他从炕上的柜子里找出了一捧捧地瓜糖,我们一块儿嚼着,然后进入“文学”。他急着先读,让我听。可惜他的作品实在太多了,一摞摞积起来有一人高,字数可能达到了一千万字以上。这个人多么能写作啊,这个人的创作热情天下第一。为了节省纸张,那些字都写得很小。
天黑了,他还在念。一盏小油灯下,他读到了凌晨,又读到窗户大亮。奇怪的是我们都毫无困意。
那一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大写家”,是一位必成大事的文学兄长。他大我十多岁,结过婚,只因为对方不支持他的写作,他与之分手了。他曾给我看过她的照片:圆脸,刘海齐眉,大眼睛,豁牙,笑得很甜。
分手的时候我在想,为了文学而损失了那么好看的一位女子,这值不值呢?想了一路,最后肯定地认为:非常值。
书痴今何在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变了。与更年轻的人谈那些文学往事,他们会觉得一切都像梦境。那些写书的痴子今天哪里去了?有的存在,有的没了,不知哪里去了。活着的,不一定像过去一样写个不停。死去的,活到今天就不知会怎样了。
这些年来我见过几个以前的文友,无论时下的境况如何,谈到过去的情景,无不神情一振。有的无论如何也打听不到下落了,他们不是像当年一样在大山的那一边,而是隔开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比如说一个在七八十年代渐渐有些作品发表的人,几年后投身商场,如今音信全无。我问他最密切的一个朋友,对方说:“不知道,也许去了海参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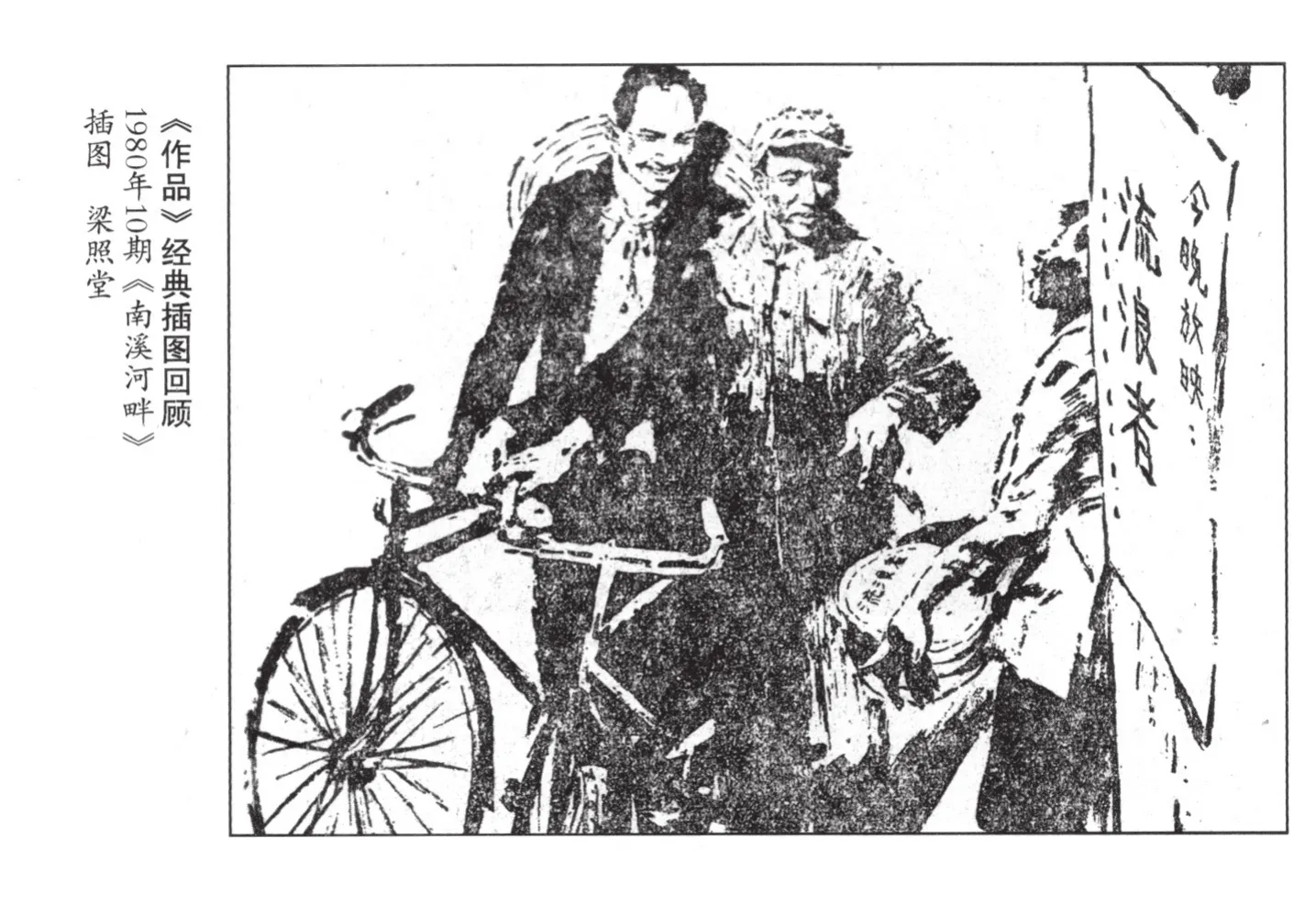
对半岛人来说,“海参崴”既是确指俄国远东的一个城市,又是闯到关外更远更远的一个缥缈的指代。
那个边写边哭的姑娘嫁了一个远洋船长,船长脾气不好,喝了酒就打她。她在痛苦中写了一些诗,都是爱情诗。原以为她爱上了别人,最后才知道这些诗都是写给自己男人的——他越是打他,她就越是爱他。她认为男人打老婆,是半岛地区不好的习俗,不能全怪男人;另外,她认为男人生活极不顺利,自己又无法帮她,实在亏欠了他。
那个写“三部曲”的老人早就去世了,他的后代不愿提那些往事,当我把话题转到这上边来,对方就把话岔开了。
我一度最思念的就是那个写了一千多万字的人,但几次都没有找到。后来终于见面了,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整个人虽然年纪很大了,但剃了板寸头,两眼炯炯有神。原来他已经做了一家公司的老板,虽然公司不大。问起他的书怎样了?他说:“书?好办。等我挣足了钱,就把它们印出来,印成全集,精装烫金!”
他伸直两臂比画,那就是全集的规模。
最不愿提及的是初中时候的文学伙伴。他就是与我第一次进山里求师的人。许多年来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可是热爱文学之心毫无改变,只是写得不多。我们见面时,他已经因为两次中风卧在了炕上,用最大力气握住我的手,摇动,说话断断续续:“咱老师……咱老师,和我一样的病,他走得更早……”
原来他还在怀念大山里的那个人。是的,尽管我们只见过他一次,但他毕竟是我们的第一个老师啊。
文学让我们更为珍视友情,朋友之间,师生之间,所有的情谊都不能忘记。仅凭这一点,文学也是伟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