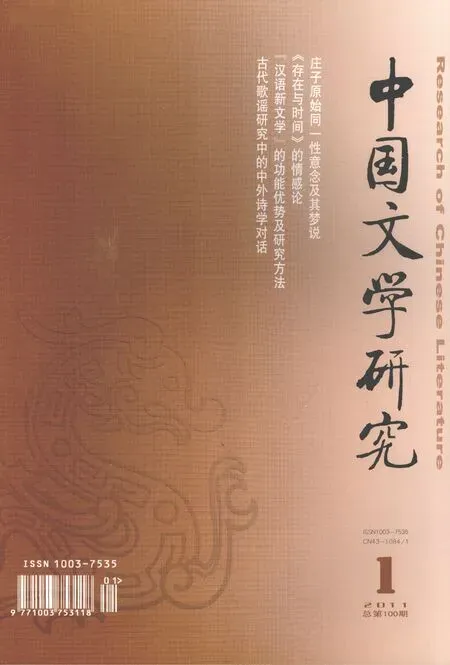论竟陵派诗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的离合
曾肖
(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在明末文坛崛起,得力于钟、谭二人对《诗归》独具匠心的选评及诗学理论的新颖奇特,以及“竟陵体”诗歌别具一体的风格特征。钟惺、谭元春的诗歌成为明末诗坛众人争相追慕、摹仿的典范,人称“钟谭体”、“竟陵体”或“钟伯敬体”。陈子龙有诗《遇桐城方密之于湖上归复相访赠之以诗》其二:“汉体昔年称北地,楚风今日遍南州。”描述了“时多作竟陵体”的现象〔1〕。竟陵派的诗歌风格及作品显示出来的文学思想,也是竟陵诗学的一部分,与竟陵派的诗学主张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一、竟陵诗学的理论倾向
公安派的“性灵”说以新变的姿态打破了七子派的牢笼,成为晚明诗坛的主潮。但是,其诗学主张的片面、偏激的弊端日渐显露,真率、鄙俚的诗风并行,“譬如百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2〕。竟陵派有意纠偏,救公安派“独抒性灵”之失,提出一条学古与性灵相结合的道路,用诗歌选本的具体实践来昭示自己的诗学观念,赋予“性灵”说新的内涵。后人评曰:“钟谭一出,海内始知‘性灵’二字。”〔3〕竟陵派标举“古人之精神”,追求“灵”与“厚”结合的审美境界。传承公安,又反对公安,竟陵派的诗学主张表现出重灵、求奇的特点。
特点之一:重静重灵。公安派从心学末期的狂禅之风获得离经谩教、张扬个性的精神,提出抒发真性情的性灵说,形成秀逸自然、活泼诙谐的诗风。竟陵派处在这股性灵文学思潮之中,同样主张真性情,但在行为方式上从洒脱随意的张扬转为孤芳自赏的内敛。以“孤衷峭性”、“幽情单绪”、“孤行静寄”的隐逸心态,钟谭提出了“静与厚”、“灵与厚”相结合的新性灵说。静、灵,指的是幽静、空灵的诗境,有着佛光道影的痕迹。静的诗学内涵与道家的“虚静”、佛家的禅定有渊源关系,灵亦与仙佛有关。“静”在道家哲学中指万物本原的虚空澄明状态,在文论中指主体在审美观照或创作活动前的宁静灵明的精神状态,在竟陵诗学中,则指诗歌静深清幽的美学风格,具有空、明、幽、奥、清、旷、远的美学特征。静能体物入情,悟理观妙,静能虚空生灵、幽清致远。“静与厚”结合的诗歌,表现出静远、幽厚、孤深、婉媚的风格,有温和深厚的特征,又有空灵清淡的一面。“灵”包括了“灵心”、“灵性”和“灵气”,指的是心思细巧、机敏、聪慧、秀颖的人物个性气质。竟陵诗学的“灵”强调神秘奥妙的一面,重视个体的独特性,灵是独特的生机与意趣,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诗歌风格,表现出清秀、畅快、新警的美学特征。“灵与厚”结合的诗歌,按照钟惺在《与高孩之观察》信中所言,主要有两类:一是平而厚者,代表作是《古诗十九首》和苏李诗;一是险而厚者,代表作有汉代的《郊祀》、《铙歌》和曹操的乐府诗。这两类诗浑然天成,厚中有灵,前者平和厚远,后者险奇幽厚。它们能够达到厚的境界,是由于作者保持灵心,读者养气,以求其厚。在这里,钟惺提出从灵入手,由灵入厚,达到“灵与厚”的结合,强调了灵的重要性。《诗归》的选评求“古人之精神”,标举古人的性灵之言,同样体现出对“灵”的重视。明遗民贺贻孙既肯定钟谭《诗归》的大旨在于“厚”字,又指出:“钟谭所选,特标性灵。”竟陵派过于求灵重灵的倾向,具体表现为诗歌风格的“清新而未免有痕”。钟惺在《与谭友夏》的书信中承认竟陵体清新而有痕的特点,这是追求诗歌隔绝尘俗而难以避免的结果,“我辈诗文到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即过于求“静”求“灵”而流入新奇、显露刻划的痕迹。由此来看,竟陵诗学理论与诗歌风格的倾向是相一致的。
特点之二:求奇求奥。竟陵派为了纠正公安派带来的肤浅、平易的诗风,刻意追求奇奥的诗风。钟惺在《文天瑞诗义序》中指出“诗之为教,和平冲澹”,接着说:
而奇奥工博之辞,或当别论焉。然秦诗《驷驖》、《小戎》数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长杨》、《校猎》诸赋所不能赞一辞者。以是知四诗中,自有此一种奇奥工博之致。
钟惺肯定《诗经·秦风》之《驷驖》、《小戎》数篇虽不合于“和平冲澹”的诗教,却自有一种“奇奥工博之致”。他认为《雅》《颂》之言奇奥,解读《诗经》的学者不能畏难就易,以“和平冲澹以文其短”。“险而厚者”就包含有奇奥之意。“奇”、“奥”是竟陵诗学的重要概念,钟、谭品评《诗归》颇为留意奇奥诗风。钟惺评乐府古辞《华熚熚》曰:“郊庙,登歌事鬼之道也。幽感玄通,志气与鬼神接,肤语文语,如何用得?汉人不学雅颂,自为幻奥之音,千古特识。”“其奇奥处,不及《雅》、《颂》。”在评后人拟《古诗十九首》,钟惺指出“别求奇奥”者为高。谭元春的《环草小引》曰:“诗固幽深之器也。然而幽近寒,深近鬼。高流饥病,又求至于寒与鬼而后止,往往堕而不悟,悟而不悔,吾愿示之以六瑞。”指出诗歌本是用来抒写幽深风格的文体,但要避免堕入寒、鬼的境界。从“清物”论到“幽深之器”论,可以看出竟陵派追求的诗歌风格由清新而流入幽渺、深奥。四库馆臣认为“竟陵标幽冷之趣”(评《明诗综》),语带贬抑,却是针对钟谭二人刻意追求奇奥、深幽、僻冷的特点而言。钟、谭的诗风亦表现出求深求奇求奥的倾向,多写奇险幽静的山水景物和孤衷峭性的人物,营造了孤静、幽深、僻冷的意境。施愚山在《与陈伯玑书》中指出钟惺诗“可谓之偏枯,不得目为肤浅”,陈允衡在回信《复施愚山先生》中指出伯敬“文气多幽抑处”〔4〕,看到了钟惺诗幽冷深奥的特点。
竟陵派偏重静灵、幽深、奇奥诗风的美学追求,遭到后人的纷纷非议。无论钱谦益“深幽孤峭”的说法,或是四库馆臣的屡次批评:“竟陵标幽冷之趣”,“天门钟惺更标举尖新幽冷之词,与元春相唱和,评点《诗归》,流布天下,相率而趋纤仄”(评《岳归堂集》),指出《诗归》“大旨以纤诡幽渺为宗”,这些议论虽有以偏概全的缺点,却也抓住了竟陵派的痛脚。
二、竟陵派的诗歌风格
钟惺、谭元春的诗作,按题材来分,主要有写景纪游、写人纪事两大类。钟谭的写景纪游诗,选择的山水景物多险峡峭壁、清潭小舟、冷月寒梅等景物,以夜景、月景、雨景、雪景、秋景、舟景为主。如钟惺的《瞿唐》、《巫峡》、《西陵峡》、《中秋雨后月》、《深夜舟进》、《舟雨》、《五看雪诗》、《雨后灵谷看梅花》等;谭元春的《观南岩一带奇岩歌》、《黄成玉宅看灯下红梅》、《途中新月》等。景物往往具有幽渺、险怪、清静、空灵、高洁、细微的特点,如钟惺的《小孤山》:“是峰瘦且特,名曰小孤宜。石筍何曾蒂,盆莲只一枝。禽鱼殊所视,形影共为疑。水与之周始,烟无可蔽亏。登焉堪四面,过者不多时。流峙相持处,舟航未敢迟。”描写了小孤山瘦骨嶙峋、特立孤寂的形象。再如《宿乌龙潭》:“渊静息群有,孤月无声入。冥漠抱天光,吾见晦明一。寒影何默然?”描写乌龙潭静谧、沉寂、空灵的夜景。有少数诗歌描写高山、云霞等壮丽景色,如钟惺的《雨行巫山》:“我行近巫山,欲识巫山面。此峰名十二,一峰了不见。白云如积水,怀山浩似瀚。云满谷皆波,两崖才若岸。”景色壮幻而又奇险无比。
写人纪事诗主要是描绘人物形象、记述交游友情,如钟惺的《蔡敬夫自澧州以诗见寄和之》、《与弟叔静过友夏兄弟寒河居》、《哭雷何思先生十首》等作。与钟惺相比,谭元春这类诗的数量更多,这与钟好静、谭喜游有关,如《赠冯宗之》、《同伯敬孟和坐茂之榻上》、《哭江伯肯师》、《访邹彦吉先生山庄谈宴两日夜作》、《寄九江陆君启使君诗未达重有此寄》等。诗中人物多是志趣相投、性情相近的友人,具有高洁的操行、独立的人格和清远的风韵。钟惺在《梁无他水部自潘景升处投诗见赠赋答》中自言有“严冷名”,但他对友人却情深义重,如《寄吴康虞》:“旧识南中半,公还自古人。意与林壑近,诗取性情真。谭子多幽鉴,称君有远神。友朋山水理,言下特津津。”肯定了谭元春对吴康虞的称赞,指出吴为人好清静、为诗抒真情,以及相互之间的友情。再如《访元叹浪斋》:“读诗交已定,相访庶无猜。室与人俱远,君携我共来。庭空常肃穆,树古自低徊。积学诚关福,居心亦见才。棲寻钦旧物,坐卧出新裁。寒事幽堪媚,冬怀孤更开。鸟声园所始,灯影漏先催。静者方成悦,冰霜照夜杯。”钟惺此诗描写了与友人徐波之间的交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徐波孤清幽静心怀的赞赏。钟、谭也称赏英雄人物匡世救国、心怀天下的侠义精神,如钟惺称赞先师雷何思为“真豪杰”、“真人”。还有部分是以家庭亲人或女性为对象的诗歌,如钟惺的《见姬人临妆看镜中腊梅花》、《新姬手植盆兰引》、《戏题燕姬新入舟》等;谭元春的《除夕同诸弟妹侍老母守岁率尔命篇》、《江夏女客行》、《咏江上妇人看侍儿浣簟》、《拾松枝妇人》等。钟惺笔下的姬人既具有高洁如梅兰的精神,又有深情;谭元春笔下的女子形象亦是有情有义之人。这类诗歌多情感真挚,描绘生动,语言朴厚。还有小部分是通过写人纪事来抒发感慨时世之情,数量较少。钟惺有《邸报》、《王文肃公专祠诗》、《送南大司马黄公移督戎政时有辽警》;谭元春有《七月初一夜宿天界寺观老僧登座施食懺度亡辽将士春亦附荐先魂稽首悲感为之篇》等,抒发了诗人感愤时事、悲慨忧伤的情感。
总的来说,钟、谭诗主要表现出清幽、苍朴的艺术风格,主要有如下特色:其一,诗歌的意象多是带有孤、幽、清、细等特点的景物和孤、静、洁的人物。常见的梅、兰、松、竹、水仙、红叶、海棠、芙蓉等植物意象,含有高洁的寓意在内。诗歌主要传达了诗人幽微的审美感受,如钟惺《碧云寺早起》:“人语翠微闻启门,离离残露湿初暾。行经绝涧数花落,坐见半山孤鸟翻。月去寒潭林影换,云依闲砌草头温。与君莫厌频移榻,晨爽秋阴非一村。”隐约的人语、欲滴的残露、历历的落花、翻飞的孤鸟、潭中变化的倒影和天边的闲云,景物细微的变幻,尽在诗人笔下。二人观察山水景物的角度主要是及远,看幽渺之处;及近,看细微之处。人物多是志向高远、行止高洁的志士、侠士、名士和隐士。常见孤迥、独行的幽人形象,与他作伴的常常是山间或水中的一泓清月,夜里的一盏孤灯,抑或是二三素心人。如钟惺的《舟月》:“每旬无不见,每见辄云新。耳目何曾异,形神但觉真。入舟如好友,在水更宜人。别我更初半,孤灯又一身。”诗人与月亮每次见面,俨然好友般亲切无间;月隐之后,只剩孤灯映照下的孑然一身。幽人的形象,是诗人自己的艺术写真。喜静的钟惺常独游、静坐、赏花,“寒吟抱影微”正是他的形象写照〔5〕。友人也是超拔流俗之人,如钟惺《寄答尤时纯》:“满腹精神堪独往,半生气侠讳人知。行藏亦自超流俗,士所当为未止斯。”即使是女子,同样不同于流俗,如谭元春《集李客星伯仲宅隔帘听侍姬征曲》:“中有一姬不见月,闭目凝想清喉竭。隔屏偶闻弦索响,取弦学弹惊林樾。”其二,诗歌多是一种凄清、幽邃、僻冷的审美意境。描写夜景、月景的诗作最容易营造出静谧、幽深的气氛。一首首山水景物诗仿佛一幅幅冷色调的水墨画,如钟惺的《月宿天游观》、《西湖早起》,谭元春的《山夜闻鸦》、《月泊洞庭》等。试看钟惺的《舟晚》:“舟栖频易处,水宿偶依岑。岸暝江逾远,天寒谷自深。隔墟烟似晓,近峡气先阴。初月难离雾,疏灯稍著林。渔樵昏后语,山水静中音。莫数归鸦翼,徒惊倦客心。”夜色渐深,烟雾已起,初月乍现,疏灯忽见,寒鸦归巢,倦客心惊,组成一幅江边暮景图,寂静、清幽的意境,流动着诗人异乡思归的忧郁和感伤。其三,诗歌往往做到情景交融、情理并至。如钟惺的《见月得起句因而成篇》:“寒月照欢怨,清川流盛衰。众形各自取,真宰亦何知。钟应山摧后,渠成水到时。此中机彀幻,未易使人思。”谭元春的《山月》:“清光不厌多,高人不厌闲。心目周境外,置身于其间。上山月在野,下山月在山。”两诗都是以月为主题的诗,都融合了情景理于一体,钟诗借寒月、清川的物象来抒发了人生变化的感慨,以及当中蕴含的哲理;谭诗借山月发高人之闲情、说浅显的道理。其四,诗歌的语言峭拔、新奇,多用虚字。钟谭诗中常用的字眼有“孤、细、空、静、枯、幽、清、深、冷、寒、森、凄、残、一、峭、悲、纤、远、灵、新、虚、僻、渺”等,多用来形容“月、烟、雁、雨、松、山、泉、气、影、光、魂、情”等。如钟惺写山月夜景,《山月》:“山于月何与,静观忽焉通。孤烟出其外,相与成寒空。清辉所积处,余寒一以穷。万情尽归夜,动息此光中。”《竹月》:“何为竹影之,反益觉灵虚。”即使是久游之后刚刚到家之时,钟惺的喜悦仍然带着孤独、沉静的落寞,《到家》其一:“携幼慰幽独,尊酒适有余。”谭元春的诗歌也有相似的特点,如《病中同茂之寻菩提场》:“僻径渺无际,君来约细寻。香花行处是,老树到门深。”常见的虚字如“亦、何、之、已、来、其、如、不、或、欲、但、遂、而、乃、以、即”等。虚字的运用一方面使句式新奇、句法多变,另一方面又会造成诗句僻涩、诗境扞格。如钟惺《浔阳经曹能始庐下怀寄兼贻梅子庾》:“且更作一想,以豁今所思。”谭元春《道乾之北庵不值值吴彦先一宿而去》:“有约亦何久,相逢如此难。赖兹僮意洽,能使客心安。”每一句都用副词来转折语气。
从诗歌的取材、立意、语言、境界及风格来看,钟谭的实际创作透露出来的思想,主要是摒弃浅薄俚俗的诗风,转向幽深清静的诗歌路子,和他们提出的诗为“清物”论相一致;基本上符合“静与厚”、“灵与厚”结合的主张。诗歌风格过于尖新、偏仄之处,也和竟陵诗学过于求灵、求奇、求奥的倾向相符合。
三、“深幽孤峭”与“灵与厚”的关系
清初,竟陵派衰落,钱谦益用偏激的语气来批评竟陵派“另立深幽孤峭之宗”。“深幽孤峭”四字,用来形容竟陵派诗歌主要的风格特色,堪称“狠而准”,论调激烈,却得中肯綮。但钱氏把它作为竟陵派的诗歌宗尚,有以偏概全、混淆之嫌,忽视钟谭追求“厚”的美学宗尚以及丰富的诗学思想。
所谓“深幽孤峭”,钱谦益解释曰:“如木客之清吟,如幽独君之冥语,如梦而入鼠穴,如幻而之鬼国,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余尝论近代之诗,抉摘洗削,以凄声寒魄为致,此鬼趣也。尖新割剥,以噍音促节为能,此兵象也。鬼气幽,兵气杀,著见于文章,而国运从之,以一二辁才寡学之士,衡操斯文之柄,而征兆国家之盛衰,可胜叹悼哉!”钱氏极力贬抑竟陵诗风,把“深幽孤峭”喻为鬼魅幽人的凄声寒魄,文字细碎,音调急促,鬼气阴森,秋意肃杀,“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表现出“贫”、“薄”、“僻”、“凡”、“昧”、“断”、“乱”等特点。钱谦益对竟陵派的抨击,其立论原因十分复杂,既出于个人的私心与喜好,也有易朝换代之后新的发展趋向与思潮变迁的影响。从今天的标准来评判,除却其中的贬义,“深幽孤峭”的含义切合竟陵体的艺术特色。幽、深、孤都是钟谭品评《诗归》的常用诗学概念。深幽是指竟陵派讲究清静的美学趣味的反映,诗歌内容多选择山水景物、孤独的人,意象萧瑟、孤单、清静,意境深邃、幽渺和细微;孤峭,是指诗人孤迥的性情和高洁的人格的反映,诗歌行文运笔的孤单之气、峭拔之势、幽冷之语。深幽孤峭的内涵,与钟惺追慕的“隐秀”相接近。深幽包含了情意的婉曲、深沉,意象的深静、细微和风格的深远、微妙,对应于“隐”;孤峭包含了韵调的孤高、凄清和气势的峭拔,对应于秀。竟陵的厚、灵的诗学内涵丰富,不同的偏向有不同的含义。厚有温厚、浑厚、深厚、柔厚、幽厚、朴厚、淳厚、厚远、笃厚、端厚等;灵有幽灵、灵妙、清灵、灵慧、灵动、灵变、灵奥、灵活、空灵等。隐与厚相似,有厚的婉曲,却少了厚的淳朴;秀与灵相似,有灵的警拔,却少了灵的妙。“深幽孤峭”与“灵与厚”相比较,深幽有厚的幽静深远、委婉曲折,却没有厚的真淳、朴实与浑沦;孤峭有灵的警策、清爽,却没有灵的空明。
由此看来,作为竟陵派诗歌主要风格特征的“深幽孤峭”和“灵与厚”结合的诗学追求之间有一定的偏离。钟谭笔下一些描写朋友间的交情厚谊诗,以及母慈子孝、兄弟友爱的家庭人伦诗,风格淳朴、浑厚。高世泰在《谭友夏先生乡贤檄》中指出友夏诗“篇关师友,则郑重流连;语涉昆弟,则缠绵悱恻”〔6〕,“深幽孤峭”显然不能概括这类诗歌的风格。但从竟陵派重灵求奥的理论倾向来分析,竟陵派的实际创作和它的美学宗尚又是相一致的。陆云龙在《钟伯敬先生合集序》中指出钟惺诗“疏爽气多,浑穆气少;隽永味多,醇醲味少;秀颖句多,古拙句少”〔7〕;朱之臣《寒河集序》指出“友夏至性远情,其为诗清微静笃”〔8〕;鉴庵的《序友夏》指出“钟诗餐幽吐秀,出手迅疾,似姑射仙子,嫌其骨节之太轻;谭诗猎异穷窈,朴少灵多,类衣白山人,恨其眼舌之都慧”〔9〕,这些评论都是针对钟谭诗灵多厚少、幽多朴少的风格特点而言,基本上属于客观中肯的评价。
竟陵诗学重灵求奇、竟陵诗风清新而有痕的特点,使一些只顾跟风的竟陵后学者取形略神,流入了过度追求“空灵”的不良状态,沈春泽的《刻隐秀轩集序》批评这些后学者“以寂寥言精炼,以寡约言清远,以俚浅言冲澹,以生涩言新裁”,诗歌“空则有之,灵则未也”〔10〕。观念对创作起指导作用,创作对观念则表现为响应或背离。竟陵派的创作显示出来的文学思想,与其诗学追求、美学宗尚之间存在离与合的关系。
〔1〕陈子龙.陈子龙诗集〔M〕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15.
〔2〕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A〕.珂雪斋集〔M〕卷三.上海:贝叶山房张氏藏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第六种,1936:87.
〔3〕鉴庵.序友夏〔A〕.谭元春.谭元春集〔M〕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53.
〔4〕藏弃集〔M〕.周亮工.尺牍新钞二集〔C〕卷十一.上海:贝叶山房张氏藏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第三十七种,1936:196.
〔5〕钟惺.访友夏不值自朝坐至暮始归〔A〕.隐秀轩集〔M〕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96.
〔6〕〔8〕〔9〕谭元春集〔M〕附录.上海:上海古籍社,1998:956、942、953.
〔7〕〔10〕隐秀轩集〔M〕附录.上海:上海古籍社,1992:604、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