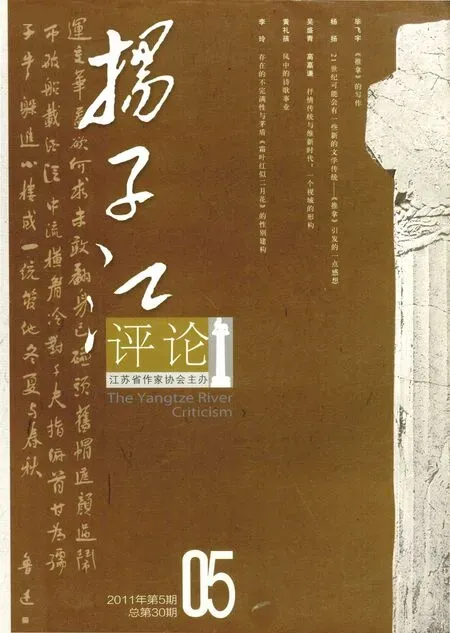风中的诗歌事业
黄礼孩
我越来越感到,编一本民间诗刊是多么地微不足道,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我做了很多努力,可是今天回头看看,它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我没有刻意去做一件事,也没有回避真正要来临的事情。诗歌是一种独立的圈内文化,她不热闹,把她当做朋友,内心自然有一种满足的喜悦。说起来,有一点像江湖,我们袖手在城市的一个小角落,呆在生活的边缘,面带微笑地编织那些与物质没有多大关系的诗歌。编民刊就成为自己小小的快乐,我没有想过愉悦他人,也没有想过要去改造诗歌世界。对于我来说,编民间诗刊,是对行将逝去的青春岁月的纪念,是一个人对自由的想象,是一个人对新理想路径的寻找。编刊物同时也是自我的启蒙和教育,更是他者力量对自身局限性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我也和刊物走上了相互完成的途中。
1999年秋天,我开始编《诗歌与人》。任何事情想象的时候总是美好的,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办民刊碰到的首先是经费问题。以往的民间诗歌刊物是同仁之间的园地,大家一起出钱、出力。我不想用你掏一百、我掏二百的方式来搞一本民刊。我把办民刊当成自己出版的著作来做,这种带有私人意念的办刊心理更能让我心甘情愿地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那点小钱花在上面。这就意味着我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在其他领域赚到钱,然后用这份钱来出诗刊。在广州,我去给别人做策划、写晚会串词、拍舞台剧照或编什么书,就这样赚到一些小钱。我想不起来,这些年是如何过来的,我只知道自己一刻不停地奔跑。奔跑是必要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全情投入,只有投入你才能深入生活的核,你才会获得人生的品质。虽然编民间诗刊与生存无关,但你不能否认它是一种人生的方式。
诗歌是一种自由的表达,能把诗刊做得多极致,就不要停留在粗糙的层面上。虽然说办刊是为了愉悦自己,但也得做得大气、时尚,具有诗学价值,对于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我曾给刊物取过几个名,但都不是很满意。广州学者林贤治先生曾办过《散文与人》,我喜欢这份以书代刊的杂志。广州有散文杂志还是不够的,还得有诗歌杂志。就这样,《诗歌与人》在此地诞生。没有人,也就没有诗歌,我们更多地是看重诗人的文本贡献和社会责任。从1980年到1990年,几乎所有的民间诗刊中没有一张诗人的影像。诗人永远躲在诗歌的背面。诗人为什么不可以像明星一样风风光光地在杂志上抛头露脸?把诗人凸现出来,这是我把刊物命名《诗歌与人》的另一个想法。
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是70年代出生的诗人浮出海面的前夜。他们在黑暗中涌动,在诗歌的洪流中挣扎。生于70年代,为自己的时代的诗人编诗刊成为我强烈的愿望。我综合诗人蒋浩等朋友的意见,在第一期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展》,没想到整个中国诗坛为之震动。接着我又推出第二期的《70年代诗人诗展》,70年代诗人以更庞大的气势,群体登上诗歌的舞台,成为中国诗坛最有力量的潮流。《诗歌与人》仿佛一夜之间受到关注,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当初的想法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行,并没有奢想就此产生什么影响,但我一直有一种松弛的状态,坚信做一些他人想不到的东西,会让诗人看到诗歌不一样的生存状态。
办了一、二期之后,《诗选刊》、《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官方诗刊在《诗歌与人》上转载诗歌。刊物有了影响,再去做其他事情就容易多了。最初,要组到全国各地诗人的诗歌很不容易。我通过一个诗人介绍另一个诗人的方法来组稿,蒋浩、安琪、阿翔等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不少他们认识的诗人。我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全国各地的诗人打电话或写信。我看过电影《阿甘正传》中的阿甘一天到晚奔跑,我与他一样有着某种相同的秉性,就是执着。但很时候,更觉得自己像堂吉诃德,仿佛是一个可笑的理想主义者。给诗人打电话的时候,我试图去打动他们给予优质的稿件。打电话,有时候也会约不到稿件。这个时候,拿着电话筒感到多么的无助和茫然。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心灰意冷时,也想过放弃这个诗刊。一个人编一本诗刊是非常繁琐的事情。琐碎之事,它容易把一个人陷入其中,产生厌倦的情绪。但第二天收到来自远方的一些诗人朋友的问候和祝福,我的热情又高涨起来,仿佛所有的困难不算什么。等到电信部门把上一个月的电话收费单寄来,我就傻了眼,电话约稿代价是那么高。今天的网络发达,约稿较为容易,但很多时候我还是以打电话来约稿,听听朋友们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记得诗人铁梅在新疆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我只记得你的声音,我觉得声音蛮好听的,有时候甚至怀念这种声音。”实际上,我是一个乡音很浓的人,我怕别人听不懂我的话而竭力把话表达得清晰一些,而铁梅的信像阳光照亮了我的心灵。也许诗人天生就是兄弟姐妹,让我在四海之内拥有极佳的人缘。
我办刊并不想固守在一种风格上,多元共生才是一个刊物的出路。这就有了后来与安琪合编的《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生于1969年的安琪,在我所认识的诗人当中,是一个狂热的诗歌分子。她不断地为“70后诗人”写文章呐喊,她也因此与“70后诗人”建立了友好的感情。安琪既不在“第三代”诗人当中,又不在“70后诗人”里,她感到自己还有他们那个年龄段的诗人有被诗歌史遗忘的危险,而整个中国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的诗人又是多么的优秀,但诗歌界没有给他们一种说法。把这些优秀的诗人团结一起,为这个群体做一点事情,成为我和她共同的想法,这就有了后来《诗歌与人》推出的“中间代”。因为这期专号,“中间代”这个名字在诗歌史册上出现,不管它是试图闯入,还是主动介入,它还是存在诗学问题的论争,“中间代”不可避免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
与安琪合作给了我新的思路。开放永远是一个刊物的个性,因为个人的充满局限性。这也就有了后来与布咏涛(江涛)的合作。布咏涛在深圳大学念的是中文系,但读书时她没有写诗。她毕业后在电台主持节目,一个偶然的机缘触动了她的情感,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了不少诗。有一天,一个朋友带着她的诗集给我看,我随意翻了一下,被一些诗篇所吸引。看到书中夹着一张她的名片,我顺手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牵出了我与她合作编女性诗歌的源头。布咏涛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女诗人,她对诗歌充满热情又不图功名,今天像她这样纯粹的人不多了。我在与安琪一起编“中间代诗选”的时候已想过要编女性诗歌诗选,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也许缘分没到吧。后来见到布咏涛,我们不约而同谈到女性诗歌,就这样我们合编了多期“女性诗歌”。
从早期的《中国女诗人大扫描》到《中国女诗人访谈录》、《最受读者喜欢的十位女诗人》、《新女性新诗歌》,到后来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女性诗歌在那段时间绝对是中国诗歌最美的光环。很长一段时间,男诗人总是埋怨我,为何频繁推介女性诗歌?其实我没有偏颇女性或男性,只不过女性诗歌从来没有这样被重视过。二十一世纪以来,发展最迅速的是女性诗歌,她们与男性诗人一起构成当下中国相对平衡的格局,但就女性诗歌评论家来说,没有太大的起色。也许,我会在这个层面多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提供新的平台。
说起来,我内心感激广州这座城市。广州是一座具有包容精神和务实精神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座城市因为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有相对独立的媒体而令人心生敬意。在广州生活十几年,这座城市的自由风格,也许已进入了我们的身体之中。在广州编诗刊,当然是我个人的事情,但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多时候是不言而喻的。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诗人,他们都过得实在而又不失诗人的激情。广州的老牌民刊《面影》创办十年,是一批批的诗人把它延续下来的。他们当中有警察、记者、老师、医生、公务员等人物。那时,他们都怀着对诗歌的热爱,你捐一百,我捐二百,把杂志办下来。他们白天都忙自己的生计,晚上有空的时候,大家集合在不同的地点看稿、聊天。小说家陈小虎的出租屋曾经是大家的一个临时编辑部。那时,每一个人拿着一叠来稿阅读,当有人找到好诗,就互相传阅,说出各自对此诗的看法,说出放在哪个栏目合适。这样的选稿会,其实也是另一种诗歌沙龙。每一次选稿会都进行到很晚,大家都舍不得离开。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又骑着自行车、摩托车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很多时候,看着他们消失在黑夜里的身影,我就莫名地感动,是什么让这些不甘寂寞的心聚集在一起,快乐地做着一本民间诗刊?那应是生命的梦想和激情,我们因为与诗歌结缘,诗歌成为我们潜在的渴望。
1997年,《面影》出十年纪念号。选稿就在我的单身宿舍里举行。那时,我住在广州歌舞团的一幢小楼里,一、二楼是开会的场所,三楼是一个小房屋,房间延伸出去的是一个阔大的阳台。阳台大得足以在上面开舞会。有一年中秋节,广州文艺界十几号人物在阳台上面过了一个快乐的中秋节。那时候,诗人世宾常在周末开车从广东的鹤山市来谈诗歌、谈人生理想;诗人吕约在一间中学教书,她有时也会带她的妹妹过来玩,还有全国各地来的朋友都会到我那里小聚。广西的诗人黄正崖还写过一篇《诗歌的阳台》的文章来纪录当年的青春岁月。佛山诗人张况多年后也写文回忆那段纯真的时光。
生活就这么过着。这么的一个地方自然成为编选诗刊的好场所。因为地方大,大家在上面唱歌、跳舞、喝啤酒、打牌什么的。有时候晚了,他们就在我那里横七竖八地睡着了,第二天,他们走的时候,留下一片狼藉。《面影》出十年纪念专刊后也就停刊了。《面影》算是一个有自己小小传统的民刊了,但即使办得不错,也逃脱不了自生自灭的命运。中国的民刊大都是因经费或者环境的艰难或激情的消退而渐行渐远,直至随风而逝。1998年我去北京大学进修,我所住的那幢诗歌的小楼也被拆掉,许多美好的回忆和往事都灰飞烟灭……
生活的变迁总令人生出许多感叹,但广州诗人的生活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与编诗刊也结下不解之缘,后来编《诗歌与人》,与我曾经参与过《面影》的编辑工作有着割不断的缘分。也许生活总是存在着种种可能,只要自己保持着一颗好奇的心灵,生活会给你奖赏。对于《诗歌与人》的命运,我没有过多地去想象,就像我们无法知道明天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意象一样。但只要还有想法,还有新鲜的思想和策划,我还编下去。
1997年,对于广东诗歌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生活在广州的青年诗人东荡子、江城、世宾、浪子、温志峰、巫国明和我联合出版了一本合集《如此固执地爱着》,由诗评家温远辉作序。这本书给多年寂寞的广东诗歌带来新的气息。这个群体逐渐走出多位有影响力的诗人。广州的诗歌生态也由此迈向一个自由、开放、尖锐和包容的境地。诗歌交流会时常举行,朋友们之间很多时候为一个观点争得脸红耳赤。在那里,我获得了很大的教益,东荡子运用诗歌语言的经验和技巧让我看到写作的多种途径。世宾的理想主义色彩也常感染着大家,他倾向于人在思想中应当承担更多。多年后,世宾、东荡子和我一起提出一个新的诗歌主张:“完整性写作”。我用两期《诗歌与人》来推出这个诗歌理念,包括诗歌文本和诗歌主张。我得说,每一种诗歌概念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但它的出现无疑也为诗歌的出路提供多种可能。完整性的主张是通过写作消除内心的黑暗,从而达到与世界对话与和解,并由此衍生出新的生命。“完整性写作”概念至今提出也有七年了,现在还有诗人和诗评家不断延伸这个概念,丰富和完整它。
短时间内,《诗歌与人》先后推出“70后诗歌”、“中间代”、“完整性写作”,一时间刊物仿佛具有跨越的能量、一种冒险的能量。除了群体性的文本推荐外,我也看重个人的文本推介。没有个体自然谈不上群体。俞心樵的诗歌才情横溢,他早期在清华园写的诗歌充满英雄主义的人文色彩,具有个案的意义,也有范本的价值。《诗歌与人》在出版了他的专号后,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又回到读者的视野中来;兰州诗人古马的诗歌写作很有特点,在西部是一个文本有异于他人的诗人,很多诗评家为他写了大量的评论和文本细读,敦煌文艺出版社联合《诗歌与人》为他出版了《古马:种玉为月》,这也是国内出版社首次与《诗歌与人》合作;东荡子的诗歌无疑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赢得诗歌界太多的重视,诗人像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他的命运。《诗歌与人》给东荡子做的专号是散文专号,他的散文很有生活的趣味,又有个人深刻的体会,诗人散文成为观察一个人写作的一面镜子;朵渔是70后诗人中少有担当的诗人,他的诗歌具有切身的痛感,他坚守个体理想、秉承汉语诗歌的尊严和创造,给予当下更多的警醒。有一年的“柔刚诗歌奖”由我来主办,我把奖颁给了他。朵渔虽是“下半身”的灵魂人物,但他的写作理念却有别其他诗人。朵渔一直没有出版过他的个人诗集,我以《诗歌与人》之名为他出版了《追蝴蝶:朵渔诗选》,除了集中呈现他多年来的诗歌之外,也期待这是一个关于70后的诗歌个案研究;此后,《诗歌与人》也给摩洛哥女诗人法蒂哈·莫奇德出版过一本集中文、英文、阿拉伯文三种语言在一起的专号,以此拓展语言的多元性。像这样的个人诗歌文本的推介,以后还会做。因为《诗歌与人》的影响力,很多诗人希望能在《诗歌与人》推出专号,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比在出版社出版还有意义。正是因为众多诗人的看重,我反而更为慎重。任何刊物,没有节制的话都会损害到刊物的自身。尽管如此,但在出版的系列作品中,还是存在一些不甚理想的专题,自我感觉对不起刊物。
也正是这样,对于一期专题的策划,更需要深思熟虑,评估它的价值和影响。我曾经提出,《诗歌与人》要去出版别人不关注或遗忘的部分。比如《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没有人来编过。后来,我与诗人陈陟云编的《新诗九十年序跋选集》也成为一本惟一的书,它是另一种中国现代诗歌史。这个选题的资料非常难找,中国社科院的刘福春老师曾经给我提供过无私的支持。如这类选题具有惟一性的专号往往会赢得研究者的青睐,听说有些人居然在孔夫子网上书店以高价出售《诗歌与人》。《诗歌与人》尽管印量在1500-2000本之间,都是赠送、交流,覆盖面很小。所以《诗歌与人》提出的口号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通过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去传播诗歌,当然还有图书馆。一本刊物除了竭力挖掘被忽略的题材外,它对于时代也应该去纪录。2008年5·12汶川地震,《诗歌与人》及时出版了一期诗歌专号,结果里面很多诗歌入选当年的年度选本。汶川地震的诗歌井喷是一种现象,问题很多,对此,《诗歌与人》还专门出版了一期《5·12汶川地震诗歌写作反思与研究》,这期专号被一家诗歌机构评为“年度十大事件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诗歌与人》在地震发生之后,第一时间联合“诗生活”网,在广州和深圳举办了四场诗歌朗会,为灾区捐了八万多元。虽然钱不多,但它是《诗歌与人》作为“社会公民”的一种担当。
因为时代的变化,民刊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对民刊的定义也就不一样了。显然,这不是一个办民刊最好的年份,人们更多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看做“民刊之春”。在东欧,一些国家则在五十年代出现以民刊表达自我声音的浪潮,他们把在民刊上的写作视为“萨米亚特”。这个隐喻来自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写的一部科幻小说:在遥远的星球上有一国家,那里的居民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们之间惟一的谈话。官方的宣传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水面呼吸被看做是犯罪。结果,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能到岸上生活。多年后,另一位波兰诗人巴兰察克在文章中引用这个故事,他说一个生活在水下的人想浮出水面,是因为他的肺受不了,他想呼吸。自此,萨米亚特写作便成为东欧地下写作的一个符号。那个时候的东欧充满冲突和变化,陷入乌托邦迷思中的知识分子醒来,他们渴望对现实有更直接的表述,争取自由的先锋力量。在《地下》一中,对萨米亚特有深入研究的景凯旋教授说:“对东欧知识分子来说,自由不仅是一种人的权利,更是人的存在。因此,他们才会将其写作面向公众,而不是当权者”。
时间过去半个多世纪,不知中东今日的“萨米亚特”如何了,而中国当下的民刊已不是当年的民刊。现在的民刊已难觅当年呐喊、突围的身影。所以当人们还拿八十年代民刊的标准来看今日民刊时,多少是失望的。做出改变应是所有民刊的出路。也正是以往的和现在的裹挟,危机感一直伴随着《诗歌与人》。因为个人的局限,这本刊物无疑也受到主编者个人气味的影响。在我看来,国际视野一直是我们所缺乏的。尽管《诗歌与人》策划了《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国外五诗人诗选》等外国选本,但还是远远不够。带着危机感去办民刊,这种适度的紧张有助于抓住一些东西。那个时候,我不满足于只是发表中国一些民间或知识分子的声音,在同一时空下,还有世界诗人的声音。在与我们同时代用别的语言写作的诗人,他们在思考什么?呈现什么?这是我所关心的。
2005年在给葡萄牙诗歌大师安德拉德做一期诗歌翻译专号时,我突然意识到是时候给刊物赋予其他的诗歌元素了。这一年,我设立“诗歌与人·诗人奖”,旨在给那些在漫长岁月中越写越好,源源不断推出光辉诗篇的诗人进行褒奖,意欲让更多的人沐浴诗歌精神的光芒,为人类的智慧和心灵的丰盈做出努力。这个奖我没有设立评委会,只有我一个人来做评委。我知道,别人会质疑这一做法,担心它的公平、公正和专业。我们知道任何奖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国内有些奖黑箱操作是路人皆知。我不想模仿所谓的权威,也不想变成小圈子,再说,我也没有多余的钱付评委费。抛弃集体举手票决的形式,选择独立的评奖品质,远离利益关系,推出有灵魂感应的文本,这是我个人的愿望。
不够诱人,但我们推出诗人的文本和给予诗人高贵的领奖仪式,这样的方式也不是哪个奖都具备的。第一届获奖诗人为葡萄牙诗人安德拉德;第二届是中国七月派最后一位诗人彭燕郊;第三届是翻译家、诗人张曙光;第四届是女诗人蓝蓝;第五届是俄罗斯诗人英娜·丽斯年斯卡娅;第六届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就在我写这篇稿时,2011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意想不到的是特朗斯特罗姆荣获此奖。很多朋友来信、来电祝贺我,都觉得我有超前的眼光,在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颁奖给这位世界大师。一年之内,两个奖项颁给同一个人,很多人觉得太巧合了。感谢上帝给我这份礼物。但我也相信,如果没有我前面十二年得努力,再好的运气也不会来光顾我。从第一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的获得者、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安德拉德,到第六届“诗歌与人·诗人奖”的获得者、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特朗斯特罗姆,“诗歌与人·诗人奖”与诺贝尔文学奖有着某个频道的同步,而我更愿意把它看做一种普世价值的认同。我以前写过一篇文《向世界输出有价值的思想》,《诗歌与人》设立这个自由的民间诗歌奖,它奖励的就是“世界范围内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和人”,我把此视为个人小小的行动,也渴望汉语诗歌自信地融入世界诗歌的潮流中,把自身有益的新思想输向四面八方,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应得尊严和尊重。
尽管《诗歌与人》已取得很好的开局,尽管我激情满怀,但面对现实也有耗尽的时候。每一个办过民刊的人都知道,办民刊是吃力不讨好的活。《诗歌与人》几乎是以我个人一己之力在艰难地坚持着。不知内情的江湖,常流传我是富翁的说法,因为按照正常思维,一个不富有的诗人不可能干这等傻事。对此,我也没说什么,一笑而过。这些年因为刊物的影响力,我常接受媒体的采访,他们试图挖出我在十几年来当中最感人的事件,有没有砸锅卖铁、有没有到卖血的地步?还好,还没沦落到那样悲惨的时刻。但痛苦的时候也有,比如当诗人说他们买了什么名牌好车、买了几百平方米的房子,内心就有所波动。十多年来,如果把办刊的钱加起来用来买房,也可以买到一套了;花在刊物上那么多细碎的时间,如果用来写作,也会多写出几本书了。这样的时候总是沮丧的,好在活到这个份上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现在编刊物的速度减下来,不再为编而编。很多时候,常常怀疑自己编刊物的意义何在?这样做有益诗歌的发展吗?它的诗文本和诗价值在哪里?质疑常让我陷入新的困顿之中。后来有些时间,我常常游离于诗歌之外,而徘徊在各种艺术行当之中。原来艺术世界大得很,有趣的东西多着呢。反过来,各种艺术因素又激活了我对诗歌的认识。
当然说得好听一点是,编民刊也是一种异质混成的行为。它除了内行的眼光、专业的精神、宽阔的心胸和一种天然的禀赋外,独立和担当依然是它远飞的一对翅膀。在我看来,编诗刊在另一个层面上改变了我的生活,它是一对空中的翅膀,一片风中的叶子,一滴深夜的露水,一束闪烁的阳光……其实,它什么也不是。很多时候,自己只是一个堂吉诃德,走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