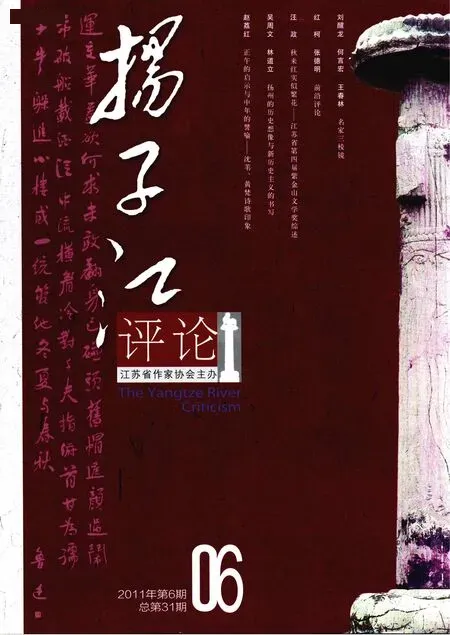高危敏感的文体 饱受非议的作家——编余琐忆之十二
徐兆淮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总喜欢把战场上的士兵和正在值勤的警察视为高危的职业,可是在当下中国却也有人把写杂文和批判性报告文学的作家,还有编发这类作品的报刊编辑,也看做是高危的职业。难怪有人感叹,在中国干报刊文学编辑难,做文学期刊的主编更难。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我在组发刘宾雁一篇有争议的报告文学《古堡今昔》时,即可谓编辑之难的一例。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钟山》在一般作家和读者的印象中,似乎是个以凸现先锋文学和现代派作家为办刊特色的文学刊物。那时节,《钟山》曾以显著版面推荐出余华、苏童、格非和残雪等人的作品,还有莫言、韩少功、史铁生等人某些带有先锋意味的作品。但作为编辑部里少有的中年编辑,我却认为,作为作协机关的文学刊物却不宜把《钟山》办成单纯的先锋派刊物。我赞成韩少功的“好作品主义”。我主张在办刊中也应贯穿足够的关注现实的文学精神。因而,在组成《钟山》的作家队伍中,我们依然可以常见到王蒙、刘绍棠、从维熙等“右派”作家的名字,亦可常见到邵燕祥、牧惠等杂文家的作品,还可读到戴晴、理由等报告文学作家接触现实话题的作品。刘宾雁不过是这批报告文学作家中的一位个性突出、创作成就显著的作家。《钟山》与刘宾雁的接触与组稿过程,又自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之处。
早在我结识刘宾雁之前,我读中学和大学之时,大约1957年前后,刘宾雁即以报告文学和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和《在桥梁工地上》闻名文坛,这些干预生活,较早接触反官僚主义主题的作品,虽然几乎使作者旋即遭到灭顶之灾,但在文学界的影响,却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即使我当时仅是中学生和在读的中文系学生,我亦不可能很快淡忘文坛曾经发生的这些令人不快的往事。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风吹拂中国大地时,刘宾雁获得平反,随即发表《人妖之间》,提到现实社会里贪官所织成的巨大的关系网时,我几乎也被作者深邃的目光震慑住了。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里,《钟山》和我把刘宾雁列为《钟山》的组稿对象,并于1979年底第四届文代会后,邀请他来江苏参加首次太湖笔会。记得那次由《钟山》和《译林》首次召开的太湖笔会曾邀请了来自全国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共60多人,一时间可说是创了笔会声势大、阵容齐之先例。那时江苏文艺界的此举亦可谓吸引了全国文艺界关注的目光,为《钟山》和《译林》的生存与发展抢得了先机。在我的印象里,这几乎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省出版社领导所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
未曾料想的是,笔会之后,《钟山》组发参与笔会的部分作家撰写的几篇短文时,竟遭到出版社某些领导的劝阻,其中就包括刘宾雁的千把字短文《不那么直接不那么狭窄》和郑义的一篇关于谈论政治开放与解放文艺生产力关系的短文。原因大约是,该短文较早地提出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说的异议,还有刘宾雁来宁参加笔会时曾受邀到南大、南师大等高校演讲,他的某些煽动性演讲,颇受高校学生们的欢迎,甚至引起不小的轰动,但却也引起高层政界的警惕,从而关嘱省出版界控制刘的言论影响。那时我初入期刊出版界不知底细深浅,曾竭力说服《钟山》头头发表刘的短文,终于勉强获得通过,而郑义的那篇短文却被“枪毙”了。以至,我一直为《钟山》与这位初期发表《枫》而崭露头角,而后又以《远村》等获奖中篇闻名文坛的青年作家,终于错失了继续友好合作的机会,而唏嘘遗憾。
我与刘宾雁初次见面,似乎在80年代初期的金陵饭店。那时,南京军区的老干部艾奇正在与刘合作撰写一篇关于金陵饭店的报告文学。一天,艾奇先生领我到金陵饭店总统套间见刘,记得那时的刘宾雁,表面看上去身体与精神倒也健壮,行动敏捷,言语反应也颇顺畅,可当他在我们面前一下子吞服了一大把药片之后,我才知道,他已年近60岁,正患有较重的心脑血管病。当时我即想到,或许这正是这位屡遭磨难的报告文学作家为了那几篇接触时弊的报告文学所需付出的沉重代价吧。
如果说,1980年在《钟山》发表的那篇难产的短文,只是刘宾雁在江苏文坛的初次亮相,那么,1985年第4期在《钟山》上发表的报告文学《古堡今昔》,则又好像是一篇引起争议的重磅炸弹。这篇报告文学不仅在陕西西安引起不小的争议,而且,又把争论扩展到首都电力系统的一家报纸,旋即被涉及到的西安电力设计院的一位领导,把反驳和声明径直寄到了本刊编辑部。一时间,争论的火花四溅,争论的热点蜂起,顿时使人有眼花缭乱,莫辨是非之感。这当是摆在刘宾雁面前,也是摆在编辑部,尤其是审发稿件的我面前的难题。
直到这时,我才领悟到,在当下中国,报告文学实在可称为是一种敏感危险的文体。真实性和批判锋芒,常常使这种文体和作家处于风口浪尖的激烈争论之中,甚至给作者与编者带来终身的厄运。诚然,真实本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与重要特性,可是,倘若从题旨到细节要求百分百的真实,那不仅是不可能不现实的,更无异于从根本上扼杀了报告文学。往往被批评主体,也正是以此作为否定作家与作品的借口与依据。刘宾雁的一些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之所以常常受到诘难与批评,往往也正因为如此。
如果说,报告文学是一种高危敏感的文体,那么,刘宾雁便是一位饱受非议的作家。他的存在,他作品所引起的争论,或许莫不与此有关。
他的报告文学思想敏锐,言辞犀利,所选题材又往往是极富政论性和挑战性的,他的那些有影响的作品,似乎是一个极易点燃的火药桶,一经发表,总会引起强烈的冲击波。五七年那两篇给他带来厄运的报告文学是这样,七九年的《人妖之间》是这样,如今发表在《钟山》上的《古堡今昔》大体亦复如此。文章一经发表,即刻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弄得编辑部也不免有些紧张不安。不过,经历过“文革”运动的斗争场面,和1979年前后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熏陶,编辑部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从容面对,冷静处置,从而及时化解了这场危机。
应当说,刘宾雁发在《钟山》上这篇批判性的报告文学《古堡今昔》,连同他的创作谈,还有著名评论家何西来的作家论《公民责任感的火光》,乃是继《人妖之间》之后的另一篇颇有分量的新作。作品一经发表,旋即引起强烈反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场“官司”与争执,如果发生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刘宾雁和编者或许都逃不过挨批受整的命运。所幸的是,这篇批判性报告文学的题旨,在总体上还是与1985年前后的时代思潮相合拍相呼应的。作品并无重大政治问题。
《古堡今昔》引起的风波委实并不算小。这自然怪不得编辑人员的紧张与后怕。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大约都知道,“文化工作危险论”并非空穴来风的吓人之语。许多文化人都遭到过因言因文获罪甚至被迫害致死的厄运。对刘宾雁其人其文的批斗,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他也写过不少歌功颂德的报告文学,赞美过张海迪、朱伯儒那样的英雄模范,但他的那些批判性的报告文学依旧常受到官方的各种责难,特别是被批判者的追究。而在报告文学这一高危文体的背后,受到诘问和责难的,往往不只是报告文学作家,也常会牵连到编发作品的期刊和责任编辑。
刘宾雁在《钟山》发表了报告文学《古堡今昔》之后,情形亦是如此。《古堡今昔》一经发出,麻烦与危险性便接踵而至。先是京中某电力报刊载程青一整版的反驳文章,指责《古堡今昔》严重失实,后来则是被批评者某电力设计院书记魏某亲自出马,写信撰文给本刊编辑部,“声明”刘文对他语多诽谤之言,要求刘与本刊编辑部对他赔礼道歉,发表他的个人声明,以便澄清事实,恢复他的名誉。
此事若是发生在“文革”前后,或是1965年之前,真不知会给刘宾雁带来多少讨伐与批判之声,甚至会再次招致下放劳改,付出沉重的代价。而编辑部组稿与签发稿件的我,也不知会受到多么严厉的追究与批评。可是,幸运的是,此事毕竟发生在党的三中全会和第四届文代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初步吹散了极左思潮所布下的阴霾,加之,此时的《钟山》主办单位已由省出版局改为省作家协会,省作协的领导已将审稿权交主编阅处,因而主编也便有了更多更大的发稿权与处置权。来自批评者西安方面似乎也明白80年中期的政治空气,已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或“文革”前后,他们也未提出更多的处置要求,因而,编辑部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允许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有话语权的原则,特地在1986年第3期上,同时刊出了刘宾雁和当事者设计院魏某的文章,总算摆平了这桩文字官司。编辑部也终于安全度过了这场多少有点让人心悸的危机。作为编辑部的审稿者和当事者,我也不免暗自庆幸,我终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否则,我真不知要遭到多少不测的厄运呢。事实上,这种猜测并非毫无缘由。1988年反自由化时,确实有人追究过刘宾雁来宁是谁接待的这类问题。
1985年前后,正是我从编辑升任副主编,负责审读稿件之初,上任伊始,即遇到这样的麻烦事,真够棘手的。幸亏当时的主编刘坪同志是一位思想解放、富有应急处事能力的老干部,省作协的领导艾煊、海笑等同志也是领导作风十分开明的老作家,因而,刘宾雁《古堡今昔》所引起的风波也就平稳安然地平息了。如今,艾煊和刘坪先生都已作古,每逢忆起这场风波,我内心依然不时地感念他们。
不过,处理这场风波时,我也并不是不问是非曲折的和事佬。编辑的责任和良知使我并不怀疑《古堡今昔》虽然在有些局部细节上可能有失真之处,但对极左思潮的抨击,对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都曾起过良好的积极作用。时过20多年之后,如今再来翻阅刊载刘、魏两人正反两面文章的那期《钟山》,顿时仍会感到,魏的两三千字的声明是多么苍白无力,而刘的洋洋洒洒两万字的反驳电力报程青的论辩文字《人血不是胭脂》,写得那么情词恳切,文采斐然,而又充满逻辑性和思想力量。
如前所说,中国文化人常喜欢将报告文学和杂文称为高危的文体,于是,报告文学作家、杂文家和一些报刊编辑便往往成为敢于闯进雷区冒险触雷之人。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30年,确曾多次冒险触雷,致使我常发出在中国办刊做编辑难,做文学期刊主编更难的慨叹。
好在因写接触时弊的报告文学而屡遭磨难的刘宾雁并不在乎这些。他曾在《我的自由》(创作谈)中坦然说过:常有人劝我说要改变自我秉性,放弃报告文学的写作,改写虚构体的小说。我相信报告文学能够发挥小说无法发挥的作用。我害虫乎?益鸟乎?尚难断言,还有待于历史的鉴定。而80年代的那位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则愿意直率地称刘为“普通的公民,敏感的记者,勇敢的思想者,报告文学大师,虽然他不是完人,他也有失误,有弱点,有缺陷”。
作为编辑,我与刘宾雁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之初我去京组稿时,顺道到他金台路家中拜访,那时他正在做出国的准备,未及细谈余事,倒是正巧见到了一位一九五七年即名噪京都高校的右派大学生林希翎。可是80年代末,出现在我面前的她已是一位神态稍显臃肿的中年妇女,再也不会让人想起那个滔滔雄辩的女大学生了。不久,听说她因未获平反,终于也出走家国了。
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树立这样的评价历史人物的观念:在评价文学家时,不因政治观点的问题,而全盘否定该作家的文学成就;不因人品和道德的缺失,而任意贬低该作家为文与作品的影响?仿佛当年毛泽东对胡适、陈独秀等文学家的评价,也曾有过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评价的类似观点。如今对于已经作古的刘宾雁及其创作成就,可否也作如是观呢?老实说,我是没有把握的。
年华逝水,转眼间刘宾雁已客死他乡多年,作为一名编辑我固无法对其为人为文作出全面而准确的评价,但对其作品,尤其是自己看过和编发过的作品,说点无关紧要的话,即使是“多余的话”,大约也无大碍吧。但愿魂归故里的宾雁先生能够理解一位编辑的纪念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