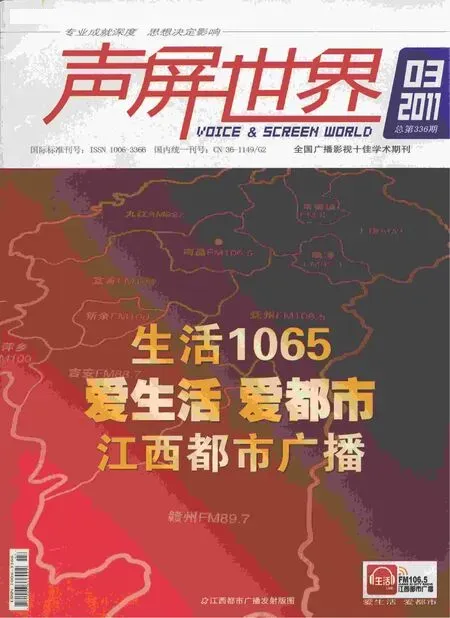从真诚载道到虚浮狂欢(下)——“赵本山春晚小品”之创作流变与文化表征(1990—2010)
□闫 伟
三、文化审视
作为一个比较知名的大众文艺样本,赵氏小品既是社会文化的荧屏缩影,又有相当的文化功能。总体而言,他一方面最大程度地调和了主流文化、乡土文化、大众文化等几种文化样式的不同需求,另一方面也在文化表征的过程中暴露出某些弊端。
主流文化之维。“主流文化是由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主流文化在电视文化中的首要作用是确定整个电视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其力量往往是无形的,电视人的思维和言行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其操纵”。①它以维护国家和社会中心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为己任,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强调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和善恶标准,注重从上而下对受众的引导和教育,是实现电视媒体政治属性的关键所在。
自1983年开办以来,每年一度的“春晚”备受十几亿中国观众的瞩目,收看“春晚”也成为了观众的一种心理定势。在国有国营型的电视体制下,我国电视呈现出与政府高度一致的特点,长期以来,电视担任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由中国电视业的龙头老大——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春节联欢晚会,一方面以多样的形式、不断的翻新履行着弘扬传统文化、营造节日气氛的职责,另一方面也集中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特色。几乎所有春晚舞台上的节目都被赋予意识形态的属性和功能,深受欢迎的赵氏小品也不例外。
赵氏小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主流话语的大众化表达。作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通常不是通过严肃、庄重、认真的方式,而是潜移默化、不露痕迹地融合于剧情与包袱中。正像张颐武教授所认为的,赵本山经常把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文化话语改变为经过农民式思维方式过滤的大众话语,形成了一种主流与边缘、官方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思维与言说的对话错位造成的滑稽与幽默,从而使他的表演贴近大众文化。小品《红高粱模特队》明确地喊出“进京”的口号:“我们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进首都。首都的楼儿高又高,我们时刻准备着。”赵本山们作为农村边缘文化身份的代表人物,通过这种方式表现了他们渴望被主流文化认可和吸纳的心情;《拜年》中“香港回归,三峡治水,十五大召开,江主席访美”这样对乡长的错位评价,巧妙地将当年国家大事串联起来,也是典型的符合主旋律要求的表演。二是大众叙事的主流化提升。即作品的主题思想明显符合主流价值观或者创作者对作品主旨的显著拔高。《说事儿》《三鞭子》《火炬手》分别把主题上升至个人品格、集体利益、民族精神,虽然个别作品在提炼主题过程中显得牵强和突兀,但毕竟表现出作品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境界,并对广大观众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
乡土文化之维。赵本山本人一直以“民间艺术家”著称,他的草根身份注定了其与乡土文化的不解之缘。一方面,民间文化内化于赵本山小品的骨骼灵魂;另一方面,赵氏小品对某些民间艺术品种起到了展示、推广和建构的作用。
对于农民文化而言,王蒙认为:“赵本山在主流媒体上争到了农民文化的地位和尊严。夸大一点说,他悄悄地进行了一点点农民文化革命,使得我们的主流文艺更加宽敞、自然、开放、亲民。赵本山并不放弃作品中‘土得掉渣’的农民心态与观点……”②赵本山在小品中始终以东北农民的形象出现,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乡土气息的人物群像。首先,他以农村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言行举止折射出改革开放后普通农民的生活状态,其历年小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时代农村社会的缩影,为中国农民谱写着心灵史;其次,他对于种种农民式的自私加狡黠加忽悠的嘲笑,也解构了以往艺术作品中人物拔高的教条公式,稀释了当年“高大全”的创作法则,因此也就为观众呈现出了相对真实的农民形象。
对于关东文化而言,赵本山更是不遗余力地将其渗透到小品中。他的表演充斥着东北乡土文化和乡村话语的特色,俏皮的言说方式是他作品的灵魂,他那口地道的辽北方言因独有的语法、语音、语汇而具有艺术的穿透力和感染力,特别能传达东北草根文化里特有的幽默感。另外,作品中出现的“上炕”“唠嗑”“小鸡炖蘑菇”等行为模式和“辽北”“铁岭”“大连”“莲花乡”等地域标识都营造出一种特有的关东氛围。更值得一提的是赵本山对“二人转文化”的极力推广,在《老拜年》《功夫》中多次用手绢等道具展示了二人转才艺,在《红高粱模特队》《说事儿》的结尾处更是直接向观众奉献了洒脱不羁、酣畅淋漓的二人转表演。如今的赵本山俨然成为东北“二人转”的民间代言人,客观上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传播做出了贡献。
大众文化之维。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现代化之路,它伴随着高科技、市场化、商品化和都市化的进程展开,并向大众化和通俗化转型。同时,以大众性、商品性、消费性和娱乐性为特征、以大众传媒为主要媒介的大众文化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并逐渐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在此语境下,人们渴望得到休闲和娱乐,使自己紧张的精神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舒缓;人们“抛弃”了精英知识界所构想的审美或诗意启蒙,也“放逐”了主流意识形态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教条式的宣传和道德操守说教。从而,大众文化使“人类感性解放”的审美理想以感性愉悦的形式得以实现。赵氏小品正是出现在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语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大众文化色彩愈加浓厚。
首先,它为大众狂欢鸣锣。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考察狂欢节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狂欢化诗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重视人类的笑文化;反对传统诗学理论重“高雅”文学、轻“低俗”文学的美学立场;消除诗学研究的封闭性,寻求各种纷繁复杂的文学因素的融洽,如各种语言、各种手法的相互联系;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以狂欢化思维来颠覆理性化思维结构;发掘人类的创造性思维潜力,把人们的思想从现实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用狂欢化的享乐哲学来重新审视世界。”③从中不难发现赵本山小品与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的高度切合。赵本山大胆地把喜剧语言从虔敬、肃穆、高雅、禁忌中解放出来,将民众的、口头的、广场的语言化入表演中,狂欢式的特殊语言容纳了民俗化的广场语言、戏谑的时尚语言、象征、隐喻、模拟、调侃、讽刺、幽默等,它展示着一种乡村话语的狂欢。因此,赵氏小品中许多台词成为风靡一时的社会流行语,如“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下来了,因为啥呀,腐败啊”“谁说我的脸长得像鞋拔子,这是典型的猪腰子脸”“你脱了马甲我照样认识你”“Hello啊,饭已OK了,下来咪西吧!”等等。
其次,它与大众传媒结缘。在现代社会中,媒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运转的传播枢纽,因而,媒介文化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众文艺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近年,赵氏小品不但利用电视这一大众媒体走入千家万户,而且其中对于传媒的展示和推崇尤为引人注目,《昨天、今天、明天》《说事儿》《策划》《火炬手》《不差钱》《捐助》等作品无不以大众媒体为由头,或依托其平台创作而成。或者以“出镜”为自豪;或者认电视主持人做“姥爷”;或者依靠媒体“一夜成名”;或者积极配合“传媒炒作”,这一切在客观上更加认可和放大了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情节相比,某些台词更是赤裸裸地展现出对媒体的顶礼膜拜之情:“感谢铁岭TV,感谢辽宁TV,将来还有可能感谢CCTV”“你 (毕福剑)要真能把我领上道儿(《星光大道》)了,我就感谢你八辈祖宗”“我太想这玩意儿了 (手指着摄像机)”“狗仔队一发现,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你要炒作啊,上中央台把白岩松、崔永元这些名人找来,要不然你白吹”。言辞之间透露出一种现代社会的媒介崇拜心理,把传媒看作一种求名得名、求利得利的万能工具,这种当下的浮躁短视心态当引起我们深思。
综上所述,赵本山的春晚小品在当代社会已经形成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它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中和大众文化的熏染下应运而生,同时也对当下乃至将来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潮产生深远影响。从艺术创作到文化品味,赵氏小品都应该引发我们的关注与思索,如何正确认识它的作用和意义,如何使它健康可持续发展?希望本文能给相关编创者、管理者和欣赏者带来点滴启示。
栏目责编:曾 鸣
注释:
①欧阳宏生:《电视文化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②王 蒙:《赵本山的 “文化革命”》,《读书》,2009(4)。
③蒋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第 7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