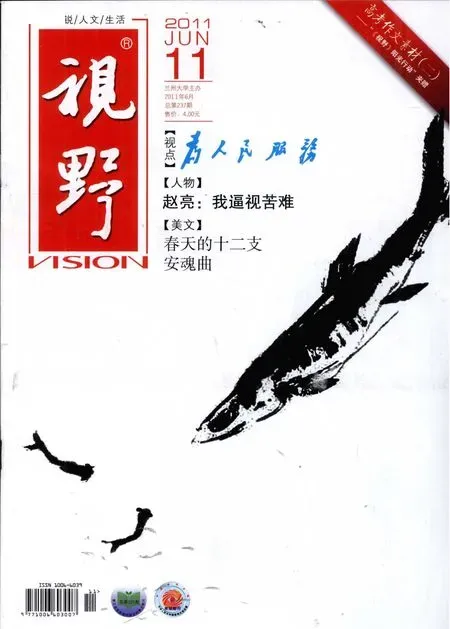疯情万种的岁月
*万 一
疯情万种的岁月
*万 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我还在南方的一个小镇子,经常有一些奇怪的歌舞团来走穴,海报上写着:南国疯狂摇滚歌手。我第一次听到的摇滚歌曲大约是《站台》,有一个半长头发的男人没道理地声嘶力竭,在台上撒泼打滚。滚得越凶,观众鼓掌声就越猛。
我初一时就有一把吉他,会第一把位三个和弦的弹唱,在学校属于二线偏一线的歌手,每次开联欢会我都会去唱歌。大家都说我的范儿很正,会甩头、和观众交流、摆POSE、在台上溜达来溜达去。后来我决定以摇滚歌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一次联欢会前,我特意为自己设计了几个高难度标志性动作,比如劈叉、下跪等。在开场的时候我背对观众坐在台阶上,灯光照出我的一个剪影,特抒情的那种。前奏完毕我一起身,正要唱歌,台下一片哄堂大笑,原来舞台不干净,我坐了一屁股白。这残酷的笑声彻底摧毁了一个摇滚歌手的梦想,至今我都这么认为,卫生条件对一个摇滚歌手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
我正儿八经听摇滚乐是在大学里,那时候我们都是一水儿的重金属,国内的是崔健、唐朝、黑豹,国外的是Bon Jovi、Def Lepard、Guns & Roses。我特别希望和自己的偶像一样长发披肩、皮衣皮裤、特立独行,只是我上的是工科大学,姑娘们比较死板,如果因此搞不上对象岂不是得不偿失。三年级我终于买了一件黑色皮衣,没穿一个礼拜就开始掉皮,迎风一甩,黑色的皮屑飞扬,只能夜黑透了才敢穿着出门,真他妈的叫锦衣夜行。
由于追求摇滚的表层未遂,我决定深入它疯狂的灵魂。我买杂志,看乐评,刻苦研究摇滚乐的起源、发展和变异,我终于知道摇滚乐是一种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音乐,比如,“披头士”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性手枪”用性和暴力对抗传统的社会道德;“朋克”见证了冷战时代的历史进程;Rap就像一把小刀剃着资本主义的腐肉……你可能要说,他们都是抽白面死的,我会立刻反击你:抽白面只是一种表象,他们其实是表达了对整个社会的失望和控诉,他们用死来唤醒我们的无知和懦弱。
我组织了一支乐队,叫“绝缘”。我对我的成员说,我们要做有史以来最深刻的一支乐队,每个人都应该在我们的音乐中涮涮自己肮脏的灵魂。只是工科学生一般比较鲁钝,他们都睁着无知的大眼睛看着我。排练了五六次,我的乐队就解散了。他们背着我偷偷摸摸又组织了一个乐队,后来在学校大受欢迎,女Fans无数,真叫我吐血。对此我只想说一句:同志们哪,千万不要相信乐评人!
生活教育了我,现在我对摇滚的态度就是:兄弟,要不要出去爽一爽?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摇滚乐有更高的要求,除了毒品、性、暴力的三大要素,还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范音乐、服饰、发型、动作的摇滚文化,比如每次演唱会完了吉他手都要砸吉他、烧吉他,这已经成了一个仪式。但这在我们国家显然行不通,我们的生活水平低,天天住地下室,方便面还不管够,看人家砸已经够心痛了,因此我们需要发展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低成本、非暴力疯狂方式。
疯狂是一种年轻人的消费,而摇滚就是它的载体,现在我已经越来越难找到那种激动、投入的状态了。如果一个主唱从台上像跳水一样扎下来,我肯定幸灾乐祸地看他摔在地上,骂一声:傻×。
记得一次春节晚会,郭冬临弹吉他唱歌的时候,突然背带松了掉下来,因为当着几亿观众不能停,他只好拿胳肢窝艰难地夹着,还要作轻松幽默状。我们疯情万种的岁月也是如此,停也停不下来,耍酷还总露馅儿。
(林亮摘自北方文艺出版社《记忆碎片:七零一代的鸡零狗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