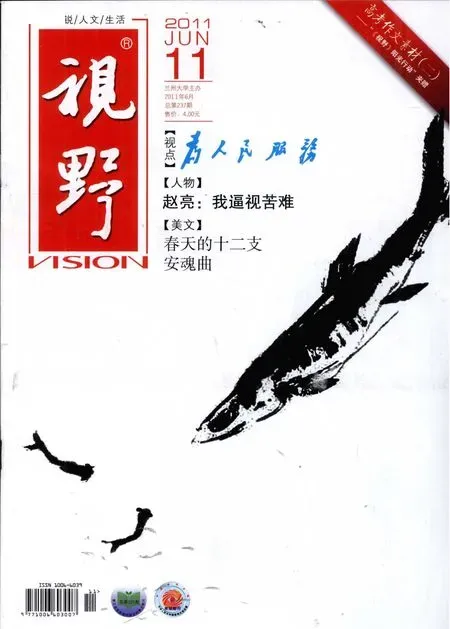我的老师严侨
*李 敖
我的老师严侨
*李 敖

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就是严侨。
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8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和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
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1951年到了,我16岁。暑假后进了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
这时我的知识成长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词,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施启扬(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司法院长”)喜欢同我辩,但他实在很笨,又作少年老成状,令我总要用口舌修理他。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就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
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吴铸人等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
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的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画,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专家,我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
那个时候,我们的数学作业有专门印好的“数学练习簿”,我在练习簿中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倒有一套。我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用Oscar W.Antho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簿”发回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严侨真是迷人的老师,我愈来愈欣赏他。
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我成长的历程、我对现实的不满、我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交给了他。严侨看了,对我有所劝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师生了。1952年我升高中二年级后,编到高二戊,数学改由黄钟老师来教。严侨虽然不再教我数学,但他和我的交情却与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对面宿舍,就是育才街五号,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师(他是江西兴国人,国立中正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在景美军法处坐牢,和我见过面),后面就是严侨家。因为一栋房子硬分成二户,所以变得狭长阴暗,不成格局。
严侨约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时去。在黄钟住院后,一天严侨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诉他医生说黄老师恐怕已没希望了,严侨颇多感触。那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我同行。在路上,他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我:“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他说蓝色,当然是指“国特”)我顿时若有所悟。
隔天黄钟死了,严侨再去医院,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约我进去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劣酒下肚,终于告诉我,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产党!
黄钟的死,给严侨带来了极大的感触,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好人难长寿。
黄钟死后,严侨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为没有钱,严侨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我从没看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哪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著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去,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中国国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七十九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半个多世纪,却使我记忆犹新,永远难忘。
(乔文靖摘自三联书店《李戡戡乱记》韦尔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