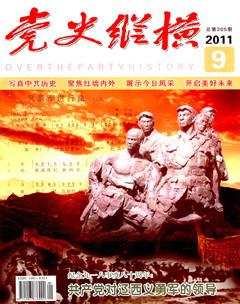中共成立的几个焦点问题揭秘
刘永路

回首90年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从一叶扁舟开始的。当年嘉兴南湖游船上的十几个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然而,当我们由衷赞叹党的伟大光荣的历史航程时,也对其中的一些历史悬疑产生浓厚兴趣:为什么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在中共一大之前?为什么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如何看待中共一大代表的迥异人生?为什么中共一大没有留下中文版的文字材料?中共成立时与共产国际到底是什么关系?笔者参照当前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披露资料,试就中共成立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揭秘,以飨读者——
揭秘之一:为什么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在中共一大之前?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1921年7月,但是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却是在1920年。此事并非空口无凭,而是毛泽东本人亲自确认的。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隆重召开时,毛泽东主席在代表证上入党时间一栏中,庄重地写上了“1920年”。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毛泽东就已经入党了呢?
对此,改革开放以来,有学者不断发表学术文章提出质疑,其主要根据是:1962年“七一”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说,毛泽东接到他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他俩找到李达后,李达问:“你们是C.P.还是S.Y.?”(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的会吧,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有一个过程的。大致可以分为建立早期地方组织和建立全国组织两个阶段。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李达、杨明斋等人在上海成立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当时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这是征求李大钊的意见之后定的,陈独秀为书记,后由李汉俊、李达先后代理书记。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张申府、周恩来在法国巴黎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致函毛泽东,建议湖南也成立这种性质的组织。毛泽东就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成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6人,后发展到10人,骨干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说: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活动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毛泽东对这一段建党活动也有明确的回忆,1945年4月21日,七大召开前,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回忆道:“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指中共七大)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这就是说,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八个早期地方组织,后来习惯上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共产党性质的组织,一共有五十多名早期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是1920年入党的,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他的入党时间确定无疑是1920年。
揭秘之二:为什么陈独秀、李大钊没参加“一大”?
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党成立的头等大事,可是为何党的两位最重要的创始人“南陈北李”都没有出席?表面上看,原因非常简单,是因为忙于事务,脱身不得。但深层次的真实原因,则是当时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中共一大的历史重要性。
当时陈独秀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巨款修建校舍,如果他离开广州,这笔款子就会落空,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李大钊当年担任北京八校的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由于向北洋政府请愿讨薪,李大钊还遭到军警殴打,头部受过伤,在这场斗争的结骨眼上,李大钊不能离开北京。如此看来,两位党的创始人都是为了要“钱”而放弃了出席“一大”,未免有舍本求末、因小失大之嫌。其实,这正是历史的真实所在。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一大”的历史地位是后来才重视起来的,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谁也没有这种预见性。据史资记载,北京小组的成员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开会通知后,认为这是一件不大的事情,所以,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相互谦让一番后,最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据刘仁静本人回忆,本来在选他当代表之前,大家曾推荐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事实上,就是当年亲自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没有意识到会议的重要性,以至于十几年后,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开会的具体日子。他们每个人回忆的日子各异,最后,只得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党的生日定为7月1日,与实际的日子竟然相差了22天。这恰恰说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后,由历史和人民认定的。
揭秘之三:为什么中共一大没有留下了中文版的文字材料?
文字是研究历史最可靠的依据。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只有俄英两个版本,唯独没有中文版本。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俄英两个版本的“一大”党纲又是怎样发现的呢?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访问莫斯科,要求苏共中央把原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杨尚昆从莫斯科带回了几箱档案。这批档案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整理这些档案时,找到了“一大”通过的三个文件,都是俄文译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次年,中央档案馆将其译成中文,并于1959年呈送董必武鉴别真伪。董老仔细阅读后,认为这些文件是可靠的,但有个前提──“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这是“比较可靠的材料”。
中美两国建交之后的1979年,在太平洋彼岸,又有了新的发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廷,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1960年在大学图书馆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用英文打印,题目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署名“ChenKung—po”。经韦慕庭教授考证,ChenKung—po即陈公博。陈公博的这篇论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经过,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写作时间1924年,距中共“一大”召开仅隔3年。这篇论文后面还收入6篇重要文献,其中两篇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这两篇重要文献与前面提到的俄文本内容完全一样。
陈公博论文中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陈独秀)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从陈公博论文中发现的英文版中共“一大”党纲,随着学术交流传到中国,中央编译局将其译成中文,人们才了解到中共“一大”党纲的全貌。这就是英文版“一大”党纲的由来。岁月沧桑,环境险恶,中共“一大”这两个文件的中文本原件,今天已不知遗落何方,因此,俄、英两个译本也就成了“一大”留给后人的、弥足珍贵的文献。
由此,又牵涉出一桩最新秘闻。2011年3月,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之际,重庆党史研究机构又有一个重大发现,并于2011年3月1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中共“一大”鲜为人知的档案:中国最早共产主义组织重庆诞生》。这项重要的发现,填补了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的空白。原来,从1958年共产国际移交的存放于中央档案馆的几箱机密文件中,又发现三件地方组织报告的俄译稿:《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和《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重庆小组报告的发现具有填补重大历史空白的意义。以往中共党史上只有八个共产主义小组,国内六个(上海、北京、湖南、山东、武汉、广州),国外二个(法国、日本),并不包括重庆共产主义小组。而且报告的日期是1920年3月,说明它比1920年8月成立上海发起组的时间还早,这不仅有重大的历史发现价值,而且也留下“中共创建史上的最后一个谜”:即《报告》的作者究竟是谁?《报告》究竟是在哪里写的?《报告》究竟写于何时?《报告》究竟是报送给谁的?尤其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等等。迫切期待学术界对这份报告,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作出确定的回答。
揭秘之四:中共的成立与共产国际到底是什么关系?
1920年1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北京南下之时,就相约了建党问题,因此,中共党史上一直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作为外因的共产国际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是维金斯基。陈独秀非常欢迎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对中国革命加以指导。
应当说维金斯基在中国的活动是顺利的,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关系是融洽的,这与维金斯基的个人品格有关。192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的情况下,维金斯基返回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此次在华共计活动了十个月。
接替维金斯基的第二个共产国际代表是马林,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马林的风格和维金斯基截然不同,他一到中国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索要工作报告,并以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而自傲,陈独秀不见他(一个月)派李汉俊李达与马林会谈,但二李因不满马林的作派,每每发生争执。马林声称自己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要李汉俊向他提交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可以给即将成立的中共提供经费支持。据张国焘回忆:二李回绝了这一要求,“认为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张国焘认为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打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开了一份每月一千元的经费预算。张国焘并没有狮子大张口,但陈独秀立即批评了张国焘,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本着这种立场,陈独秀与马林谈成了僵局。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陈独秀不同意。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持,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对此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不料陈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力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要不要向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共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但经费问题毕竟是极其现实问题,英雄也有气短的时候,很快,连火气很大的陈独秀也无法“无报酬地为党服务了”。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出现转机是因为他的被捕。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马林四处奔走并交付一大笔保释金,陈独秀才被释放。陈本来估计要坐七八年的牢,结果马林把钱花到位,立即无罪释放。这件事让他感悟很深,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从监狱和枪口下救人,也离不开钱,钱不仅能通神,还能买命。这些现实问题不是凭书生空口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陈本人极重感情,出狱后,陈独秀态度180度大转弯,开始会晤马林。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陈独秀后来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在经济上接受其提供经费,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他的一个支部。(二大正式通过《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
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一般不是纸币,而是珠宝和钻石,藏在皮靴子里,加一块皮子就能多藏好几块,顶几个月的经费。
马林亲自参加中共一大,并一口气做了四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说他“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但马林却对刚诞生的中共评价不高,认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
1921年马林经张继介绍认识孙中山以后,其兴趣便主要放在国民党身上。马林感觉当时的共产党太幼小,而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公认领导人,便力劝中国共产党废除关门政策,直接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马林为此东奔西走,既要说服孙中山,同时还要说服共产党人。这一建议遭到中国共产党内绝大多数人的反对,陈独秀反对尤甚。马林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专程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做了一个长篇报告,阐述了孙中山的地位影响,国共统一战线的重要,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并作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面对这一决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只有接受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回过头来看,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是因它种下了北伐成功的种子,但正确前面要加“基本”二字,因为它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没有处理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和能力,由此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一言堂、家长制,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曾经叱咤风云,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固然有他的错误,但面对共产国际作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好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大革命失败后他还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这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了。可以说党内合作这种方式就种下了祸根,与共产国际的策略,马林的指导有着很大的关系。可是当时《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陈独秀“这个死不悔改的机会主义者,实际上是汪精卫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陈独秀下台后的个人反省期间,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其实,实践他这句话的人是毛泽东。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