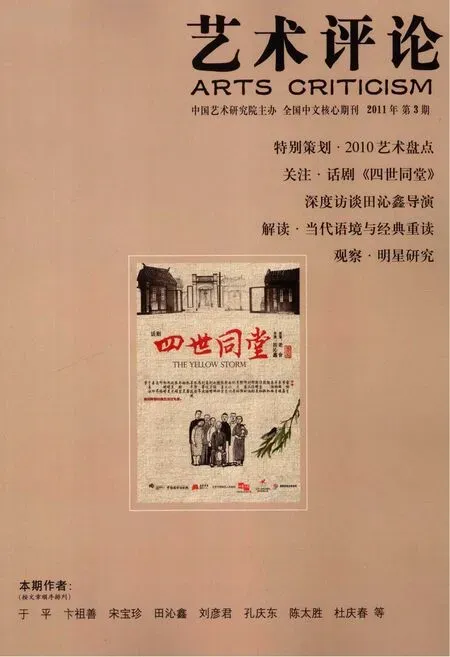对中国当代“精神还乡”主题油画创作的透视
韩 靖
对中国当代“精神还乡”主题油画创作的透视
韩 靖
回归身心安处的家园是人类的永恒渴望。很多艺术家也都在通过艺术抒发他们“还乡”之思。艺术终其本质也在于其引领人归家的功能。然而消费时代的艺术,似乎正在引领人们越发地远离精神家园。本文通过对于当代“精神还乡”主题油画创作的透视,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还乡”之思进行一番回顾与反思。
一、何处是家园:寻找精神和艺术的故乡
海德格尔曾提出“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的思考。在这个家园中,天、地、人、神四个要素彼此依附,共同存在,但没有哪一位是统治者。因此:“‘在大地上’已经意味着‘在天空下’。这两者也意味着‘留存在神面前’,还包括‘居于人的共在’这一层意思。”[1]在“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的设想中,海德格尔注重的是天、地、人、神四个要素的“共在”。而就“人”的存在来讲,他只有与脚下的大地、天上的神灵同时建立起关联,他才是在家的。“正是在此大地上和此大地之中,历史性的人才获得了栖居于世界之中的基础”[2];但同时人又必须保持与神性尺度的关联,“神性乃人借以度量人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栖居的‘尺度’”。在神性尺度下显示出大地和天空、现实和理想、遮蔽和澄明的距离。没有神性尺度的指引,人便不能够追求和超越,而由于他自身的大地性所带来的生命局限和残缺也不能够在本质上被安慰、被救赎。
海德格尔认为,回归“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里是人类唯一的“命运”和“自由”。然而,现代性的进程和人本主义的高涨却使人出离了与大地、与神圣的先在关联,如此生命家园也就解散了,人在成为世界的统治者的同时也成了流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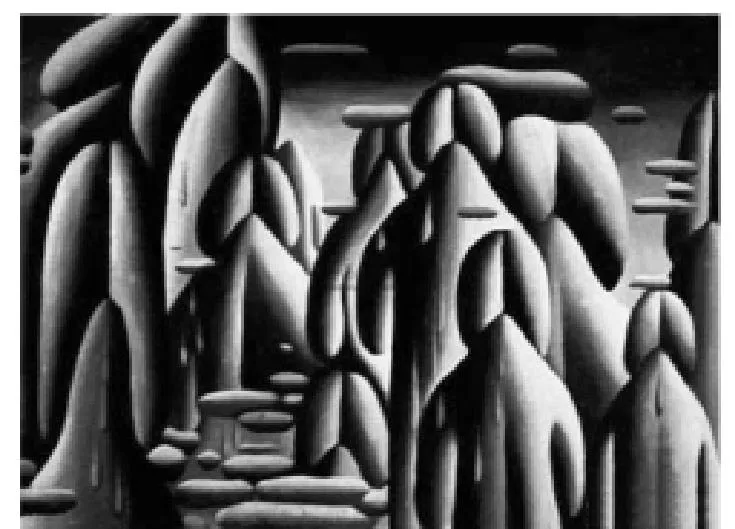
图1 王广义《凝固的北方极地》系列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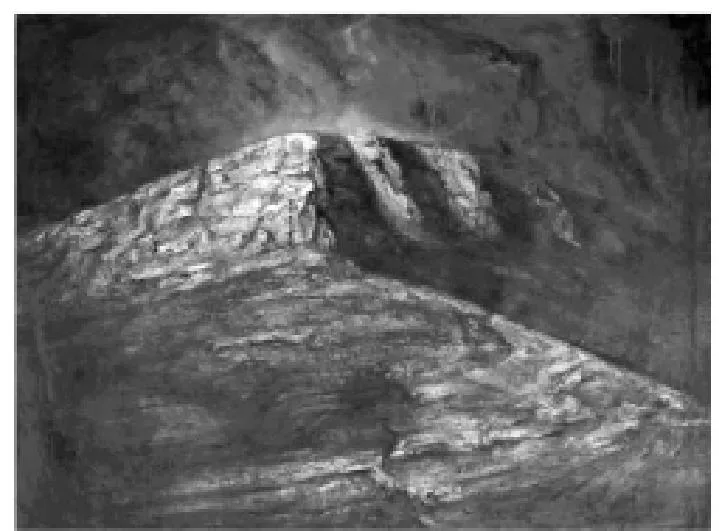
图2 丁方《橄榄山》

图3 郭润文《永远的记忆》
伴随着对于现代性进程的批判,海德格尔展开了他的艺术的“归家”之思。海德格尔为艺术的本质做了全新的规定:“艺术‘创建’(Stiftung,Founding)存在者的‘真’(无蔽状态)。”[3]从海德格尔的艺术论出发,艺术的视角重又回到了人的“真”的存在:那大地之上、星空之下奔赴在归家途中的人,这是对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念影响下的艺术论的颠覆。在艺术作品中,是真理,而不仅是真实的某物在活动,无需艺术家在其中指手画脚。艺术家只是听到了归家的召唤而将家园之美景记录下来的人,从而使欣赏者沿着艺术所开启的归家路重返家园。与此相应,海德格尔推崇的艺术风格既不是“极端的现实主义”,也不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而是同时拥有“伟大的现实性”和“伟大的抽象”一种“单纯的宁静”——一种“伟大风格”,或曰“古典风格”。[4]
二、当代油画创作中“精神还乡”的三种向路
在当下的精神双重缺失的文化背景下当代艺术家展开了他们尤为曲折、也尤为可贵的还乡之思。综观当代“精神还乡”主题的油画创作,艺术家的还乡之思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向路:
1、无法超越的“千秋家国梦”:以北方艺术群体的“理性绘画”为代表
较早通过艺术进行自觉的精神归宿思考的是“八五”新潮期间以王广义、舒群为代表的北方艺术群体和他们的“理性绘画”。北方艺术群体将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崇高的”境界作为精神和艺术的追求:“崇高精神就是人对于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所怀有的特殊信念,这是一种文化整体的复兴动力……这种精神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在于它显示了生命具有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与可能性,而人的意义和使命正是建立在此之上的”。[5]
显然,北方艺术群体的个体生命意识受到了尼采的影响,然而在本质上两者并不相同。如果说尼采哲学的起点是对于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的反思与批判,北方艺术群体从事的则是相当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的工作。他们推崇的个体生命意识的内涵是和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密切相关的人的自觉自信,有时他们用“理性”一词统称之,而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反叛精神。与此相应,虽然他们的思想有着宗教因子,但他们吸收的不是宗教的怜悯和救赎因素,而是宗教所启示的一种为群而牺牲的大我精神。
王广义的《凝固的北方极地》系列和《后古典》系列是北方艺术群体的代表性作品。肃穆、冷凝、古典、崇高是这些作品共有的美学特征。在《凝固的北方极地》(图1)系列作品中,一片散发着寒意的蓝色调子的笼罩下,那一个个背对观者的抽象的、沉默的、似乎蕴藏着无限内在坚韧的、朝着那天际那若有若无的光亮趋近的人形,启示着为信仰而追求的力量和勇气;《后古典》系列则是通过对于耶稣、圣母子等宗教故事以及对于大卫的《马拉之死》的重新阐释,表达了对于个体为大群的崇高牺牲精神的礼赞。
显然,过度张扬个体的使命感与牺牲精神和西方人本主义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显示了与传统家国思想的关联。对于王广义这一代人来讲,西方哲学思潮的涌动唤醒了他们久被压抑的个体生命意识和思想激情,但家国主义的情怀仍是难以超越的。《凝固的北方极地》系列中那一个个背对观者的沉默人形既启示着信仰的超越追求,却又让人联想到北方农民的形象以及忍辱负重等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资源。总之,虽然北方艺术群体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个体的精神世界,但无法超越的“千秋家国梦”使得他们的还乡之思最终不能在根本上触及人类存在的渴望与伤痛。表现在艺术上,虽然北方艺术群体的作品采取了抽象的现代艺术形式,却不能掩盖骨子里的现实主义。
2、在历史的深处迎接神圣之光:丁方绘画的“神性”向度
首先站在存在主义的高度、以“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之“神圣”一维对民族文化传统和国人当下存在状态的进行关注和反思的,是丁方的具有“神性”向度的油画创作。
余虹曾将丁方的还乡之旅概括为两次“出离”和两次“走向”。[6]第一次为“出离”现代城市,“走向”高原和古代城堡。《高原的灵魂》、《山与城的构造》、《城系列:不死者之城》等就是丁方第一次“出离”和“走向”的结果,画面上展示的是自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伟力。然而,丁方不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盲目讴歌者,而是有着反思和批判精神的思想者。在感受到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伟力的同时,丁方也看到了这“深厚”的复杂意味:“但在我的理解中,这种深厚也能成为一道屏障——以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的名义来阻碍我与神圣真言的相遇。”[7]也就是在这里,丁方超越了当时一般的寻根主义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热狂,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出离”和“走向”:出离高原和古代城堡,走向雪峰、光源和教堂,走向和神圣的相遇。
“神圣”在丁方的作品中是以“光”的形象出现的。丁方说:“我在画面上进一步突出了光的作用,它作为我所要表现的神圣突入此在的标志,充盈弥漫于沉重的山脉躯体上,现代绘画中极力要消除的那种‘古典的光影效果’,在我的画中得到了现代涵义的复活,但这光又不同于形而上画派(如契里柯)的那种诡秘悚然的怪异之光,而是一种沉凝有力的执著之光,它从另一个世界突入此世,温厚地漫溢在坚实的躯体上;而天际尽头沿着地平线那一缕将升未升之光,把神圣之光君临此世带来的希望,呈示给了我们。我深知这一希望的价值和意义。有了这一希望,我便不再企求任何了。”[8]在丁方的画面上,神圣之光穿透了历史迫压的沉重(《悲剧的力量》系列),它从深幽的山谷升起(《走向信仰·受难》、《光辉深处的灵魂》),照亮了凄凉的大地(《为晨曦而流泪的大地》、《大地的希望之光》、《夜》、《圣十字的君临》、《橄榄山》[图2]),引领着流浪的灵魂走向回家的路(《孤寂中的祈祷》、《皈依之途》)。
尽管神圣之“光”君临,但在丁方的画面上,光所照临的这片土地,是何等的荒凉、孤寂。正是由于光的辉煌明亮和大地的荒凉孤寂的对照,丁方的作品有了悲剧色彩。余虹是这样解释丁方作品的悲剧性的成因的:“丁方是在一个非信仰的世界中体验神圣的,即他的信仰经验是以神圣不在此地为核心的,在此,悲剧尚未成为过去。”[9]然而,正是其悲剧性使人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了神圣之光君临这片苦难的土地的必要和必然。在艺术表现上,虽然采用的是具象手法,但由于丁方的创作动机的基础是理性的文化批判和展望,观念的表达使作品有着浓重的表现主义意味,和王广义的看似抽象本质“现实”的作品恰好形成对照。
3、重建人与大地亲情的关联:郭润文油画中的“亲情世界”
如果说丁方是从“神圣”一维对人的存在投去了关注的一瞥,九十年代出现的郭润文的创作的则是用一个“情”字温热了被宏大叙事所架空的心灵,重建了生命与“大地”的关联。
对于亲情的怀念与向往是郭润文油画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郭润文说:“综观我的作品,人们并不难发现,我的题材千变万化,内在的主线却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和相互依赖。”[10]而亲情对于一个人的存在来说,则属于“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生命家园中的“大地”部分。
郭润文是从两个向度上来表达他的“还乡”之思的。一方面是对于人之“失家”状态的描绘。这主要表现他的一系列女性题材的油画创作中。在这些作品中,郭润文描绘了失去孩子的母亲(《落叶的春天》),失去童年和人生明媚的少女(《童年的游戏》、《本命年》),处于人生困境的女性(《疲惫》、《梦魇》、《梦归故乡》、《缝纫女工》、《出生地》),浓重的感伤情怀表现出对于“归家”的强烈渴望。而在另一方面,则是对于亲情的怀念和向往的正面表现。这主要表现在他的“缝纫机系列”等静物作品中。如在《永远的记忆》(图3)中,那斑驳的墙面,流泪的红蜡烛,脚踩缝纫机和剪刀,高超的写实手法造成的强烈视觉效果足以唤起曾经生活在那个岁月的人对于童年母爱的怀想和追忆。《痕迹》所描绘的则是一间老屋。式样老旧的桌子和木箱,破纸箱,煤油灯,散发着酸辛而追忆的气息。还有《碗》,一只粗砺的、边缘已经破损的大碗,令人想起童年的饭桌散发着母亲的味道的稀粥。
向大地亲情的回归成为郭润文归家之思的最强音,也是他作品中最具艺术感染力的因素,不过相对来讲郭润文的归家之思忽略了神性的超越尺度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在艺术的表现上,郭润文的作品表现出与其归家之思相应的、向着海德格尔所推崇的“单纯的宁静”的趋近,使古典主义的和谐肃穆又回到了画面上。但是,由于宗教超越精神的弱化,这使得郭润文笔下的“家”之意境虽然温暖,然而境界略显狭隘。
反观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还乡”之思,北方艺术群体、丁方、郭润文等艺术家的精神探索,分别体现了在社会、宗教、亲情伦理三个层面上对于人生归宿的思考。虽然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的影响和制约,他们的探索各有价值,也各有局限,但他们的思考中所体现出来的存在关怀、生命关怀精神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是非常宝贵的贡献,值得后来者去继承和突破。
注释:
[1]海德格尔:《系于孤独之旅:海德格尔诗意归家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
[2]同上,第41页。
[3]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4]刘旭光:《海德格尔与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248页。
[5]王广义:《对三个问题的回答》,《美术》,1988年第3期。
[6]余虹:《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
[7]同上,第307页。
[8]同上,第309页。
[9]同上,第312页。
[10]鲁虹:《对亲情的向往与怀念——鲁虹与郭润文对话》,
http://guorunwen.artron.net/main.php newid=29482&aid=A0000214&pFlag=news_2
责任编辑:唐宏峰
韩靖:广东肇庆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