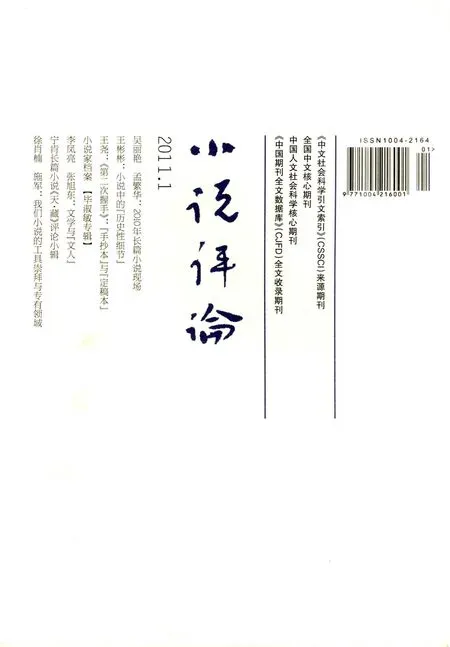宗教精神在世俗情怀中永生
——《清水里的刀子》仪式解读
刘晓鑫
宗教精神在世俗情怀中永生
——《清水里的刀子》仪式解读
刘晓鑫
民俗是人类社会群体共同信仰行为构成的风俗习性和文化意识,是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而又具有特殊本质、性能和地位的一种社会现象。民俗对我们社会的众多领域均有很大影响,文学更不例外。从上古以来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派”到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过程中,民俗文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意义。祈祷和忏悔是西方人(不论高官亦或平民)祈求上帝宽恕的人格体现,我们经常在影视书籍中见到;我们也看过阿拉伯人念诵古兰经的宗教活动场景;还看过藏族民众跪拜朝圣的艰辛和佛教徒的平和与宁静。这些宗教仪式和民俗文化建构了一道世界性的永恒风景,成为世俗生活中的一个精神原素,已经深深潜入我们大众生活中。
民族,作为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俗就是这种民族及地区共有的文化意识和心理素质的体现,而不同民族区别在于文化精神形态上的差异。伊斯兰教,一个远古久远充满灵性而神奇的宗教。茅盾文学奖得主霍达等作家曾经以之为叙述核心创造出一批反映伊斯兰民众世俗生存和精神游走的名作,我曾被他们的叙述所吸引。但当读到2001年鲁迅文学奖得主、回族作家石舒清的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①时,我用言语编织的视野期待防御轰然坍塌,被他的叙事所击碎,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袭遍全身。这是一种独语,别人无法进入的言说,是石舒清所特意的并呈现着一种弹性十足的张力。我想,当一个人或一种生灵大彻大悟时,这是何等的壮美。
与其说石舒清是一个小说作家,毋宁说他是一个诗人,一个为人类阐释富有人性和诗意的死亡崇拜下的宗教精神的使者,我被作家智性语言所描绘的情性意境深深地打动了。西海固,那块荒凉而平凡的土地,孕育着一群对生活的耐力和韧性、对宗教的虔诚和坚定、对死亡的追问和思考的人类,文本的叙述不夸张、不做作,娓娓到来如同泥土般气息扑面而来,素朴的背后隐藏着令人深思的慨叹。作品以全知视角——一个平凡普通的埋掉了自己女人的老人马子善为叙事视点,通过宗教仪式“举念”的过程,去观照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宗教的天人合一的内在关联。
很多学者把本文的主人公钦定为马子善老人和他的儿子耶尔古拜,其实“牛”也是文本中的不可或缺的主人公(精神升华后隐喻性主人公),它已不是自然界里的动物,而是一个经宗教澄净后发展为人格化、人性化了的“通灵人”的精神最高阶段。我认为耶尔古拜、老人、老牛其实就是一个“通灵人——安拉之子”的青年阶段、老年阶段、死亡阶段的生老死亡的组合过程(亡人经过举念后走向新生,又开始了人的新生阶段),所以文中“安拉之子”的生老死亡与宗教精神的终极存通过“举念”这一宗教仪式形成一种循环封闭的互动模式,如图所示:

三个“主人公”(耶尔古拜、老人、老牛)对“死”都具有不同“看法”,但是,通过一次宗教仪式(举念)的生命与精神之旅,他们已经走向新的视阈境界,进行了伊斯兰教精神的美丽皈依,完成了一个“通灵人”从潜意识到意识自我价值实现的生命过程,这个过程也是通过“举念”而形成的生命终结和精神层次递进的过程,并由此构建出一个生生不息、相互循环的封闭系统,从而完成“通灵人”的发展之旅。《古兰经》上曾说:“每一个有生命之物都要尝到死的滋味,”“死”是人的必然归宿,他们从容面对死亡,去抵达圣洁的彼岸,无论是人还是其它生灵。我们触摸着被时间的尘埃所掩盖着的古远的脉搏,回复到一个和民俗、世俗、宗教融合的仪式——举念中。
耶尔古拜在举念的引导下成为了“通灵人”的初级阶段。通过其对举念所作的努力行为,我们都知道他对真主的信仰,不仅是内心诚信还身体力行。宗教情怀在这一个体上显得更为复杂。我们现有的评论大都去挖掘老人和老牛的形象及其文化内涵,而将这位主人公给忽视了。年轻人对死亡的概念是没有老人深刻的,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死亡会对自己产生威胁,因为那是一个遥远的事情,正如马子善老人的内心独白:“儿子若到了自己这个年龄,就不会因亡人而哭了。自己若在儿子那个年龄,大概也还是要哭的。”耶尔古拜的目的是为了回忆和祭奠自己的母亲,因而在老牛被决定用来作搭救亡人的举念仪式之后,耶尔古拜把对母亲的爱和回忆倾注在对老牛的殷勤照料上,耶尔古拜用“难以言述的感动与狂喜”侍候牛,像“干着一件神圣事业”。老牛此刻俨然成了母亲的灵魂化身,成了阴阳两界的“喜鹊搭桥”,“他对母亲的强烈的情感与想念都寄托在这头牛上了。他觉得自己不是在侍候一头牛了,而是虔敬地侍奉着自己敬重的一位老人”。就是在这一情感的位移和替换中,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想法,“他就觉得这头牛已超越了其它一切牛,”“具有了独特的品质与意义”,他甚至“突然想对着这头牛,泪雨婆娑地喊一声娘。”这已经不仅仅为一种赤子情怀的庄严传递,他此刻已经决绝于过去,如果说,在这之前耶尔古拜只是一种情感的感性显现,那么这举念仪式之后他进入了宗教的理性表达,开始进入思考的语域。当老牛不吃不喝的时候,“儿子突然问他说,大,是不是……他知道儿子要说些什么。”耶尔古拜想说什么呢,他此时此刻已经彻底领悟了老牛原来怪异行为的目的,在意识深处产生了无限的震撼和感慨,是同情亦或悔恨,是尊慕还是敬仰,我想这些都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他人死去之际可以经验到一种引人注目的存在现象,这种现象可被规定为一个存在者从此在的(或生命的)存在方式转变为不再此在。此在这种存在者的终结就是现成事物这种存在者的端始。”②年轻的耶尔古拜把对死亡和宗教情怀的领悟释放出来。
老人在举念仪式下突然看到老牛的平静,于是在坟院中开始思考生命的死亡,此时的老人已经开始走向“通灵人”的高级阶段。他知道,自己的生存只不过是在流浪中的行走,只有死亡才是旅途中的回归,才可以通过安拉的指引走向灵魂的憩息地,回到自己的家园,“马子善老人轻轻叹一口气,应该在这里多走走的,应该在这里多看看才是,这里才是家。”他仿佛听到了地下妻子的亡音:“再转悠几天就回来,这里才是你的家。”所以,在他高级阶段过渡。
老牛是这一家庭的一份子,和马子善老人已经情同手足,为了完成搭救亡人的仪式而被举念。在举念的前三天,具有通灵能力的老牛已经知晓了它的生命意义,因而它在清水中看见了刀子,它不吃不喝任清水与嫩草放在面前,“牛宁静端庄地站在那里,像一个穿越了时空明察了一切的老人。”宗教精神在世俗生活中穿透时空的隧道,走上阳光之旅。老牛已经成为了“通灵人”的精神最高级阶段,在接下来的几天,老牛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清洁的“内里”,清洁清洁地归去。“它依然在不缓不疾、津津有味地反刍着,它平静淡泊的目光像是看见了什么,又像是什么也无意看。”老牛已经具有了自我的感知:
一方面老牛重“义”,马子善老人年轻的时候,老牛也还年轻,“和他一般有着暴烈的脾气,不时就将自己那样一个健壮而沉重的身子腾在半空,在半空里有力而又极度紧张地扭曲一下。”年轻调皮火暴的牛和马子善夫妻共同生活,直到马子善老人孩子的长大、妻子的死亡、自己的衰老,他们已经建立了一种“朋友的友情”。记得一位哲人说过,动物是有灵性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老牛欣然愿意以死亡超度自己的另一个“朋友”——马子善老人的妻子。所以耶尔古拜把牛带走的时候,“其实不是耶尔古拜在牵它,而是它跟着耶尔古拜走着罢了”。这里已经形成了动物感恩的神话模式,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因为作者依据人类感恩的方式进一步使伊斯兰精神变得更庄严、更纯洁、更肃穆。
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有生命的生灵都惧怕死亡,当死神降临时都会反抗,然而老牛却沉着面对死亡,因为“它”也信仰伊斯兰教,把“自己”看成了一个穆斯林教徒(也许这是很荒诞,但确是事实,由一个动物变成了“通灵人”)。老牛很了解“举念”这一仪式的宗教意义,当它看到清水里的刀子时,“微闭着眼睛,忘我地享受着对它无微不至的洗浴,似乎这个被洗着的身体不是它的一样。”这说明牛已看来死亡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基点,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死亡是完完全全的此在之不能的可能性。于是死亡绽露为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作为这种可能性,死亡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悬临。”③在伊斯兰教信仰的指引下,他渴盼自己死亡:“他想自己若是知道自己归真的那一刻,那么提前一天,他就会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穿一身洁洁爽爽的衣裳,然后去跟一些有必要告别的人告别,然后自己步入坟院里来,”(这种想法是在老牛的引导下才产生的震撼,所以二者是惊人的相似,老牛的通灵在两相比较下更具有了为信仰献身的宗教情怀)与妻子同枕而眠。信仰净化了他的灵魂,关怀着他的世俗生活;死亡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消亡,更是精神上的皈依,因宗教文化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生命的旅途,用神性的启示走向超越生命的彼岸。一个人只有坦然洞察生死的奥秘,获得生死的大智慧,才能超越死亡。宗教赋予马子善老人对死亡的领悟,“找到自己的长眠之地,含着清泪,诵着《古兰经》,听任自己的生命像和风那样一丝丝吹尽。”“马子善老人正在离树冠较近的房子里精心地粘《古兰经》,经典历时久了,纸质已经泛黄,而且轻若鸿毛,但上面的字迹却似愈加清晰。”“阳光照进来,像金子那样的阳光,落在大大的桌面上,落在摊开的古老的经典上。”《古兰经》是真主的语言,穆斯林教徒把它奉为至宝,通过这些描写我们可以看出马子善老人超脱自我的宗教情怀和无限虔诚。无论一个人的信仰如何,都最终要在死亡之时寻找一种支持,以自己的方式踏上自己的永恒之路,这将是每个人的最后归属。“采菊终篱下,悠然见南山,”老人心无旁骛,对人生信仰加以思虑参想,使思想更加纯正晶莹。作者不仅追问着生命的死亡与延续,还带着一种永恒的精神体验与哲理思考,以虔诚的宗教精神对人生终极意义进行跟踪和追寻,从多角度多侧面挖掘人的思想困惑和忏悔意蕴。所以老牛是“通灵人”精神系统中的中级阶段,并经老牛“点拨”醒悟后开始向经知道自己的身体将要祭献给神灵,献给无上的宗教,对“它”来说这也是一个多年期盼的梦想。此时它由情感程度的“义”上升到宗教深度的“意”,这应该说是老牛一生中最伟大的转折。所以举念的前一天老牛因为不吃不喝而触目惊心地瘦瘪下去时,它依然“静静地立着,双眼微闭,依旧在轻轻地反刍着,”最后在生命走到大限之后,硕大的牛头“一脸的平静与宽容,眼睛像波澜不兴的湖水那样睁着。”在生命情境的人文关怀之后,宗教具有了神性而富有诗意的光辉,照耀着它的每一个子民,老牛在这种关爱中获得了永生。“每一此在向来都必须自己接受自己的死。只要死亡‘存在’,它依其本质就向来是我自己的死亡。死确乎意味着一种独特的存在之可能性:在死亡中,关键完完全全就是向来是自己的此在的存在。”是的,牛作为一个存在,在被举念之后依然“颜面如生”,依然存在于世俗之中,依然永立于天地之间,通过生命神性的升华从容步入宗教情境的殿堂。所以马子善老人觉得“这么多年竟是把牛看轻了,牛有着博大而宽容的心灵,他觉得牛实在是一种了不起的生命。”作者用优美的语言阐释了一个神秘的寓言,一个宗教般的生命境界中蕴涵的古老话题——死亡。“这头牛已超越了其它一切牛,这头被举念了的牛已有了一种独特的品质与意义。它将携带使命去拯救苦海中因自己的罪恶而受难的亡灵。”正如文化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所说,身体作为符号用以表达人神关系的符号或象征。④
由上可知,老人、儿子、牛三个主人公的思维转变都是因了“举念”这一宗教仪式。文化人类学家特纳认为,人性只有在仪式和宗教、艺术中才得以繁荣发展。⑤在举念前,不管是老人、儿子还是老牛他们都任劳任怨、本本分分做自己的事、想自己的事,都是以一种平常而又素朴的心态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和谐平衡的稳固体;而一旦“举念”,这种稳固体坍塌,三个主人公在仪式的具体操作中,都感到了一股庄严,而这庄严就是宗教情怀给以芸芸众生的世俗关爱。所以仪式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视阈生成之时,经过一次形而上的精神洗礼,在形而下的突围中完成了人生中最壮举的转折,他们都披上了神圣的光芒,如同西游记唐僧四徒西天取经结束后都修成正果。儿子、老人、老牛就这样完成了一个“通灵人”的青年阶段(初级)、老年阶段(中级)、死亡阶段(高级)的组合(亡人经过举念后走向新生阶段),所以文本中“人”的生老死亡与宗教的终极存在形成一种互动。而这“通灵人”则象征着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伊斯兰精神和穆斯林文化。宗教仪式及情感深入西海固这块贫瘠干裂而又精神充盈久绿生机的土地上的回族民众的世俗生活中,并内化为一种道德准则,不断净化这“诗意和温情”的心灵和生命,于是,一种宁静的燃烧、苦难的愉悦以超验的情感方式传递出来。
石舒清先生曾说:“首先我很庆幸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作者,我更庆幸我是一个回族作者……回回民族,这个强劲而又内向的民族有着许多不曾表达难以表达的内心的声音。这就使得我的小说有无尽的资源。这些年我尽力表述了一些,使我欣慰和感念的是,愈是我写我的民族的一些日常生活、朴素感情和信仰追求的作品,愈是能得到外部的理解和支持,像《清水里的刀子》《清洁的日子》……”⑥《清水里的刀子》可以说是回族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收获,我不赞成有些学者所说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回族文学’”。⑦作者在文本中展现了典型的回族民俗心理及民俗地域上的宗教仪式:虔诚信奉伊斯兰教,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民族亲近感、民族认同及民族凝聚意识。文学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独特的民族心理决定了创作的心理定势,回族作家的民族自觉心理、民族认同感是促成其作品民族化风格的关键因素,正如英国评论家海伦·加德纳所说:“在各个时代和各种社会中,宗教表现在各种必须举行的仪式和各种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必须遵行的行为准则之中。”⑧追求创作民族化历来是有识作家们的努力方向,而对民俗生活的再贴近,无疑是步入创作民族化道路的主要手段。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由此化之,越是民俗的,越是民族的。身处某一地域的作家,情感和意识必然受该地民俗群体凝聚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为某一地域作家的作品风格、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品的地方色彩,实质上就是特定地区民俗事像的艺术展现。民俗作为人类社会集团群体共同心意行为构成的风习性的文化意识,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同时它对人类的活动又有着很大的束缚和制约性。虔诚的信教心理民俗成就了这篇极富回族伊斯兰文化色彩的篇章。纷繁的民俗事像一旦为作家所关注、所利用,便以其本色的感悟、理解和诠释,直接使文学创作更贴近民族化,使文学作品更具地域色彩与民族色彩,也使作品本身内涵更厚重。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伊斯兰精神渗透到穆斯林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从出生到死亡,从摇篮到坟墓。”⑨石舒清在《清水里的刀子》中从容地表现对生活的审美价值理想更为开阔的视野,在舒缓而冷静的叙述普渡众生之后,回归穆斯林精神,回归伊斯兰教的神圣情怀而落下帷幕,这是一部回族的心灵史,更是一出民族的风情画。我国共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尤以回族穆斯林为最,伊斯兰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当中国以崭新的姿态进入21世纪时,广大的中国穆斯林群众和全国人民一道,正以满腔热情投身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复兴做出贡献。所以,我们要继承伊斯兰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一步宏扬兄弟民族的精神自豪感和主人公认同感。
格尔茨认为:“仪式不仅是一种意义模式,也是一次社会互动形式。”⑩神话的力量、启示的权威和生活的戒律做为真实的存在,影响着人类对宗教的虔诚与信仰,这也正是宗教使得灵魂演绎为人性的基石,由此走向澄明之境——宗教精神在世俗情怀中永生。作者石舒清借助《清水里的刀子》的叙述,在历史与现实、感性与理性、世俗与审美、宗教与民俗的关联纠葛中纵横捭阖,在伊斯兰宗教文化的宽阔视野中言说自己的精神内蕴,并返回内心寻觅人类的栖息之所——精神家园,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最远的地方,我最虔诚!
刘晓鑫 井冈山大学
注释:
①石舒清:《清水里的刀子》,《名作欣赏》,2002年第5期,第1页。
②③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88页,274页。
④⑤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第319页。
⑥石舒清:《自问自答》,《文友》,2002年第4期。
⑦吴宏凯:《诗化的死亡叙事》,《名作欣赏》,2003第1期,第43页。
⑧海伦·加德纳:《宗教与文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⑨高惠珠:《阿拉伯的智慧:信仰与务实的交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0页。
⑩格尔茨:《仪式与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第52页。
book=139,ebook=9
- 小说评论的其它文章
- 小说中的“历史性细节”——以打狗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