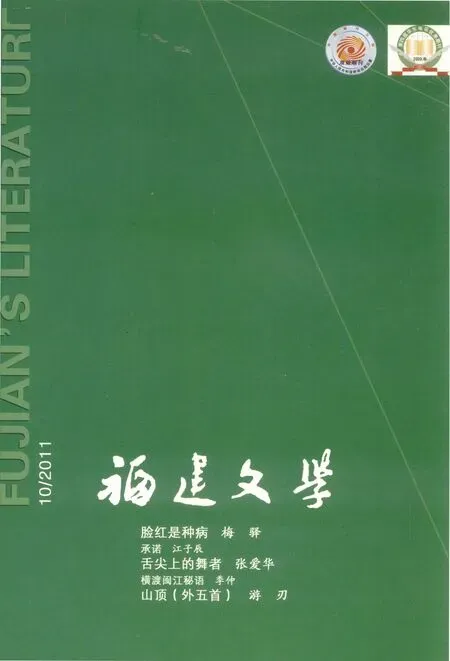我寄人间雪满头
朱朝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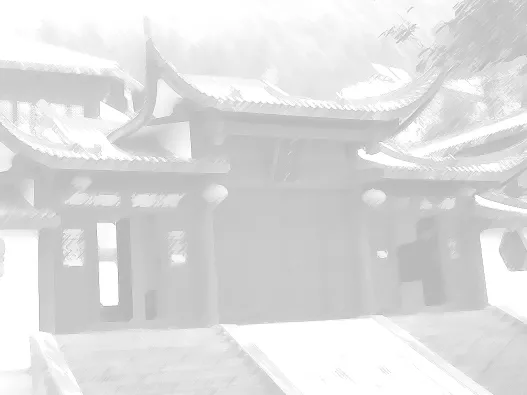
白云寺在密匝高大的林木丛中,林木多是枝叶繁盛、树干挺直的香樟,偶尔穿插几棵耸入云霄的银杏。车跟随青翠欲滴的绿色一路披光泛亮,亮阔的车窗玻璃横亘着青枝绿叶的倒影。走着、走着,黑瓦白墙的寺院在眼前出现。
白云寺不大,不像寺庙,倒似过去年代的祠堂。三进三出的院落,雕楼与砖瓦上的颜色斑驳皲裂,与青石板合力削弱扑面而来的天光,幽暗与沉寂渗透了墨绿的樟叶、缄默的枯井和大堂中的各路菩萨佛祖及蒲团,脚步无形被抽去了重量,轻幽地滑动,树须仰头才见,高而宽的门槛须牵起裙角、弓下腰身进去。我不信佛,但喜欢这样的氛围,幽静沉寂。我来白云寺不为烧香拜佛,而是找一个人。
了尘呢?
推开虚掩的木板门,问一个面容有些枯槁的出家人。他在习字,俯身一张案几,拈毫泼墨,雕花木窗与案几斜对,半开,竹枝横逸,天光倾洒。
劳驾,了尘师父可在?
果然是一张枯槁无颜色的脸,面对我,右手按住宣纸,左手——哦,他用左手写字——提笔仍在继续,我瞥见,一个“雪”字,隶书赋予的高古,在收尾的刹那有些寡合、肃穆。我不禁再次重复“劳驾,了尘师父可在”。
云游玉泉,辩经求学。
看着再次俯身案几的背影,我脑海一一闪过他文绉话语,他倒是与这个几近破落的白云寺挺相符的。这个了尘,云游四海去了。
退身而出。辨别不出色彩的声音再次响起——施主,请帮忙掩上门。
白云深处有人家。这个人家不在俗世中,沉寂得名副其实,我轻轻划动脚步,掩门,心思无限。了尘在就好了,他去玉泉辩经,什么时候回来?我想听听他的意见,关于喜和悲,关于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以后在哪里才见到小师父?
白云深处有人家——当时,了尘就是这样回答我的。一伙人在名为泗水的森林中游玩,我落在后面,爬一处斜坡,手中拈着才刚刚结出果实的野草莓枝。一个斜挎着布袋的小师父从旁边的溪流中跳到台阶上,我侧身让小师父过。小师父竟然羞赧地一笑,一手搭在腰身下的布袋上,一手在鼻梁间竖起:女施主,看你是有福人。
何为福?我笑了笑,不置一言,低头抬脚爬台阶。小师父后退一步,继续说,福者,喜形于色,女施主面善,喜色盈人。
我停下来,面对小师父,耸耸肩膀,问,你找我是算命吗?很抱歉,我的皮包不在手中,你可能一分不得?
小师父摇头,继续说,有缘乃天作,唯有顺应,钱财不过身外媒介,见笑大方,遇有福之人说福,乃双福为大喜。
何为喜?
添丁、路顺、人和是为喜。
我不禁哈哈大笑——小和尚说的福与俗世理解的“升官、发财”之类的福完全相异,耳目清新。小和尚见我如此开怀,也咧嘴微笑——顺喜即为福,然后转身而去。顺喜为福,倒有些禅意。我踮起脚尖,喊:小师父,怎么称呼你?
了尘。
了尘又要朝林中走去。我继续喊:我以后在哪里才见到小师父?
白云深处有人家。
想想,那样破落的寺庙,储集的时光,漫漶着陈旧气息,还没到被改天换地的日子,破落的意味,何尝不是古意的坚守?这,倒衍生出一丝丝真了。
一个多星期后,我寻来,白云寺里,了尘师父不在,却仍然没有让我失望。
在枯井口的青石上坐了一会儿,起身,行至刚才掩门的禅房门前,放下一袋茶叶,是野生的绞股蓝,纤细、墨绿,一根根性格十足地挺直成针杆模样,那是我准备与了尘师父一起讲话时喝的。茶叶在高阔的门槛下,落寞孤单,我想了想,在皮包里乱翻,翻出通讯本,撕下一张空白页,写上:山中之叶,自然恩赐,喜者可饮。压在茶叶袋下。
从医院出来,我捂着平坦的肚子,脚步轻缓拖拉,犹如身怀六甲,走出诊室,下电梯,心中五味杂陈。这么些年的婚姻生活,习惯了二人世界,我开始是坚持不要孩子,后来想要,却怀不上,七年之痒,白光天已经发福,他比我还着急,拉着我到处检查,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可孩子就是不来。今年是第八年,我却怀孕了,先是试纸查尿,然后憋尿做彩超——我不相信啊,或者说,心中有恐慌,祈愿是误会,试纸失误而已,但在我躺下的刹那,懊丧与恐慌袭击下的我灵光一闪,突然想起了与了尘师父的偶遇。他说我喜形于色,是有福之人。
他还解释,顺喜为福,而喜表现为:添丁、路顺、人和。
我脑袋一轰,完了,做什么彩超,都是事实,试纸验证无误的事实,而最先发现我怀孕的不是试纸,也不是我身体异常引发的小怀疑,是那个小和尚,了尘小师父。
他在一星期前就告诉我怀孕的事实,这个小和尚,说得蛮准——添丁,还夸我喜形于色,但与“福说”南辕北辙。他只知其一不解其二啊,我是盼望有个孩子,可是我盼望的是与白光天有个孩子。
我被医生严肃按下肩膀,静静躺在洁白的床铺上,袒露着肚腹,接受凉湿的润滑剂的涂抹,接受类似按摩器物件的仔细挤压。
恭喜你当妈妈了。
我心中已有准备,噢了声,耐心等待医生下一个告知。
一个多月的胚芽咧,好得很。
脑袋再次一轰,一个多月前,我在外地出差,一个星期。而那个星期,我唯一记得的就是会议中的一次游览,陡峭的悬崖,没有缆绳的原始栈道,所有人都离开了,但我和他留了下来,他左我右,冷飕飕的风从背后连绵大山的缝隙处灌来,长出阴森而锋利的爪牙,刚才还挂在头顶的圆硕的太阳突然消失了,浸染了冷凉山风的黑暗,宽阔无边、浓厚沉重,天地改变了模样,雨水冰凉地滴落我们的头顶和肩膀,脚下的栈道湿滑,旁边的悬崖冰凉,他拉住我的手,几乎是拥抱着我离开了悬崖,到了一棵不知年月的古树下,我们发现太阳出来了,挂在头顶,温馨而新鲜地照耀。我们倚身古树后面的大石墩,一起辨认石墩上面的刻字,乾隆年间的篆书,在风雨侵蚀中斑驳模糊,他细心地用无名指指甲轻轻顺着石墩上的纹路刻画,连缀辨认的字体成诗句,仿佛他不能确定,征求我的意见。我们俯身,睁大肉眼,对着大石墩,他与我那么近,彼此呼吸相通,我们一起念出时,他再次拉住我的手。
该怎么说呢?几乎梦幻般,零碎不真实,轻忽忽地来,不彻底地离去,刹那的光景中,譬如雨水,譬如凉湿,譬如幽暗……碎片扇起让人情不自禁驻足流连的梦幻。他,他他他……在我漠然中一遍遍发出信息,耳语般地穿透屏幕,带着陌生不乏亲昵的温热,倔强地培育记忆这棵大树。他要求把梦幻彻底推翻基脚,重新垒砌另一座大厦。
雄心偏遇无为。我删除他的号码,但他强悍地攀附我的屏幕,以11个数字掀起碎片边角。
那一次……时间吻合,可白光天在吻合的时间之外。
从床铺上一跃而起,一个念头闪电般冒出,我要打掉这个面目蒙昧的孩子。医生纤细的手指轻压住我的肩膀:安静,请安静,你不是一个人了。
我要打掉孩子。
片刻沉默。医生启口——你情绪有些激动,这样吧,回去与家人商量好再做决定,三五天也不迟。不,我现在已经决定,马上拿掉。
医生盯着我,她不大的眼睛在冷静中透露潭水般的冰凉,我有些心烦她了,她的举动无疑是反对我的决定。
我也是母亲了,孩子来到世界不是偶然。
她要说什么。我瞪起双眼,脸色绯红,抓起皮包跑出彩超室,朝手术室奔去。刚上楼,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推着一辆车经过,车上有一个大玻璃瓶,一个抱紧自己的婴儿雏形浸泡在血水中,我胸口一阵疼惜。
顺喜即为福。
那么反面呢?我有些发冷,愣了片刻,转身下楼。
夜色迷糊,华灯初上。我一直在街上溜达,捂着肚子,脚步拖拉,仿佛身怀六甲。手机隔会儿就冒出泉水丁冬声,是他的信息,不用看。
到小区门口时,手机铃声响起,《海边的阿狄丽娜》,我专门为白光天设的铃声,也是白光天专为我设置的手机铃声。这样一说,《海边的阿狄丽娜》的特殊意义就出来了,是的,我们曾经是大学校友,他高我两届,我到校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他,他负责接待新生,拖着我的行李箱排队、报名、找寝室。我在寝室坐下,发现《海边的阿狄丽娜》钢琴CD集不翼而飞,万分沮丧,白光天转身下楼,要我在寝室等他,我洗了澡,还到学校超市买了零食,回来时碰见白光天正在满头大汗地爬楼,我拍了拍他肩膀,白光天一转身,兴奋地拉住我的手,递给我一盒理查得钢琴CD集。噢,他刚才买来的。此后,他还送我各种乐曲演奏的《海边的阿狄丽娜》,我们反复地听,最终达成一致意见,风笛吹奏的最迷人,令人浮想联翩,钢琴演奏的最经典,无可挑剔。我们各自的手机设置的都是风笛版的《海边的阿狄丽娜》。
他在干什么呢,白光天?
我按下接听键,白光天还是亲昵如常——穆穆啊,吃饭没有?抱歉,我下午被安排出差了,给你短信你没有回。
原来还有白光天的短信,我当然没有看,下午时分,我正在医院折腾。白光天说要出门两三天,我噢噢地应着,白光天啪的一声关上手机盖。
晚上,我特意煲了一罐汤喝。肚子偶尔动下,我感觉是孩子张开了嘴巴在吞咽,看来,我是喜欢上肚子里的孩子了。
收拾好厨具,抿着茶水时,心中又有愁绪——白光天知道了,肯定会想到孩子的来历,而一算时间——我眼前一黑,心胸烦闷。
第二天,半喜半忧地上班,转到菜市场两次,买了新鲜的小鲫鱼,买了筒子骨。每每收拾完餐具,抿着茶水时,白光天与孩子的关系就缠绕在脑际,盘亘不去。
我决计去找了尘师父。
顶多有些怅惘,失望说不上。白云寺不因为了尘师父不在而失色,相反,它在我站定脚步其间时,安静心胸,沉寂浮华。
如果了尘师父在白云寺,我径直寻了他去,径直就着一杯清茶,询问喜与悲,了尘师父这次会轻易点拨,还是闭口不语?即使交心深谈,我会接受认同?我没有把握。我在俗世内,他在俗世外,我在提速飞转的螺旋中,他在幽寂芬芳的莲花上。恰如咖啡对茶水,钢筋对树林——不是不能并论,而是相提时的合适路径,能否出现,这是互通东西或南北的前提。
不失望的原因是,我似乎找到那条路径,还似乎就行走在那条路径上了。佛家不是讲究悟吗?悟在心,心在静,静在幽古的情思中沉淀。
拨响白光天电话,想告诉他,城市东上100里处的泗水森林中,有一个古老的小寺庙,名叫白云寺,白云寺里有个叫了尘的小师父,他告诉我,顺喜即为福。这些话几乎已经排好队,朝着我嘴巴涌动,伺机而出,但白光天没有接听电话。
我放下手机喝茶时,他来电话了,问我这些天可好,发你的短信一直没有回。当然,他不是问责,而是问候,他的声音慢而轻,令人亲切。刚才被拦住的句子再次纷涌弹跳,我把准备告诉白光天的话告诉了他。他竟然说,他知道白云寺,里面有个厉害的老和尚,名叫悟净,会指墨书法,最擅长的是左手隶书。我眼前闪现出形容枯槁,用左手写字的老僧人,他的“雪”字落在宣纸上,在停顿的刹那寡合而肃穆。
他很兴奋,在电话中津津乐道与悟净老僧人的交往。他说——悟净师父啊,出口就是金字良言,说“缘”就是“遇”——手机有来电提示,是白光天的,我只好打断他的话,对不起,我们再找机会说吧,我现在有急事。
白光天说明天下午回家,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停了几秒,回答,没有事情,就问问你。白光天嘱咐我:开心地玩,明天见。
终是没有向白光天提起白云寺。
夜幕降临时,喝完白菜清汤,我想想,又按响白光天电话,白云寺真是不得不说的地方。白光天半天才接听电话,懒洋洋地问我什么事?我嘴巴一开,白云寺就呼之欲出:我今天去了白云——白光天以噢声(类似哈欠声)打断:你开心就好。
在应酬吗?手机里似乎很安静,白光天在干什么呢?终是无法再提白云寺了。一丝怅惘浮在心头,失落又如水漫山坡般地充塞胸口。
白光天明天下午回来,要是还保全二人世界,明天一天来得及,做掉肚中的孩子,做掉他或者她,那团尚未成形的血肉,模糊、蒙昧的种子,医生说,还只是一株小胚芽,我心中似乎升起一丝亮光——这么说,还不是孩子。但是,我马上懊丧而羞愧,多么愚蠢啊,没有孩子的形状,但确是一具生命,血与肉糅合的小生命。
可我该与白光天怎么说!留下孩子,等于粉碎我与白光天的二人世界。保全我们二人世界,只有偷偷拿掉孩子。
我再次想起了尘师父,翻来覆去地想着他的话。
百无聊赖中,下楼散步,转到露天广场。排队整齐的舞蹈队几乎站满了广场,正在翩翩起舞,他们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律步履轻飘,身段柔和,前进后退,向左向右绕出一簇花团。旁边花坛上坐着三三两两的老人或者情侣,花坛间隙空阔处,我心中一动,静者在心,这么喧闹的广场,其实是静的,笃定的心安,于闹中取静,才是真静。
拖拉着脚步朝露天广场后面走去,后面是一处人工花园,花园右上方的霓虹正在流光溢彩,那是一家连锁酒店,我从来没有仔细看过它,在迷蒙的夜色中,被装饰成哥特式样的酒店有些吸引人眼球。不过,随着越来越近的步伐,我忍不住笑了,门楣与廊柱被嚣张的金纸包裹,低级俗气的模仿,很滑稽,贻笑大方。在我微笑的嘴巴还没有合拢的刹那,我愣住了。从旋转门前下车的一对男女,男的腰身宽阔,头发是气派的板寸,是白光天,戴着墨镜,给我背影,但并不妨碍我一眼认出,他在前,后面一个娇小的女人紧随其后。白光天不是明天才回来吗?
我退到花园后面,掏出手机,按响了扩听键,《海边的阿狄丽娜》清幽的音乐在蒙昧的夜色中飘荡出情深意长。白光天没有接。我想,能有什么事情?肯定是白光天单位的客人,很重要,他亲自安排,安排好了,自然会回来。
广场上的音乐声小了,跳舞的人群已经解散,黑暗的空间被前面巨大的电视屏幕投影照亮,犹如被凿出的一个方正的木格子窗户,窗户里面红尘滚滚,声色犬马,窗户外面时光幽暗,寂寥古老。我一脚正好踏在木格子窗户上,看见歪斜的投影,不成规则。信息声——是白光天,要我早些休息,明天晚上见。
我的脚似乎被钉子钉住,拔不出来了。耳边是喧嚣的谈话声、车辆声、孩子的啼哭声,似乎还有口角声,这个广场,到底是喧嚣浮华的,即使夜晚。
我请了半天假,再去了白云寺。我知道,了尘小师父肯定不在,他不可能这么快就回来,可他在不在,白云寺都还是白云寺。
我在院子中的铜鼎中烧了香火,又在一进厅堂的佛堂中跪了蒲团。直接朝二进厅堂去,枯井高阔的青石边沿晾着一幅水墨画,兴许是风吹来的,那天风很大,旁边古樟树的枝条乱摆,树叶簌簌而落,水墨画一角被风高高掀起,一角又被青石拦住无法飘舞。这样,我看见整幅画,在空蒙的积雪下,青黛的山色隐约可见,水洗般的宁静气场可触可感,但青山又以一处悬崖收笔,风景戛然而止。我不懂画,但画中意味却让我心头一震——我弯腰,拿起水墨画,只有画,未完的画,没有题字。
我重新把画摊放于枯井石头边沿。哪想,风这次掀翻了它,水墨画卷起飞舞,我伸手去抓,旁边的木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悟净老僧一脚踏出门槛,显然,画是从他的房中吹出。我抓住画,递给悟净老僧,悟净点头,解释:昨天一个朋友信手画下的。
我朝画望望,微笑着说:一看就知道不是悟净师父的画作。
悟净师父淡然一笑,说,女施主上次留下的茶叶,是好茶。
我眼睛一亮,他喝了,我有些兴奋地说,只要合乎师父口味就好。
了尘可能一年半载都不会回来。
悟净师父以为我来找了尘的,我是找过了尘,可是他不在,现在他在与不在,都没有关系了,我有大半天的时间在白云寺,看来我的运气不错,刚来就遇到了悟静师父。他昨晚在手机中说,悟静师父说缘就是遇,那么今天的遇也是缘了。
我随着悟静师父走进他的书房,轻轻掩上木板门,师父摆手,说关窗即是,门开着亮光。师父把刚才的画作摊在案几一角,继续写他的隶书。我偏头,发现案几下面的一排小凳上,晾着两三幅隶书作品,“雪”字的肃穆从高古、幽深中跃然而出,我拎出中间的一幅,很大,看得出是接纸而成。铺在地上,马上辨认出,正是我搅扰悟净师父的书法作品。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
是香山居士的《梦微之》,伤感在悟净师父高古的隶书中发酵出沧桑风骨。我望望悟净师父,心怀疑问——出家人还有悲喜?
悟净师父此时没有继续书写,而是收拾案几,看我铺在地上的隶书《梦微之》,点头自语:一寄一雪,情怀与心境皆出,女施主也喜欢香山居士?
逡巡一会,点点头——开始读《梦微之》只觉得忧伤,令人唏嘘,看见悟净师父的书法,特别是“雪”字,不禁心生沧桑,白雪茫茫,忧伤无迹,又有超脱之感,师父的隶书与这首《梦微之》相得益彰,如果可能,师父可否割爱送我?
说完顿感冒昧,脸色讪讪,又想说出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干脆坦然地望着悟净师父,悟净师父双手捧起作品,重新置放于案几下的排凳上,说,物遇喜欢它的人,算是好去处,我装裱好了施主即可来取。
悟净师父领我进入三进院子,里面兰草习习,金桂摇曳,青石板上阳光斑驳跳跃,雕花木楼上书写的“藏经阁”古朴、遒劲,旁边是禅房,断续的木鱼声与唱经声相和。我随师父走进一间简陋而清净的小房间,靠窗的案几上有一个烧炭火的小茶炉,沸水滚滚,茶炉上的盖子几经掀起,丝丝白气袅绕不息。悟净师父洗净青花瓷杯,取出一小袋茶叶冲水,正是我留下来的绞股蓝茶叶。
茶水清碧,口感先苦后甜。悟净师父抿一小口,闭目自语,苦尽甘来,清雅脱俗。
虽然师父夸的是茶叶,但我仍有欣慰之感。询问,师父如何理解脱俗。
以空还空,来归超尘……我在心中仔细领悟,以求思维跟上悟净师父的佛理,他并不执着他的说教,及时收口,问,施主为何而来?
为何而来?先是准备找了尘小师父请教,了尘师父远游四海,现与悟净老僧对饮,心中盘亘喜忧参半的纠结,可是,如何出口?
一时语塞。在茶水汩汩的欢叫中,一声悠长而浑厚的钟声响起,余音袅袅,经久不绝,顿感灵魂出窍、人在世外。
为遇师父而来。
悟净师父抿茶,面色淡泊。
师父讲“缘”为“遇”,其中定有款曲,所谓“随遇而安”,是不是随缘就是喜?
悟净师父举杯,双目平视,侃侃而谈:施主定是为心中纠结而来,明说喜实说的是忧,忧喜无界又有界,淡心为定……他把深奥的佛理删繁就简,说一颗心,我不难理解。
了尘师父曾说我怀孕有福,而在我却是忧虑。忧虑的是怕白光天知道,而非怀上孩子的事实,相反,孩子的到来——如果舍弃担心白光天知道的事实,总归是令人欢喜的。忧喜无界,淡定在心……我似豁然开朗。
始末由缘,无异风生水起,结束意味开始。我扶着清凉的砖石,心想,孩子的到来到底还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他或她令此时的我欣慰无比。
他要求与我再见面,我不同意。他说:我去过白云寺,在悟净师父那里看见你留下的纸条,我记得你的字,方正圆润,喜欢写成繁体。
我不作声,嗞嗞的电流声在耳际边震动。
还有事情吗?
别——别挂电话,他着急地喊道,然后是轻微地嘘气声,穆穆,那天晚上你在电话中提到悟净师父,我没来得及说,你就挂上电话了,我那天下午也去白云寺了,在悟净师父那里还作了画,不过,画到一半——
我脑海中立刻闪现一幅在风中掀起的雪山画,画到悬崖就戛然而止,我心中一震——果然是他。
没画好,画着画着,心思就乱了,日子怎么就又回到那天,可那天是暴雨,不是雪,我开始想画暴雨下的青山,结果画成了雪,雪白满山头……
他没完没了地叙说,我无语。我的左手搭在肚子上,一时恍惚——如果留下孩子,要不要告诉他呢?我无法启口,孩子当然与他有关,可是,此时,我心中认定,孩子只与我一人相关,来了如同我们的遇见,随遇而安,顺喜为福啊。
淡定是多么勇敢的态度——担心和忧虑,见鬼去吧。
白光天在办了手续后找我几次,他反复征询——穆穆,你必须给我最具体的理由,说什么缘分已尽的空话,等于白说。
一次是约我到一家茶楼,还有一次是晚上找到家中来。第三次,令人匪夷所思,竟然是在菜场上,他不知道菜场位置,向来对买菜深恶痛绝,认为是市侩、流俗的集散地。但他的确在菜场上与我碰面,拉住我,毫无君子风度,气咻咻地询问,事后,我突然揣摩出——他在跟踪我,一无所获后,恼羞成怒地拉住我盘问。
真的是缘分已尽。
具体的理由,是因为我那天晚上亲眼看见白光天的出轨,还是因为我肚子中属于我一个人的孩子?似乎都是具体理由,但绝对不是真正理由。如果,我把这些看成理由,我如何解释那次游览中突然而至的暴雨——它与爱情或道义有关吗?我至今觉得犹如梦幻般,难道白光天没有做梦的时候?
我不接手机,除非迫不得已的事情,他……随着我对手机的淡薄几乎不再有任何音信,连同梦幻般的暴风雨和悬崖,真正化成轻如鸿毛的碎片。
迎着微风在晨曦中散步,去菜场买合乎胃口的菜肴,淡着一颗心上班下班,周末休息去郊外散心,或者去白云寺就着绞股蓝茶水看悟净师父习字。我也爱上书法,隶书需要功力,我尚且不够,却仍有钟爱,每天都找时间临摹陆游帖子《原上一缕云》,虽是草书,却有章法可循,究竟什么章法,我私下认为,是“胸中磊落藏五岳”的心胸,那种糅合天真与朴拙的洒脱气势,简直要我痴迷。
这就是了尘师父所说的福了,果然是孩子带来的。
我走路真的是脚步拖拉,肚子圆滚滚地鼓起来,经过春夏两季,孩子几乎成形,在我不经意时拳打脚踢,提醒我注意,按时吃喝、休息,随天气变化添减衣服,保持愉悦心情。
那日,秋风萧瑟,黄叶萎地,我从医院出来,迎面碰见白光天,不,是他喊住我的,如果不是他喊我,我几乎没有注意到站在红彤彤的枫树下的白光天,虽然他还是老模样,他的喊声有些干枯——穆穆——我才发现对面的白光天,他摘下墨镜,脸色泛红。
难怪,你拼死要跟我离婚,原来是怀上了别人的孩子……
白光天嘴唇颤抖,他激动了。我咬着嘴唇,一时无语,白光天说的没错,我确实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可是与他所说的离婚理由并非因果关系。
对不起,我擦身而过,你多保重。
这个孽障,给我戴上绿帽子,不得善终的。
我的心恍惚起来,白光天骂什么呢?他若是体会怀上孩子的感觉,他肯定不会这么骂的,可白光天是男人,怎么会怀上孩子?他只在乎帽子的颜色。
秋风摇曳,接着是连绵数日的秋雨。我去白云寺取悟净师父装裱好的隶书《梦微之》,他早装裱好,我以取字为由去过多次,返回时却总忘记,我知道,有意无意之间,不过是给自己留下奔赴的缘由,可我的书法大有长进,自认为高古的隶书临摹为期已近,版本就是悟净师父的《梦微之》,我要挂在书房,日日研习,剖开纹理,参悟风骨。
打的来到泗水,然后步行到白云寺,抱着卷好的作品匆匆下山。为节省时间,能赶上泗水下面公路上的士或者公交,我选择林间小道,全部是石块砌成的台阶,我拾级而下,雨水淋湿的台阶路滑,我不小心摔倒几次,肚子剧烈地疼痛,我越发着急,慌不择路,终于在凉湿的台阶滑倒,顺着台阶朝下滚,手中的《梦微之》缓缓打开,斜铺在台阶上,挡住我滚动的身体,坚硬的石块与路边的荆棘划伤我的肩膀和双手,缕缕鲜血在悟净师父的书法作品上漫漶。
正在拾级而上的几个游客,看见倒地的我,痉挛成一团,他们抱起我。我手指台阶上的书法,他们用悟净师父的师法作品抱起我,一边拨打120,一边朝山下狂奔。
“我寄人间雪满头”,白雪茫茫中,忧伤无迹。我脑海中闪现这样的句子。孩子能否留在这个世界,自有定数,他或她的始末终有无法预知的缘,牵扯出白雪满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