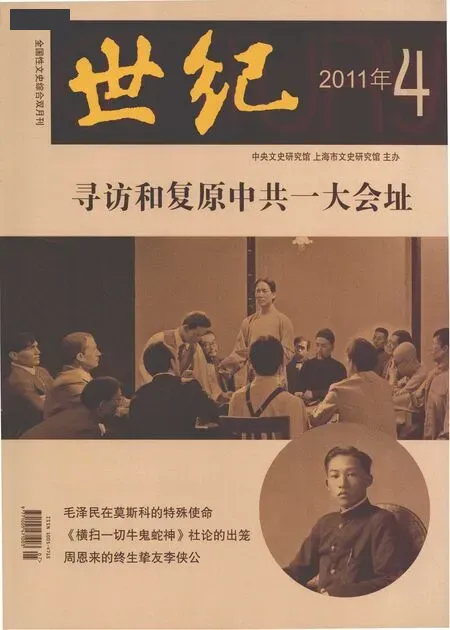我记忆中的杜家伯伯
吴耀中口述 沈润章整理
我记忆中的杜家伯伯
吴耀中口述 沈润章整理

杜月笙这个名字,老上海人家喻户晓,对杜月笙的评说,众说纷纭。杜先生谢世已数十年,想必当今在世与杜先生直接接触过的人为数不多,我是为数不多中的一个。我父亲吴锦文是杜月笙的知己,童年的我跟随父亲出入杜公馆,所以我称呼杜月笙为“杜家伯伯”。“杜家伯伯”那浑厚、低沉的高桥乡音还时不时在我耳边响起……
流浪高桥镇,初闯上海滩
上海一代闻人杜月笙,1888年8月生于浦东高桥杜家花园。杜家十分贫穷,他童年屡遭不幸。4岁时,母亲因劳累过度得病身亡。5岁,父亲杜文庆续娶张氏为妻,6岁那年盛夏,父亲染病不起,医治无效故世。杜与后母张氏依靠变卖度日。时隔不久,后母张氏忽然失踪,从此童年的杜月笙成了一名无父无母的孤儿。无依无靠,时时饥饿的啼哭声响遍乡里。数天后,杜月笙无奈,只得投奔外婆家去。年老体弱的老外婆,家境十分清贫。中餐难觅,晚餐难求,她看着饥肠辘辘、满脸泪痕的外孙心如刀割,从此这祖孙两代人以汤菜度日。当时杜的舅父黄家仁在高桥“蔡家庄”老茶馆当跑堂,收入低微,要养家糊口,已入不敷出,怎能扶养外甥。杜月笙只是七八岁的孩童,需依靠亲人扶养。外婆家如此艰难,怎能久留,只得跟随舅父来到了高桥镇上。到了镇上,整日东游西荡,在一伙游荡儿中,东家讨一口,西家要一碗,以求乞度日,衣衫褴褛,夜宿街头。
光阴易逝,转瞬间秋去冬来,单衫烂衣的杜月笙,怎能御寒过冬?蔡家庄老茶馆隔壁(高桥镇北街401号),是我祖父吴允珊开设的福兴衣庄,这是镇上唯一一家买卖新旧衣服的店铺。杜经常游荡在衣铺门前,祖父不时施些剩菜余饭给杜充饥。但杜得了施食一口不吃,包妥后飞奔离去,经常如此。祖父十分奇怪。一次,祖父宴请宾客后将剩菜余饭施于杜月笙。杜包好后仍匆忙向外奔去,不到一个时辰,杜又重新回来讨吃。祖父问杜,“侬刚才不是拿过菜和饭了吗?为啥再要呢?”杜回答说:“我一直把讨来的饭菜先给外婆吃,她老人家吃下来的我再吃。这次饭菜有鱼有肉,我外婆好久没有尝到荤菜,所以胃口大开,全部吃光了。”祖父听后非常感动,这么一个自己在饥饿中的孩子,忍饿孝敬外婆,实在难得,顿起收养之心。从此,杜不再沿街求乞,一日三餐正点,他吃饱后还给外婆送去。
饱暖后的杜月笙,不忍孤单,不时溜出店外与往日的小兄弟们混游。一年冬天,祖父给杜一身棉衣裤,但到了第二天,杜还是穿着他的单衣衫,冻得浑身发抖。祖父责怪他说:“棉衣为啥不穿?”杜说:“有个小弟兄病重高烧,他不能再受冻了,所以你给我的新棉衣给他穿了。”说完,低下了头。祖父听毕,不但不再责怪他,反而为他的义气所感动,当即再取出一套棉衣让他穿上。
祖父见杜常与一帮游荡孩子混在一起,非常担心,有心让他读书上进,不日与东街私塾邹鹤田老先生谈妥,让杜月笙和我父亲一起读书,免得再游荡街头。可杜对读书不感兴趣,半月后就逃学了。祖父生气地对杜月笙讲:“作为一个孩子,要懂得勤奋好学,如果你还同你的小兄弟们整日混混,也有可能飞黄腾达,但更多的是暴死街头,无人收殓!”
俗语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由于杜经常与一伙小混混东西游荡,染上了赌博等恶习。有一次杜偷了舅父的衣服去了当铺,得钱后又去赌,他舅舅黄家仁气得将杜重重地打了一顿。当时镇上的父老邻居都异口同声对我祖父讲:“杜是一个坏小囡,长大后侬要吃他苦头的。”祖父回答说:“不收留他肯定会冻煞,饿煞。俗话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祖父仍决心收留小杜月笙。一个冬天的晚上,祖父有意将五块银元“遗忘”在账台上,旁边放着一盏油灯。对杜说:“侬睡觉前把油灯吹灭。”说后立即离去。待到明天祖父来店时那五块银元依旧放在原处。从此祖父认定杜不是不讲信义的“坏小囡。”
杜十三四岁时,外婆和舅舅总觉得该为他寻个谋生技能。于是再三托人,几经周折,结果被举荐到上海十六铺黄文祥开设的宝大水果行学生意。我祖母闻讯后,不分昼夜替杜扎了两双鞋底,赶制成两双布鞋。并把鞋底涂上桐油,日后可以防潮湿。还连夜备了自制的硬壳塌饼交杜作路上充饥。我祖父与杜挑灯夜谈,再三叮嘱。一老一小依依不舍,直到深夜。
这天一早,祖父同杜吃过早饭后,一路送杜到浦东八字桥船码头。杜的外婆和舅舅也前来为杜送行。即将离别,总有千言万语,难离难分。祖父叮嘱杜说:“到了上海后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一定要为你在九泉之下的双亲争气!侬如果混不下去就回到高桥来,我允珊伯伯还是收留侬的。”祖父随手给了杜五块银元,要杜留着身边备用。杜含泪接受,并对着祖父深深一揖说:“我在上海不混出个名堂决不回高桥!”杜说毕上了船。众人含泪挥手而别。从此杜月笙结束了家乡高桥的童年生活。
杜来到上海十六铺,在黄文祥老板开设的宝大水果行当学徒,黄老板对杜说:“我保你吃住,但不给月规钿(工资)。侬把挑拣出来的烂水果卖了,得钱归你。”当时十六铺码头到处都是手拿扛棒的脚夫,收入低微。买些烂水果吃一可解渴,二可充饥。杜将烂水果去皮后任人吃,不论斤两,不论价钱,愿付多少就多少,因为大家都是穷苦人。脚夫们都说:“这个小囡上路。”赢得码头工人齐声赞赏。
以上所述是家父生前亲传。

感恩老乡亲,难舍浦东情
20世纪20年代,黄金荣同军阀卢永祥之子卢筱嘉相互争夺京剧名伶露蓝春,黄在共舞台被绑票后,经杜月笙与卢永祥周旋才获释放。从此黄金荣的名声日下。而杜月笙在上海声名大振。黄、杜本是师徒,经此事后即成换帖兄弟。黄金荣还将华格臬路216号整套房子送给杜月笙以作酬谢,而后就成了杜公馆。由于杜月笙初到上海时得到宝大水果行黄文祥老板的照料,杜为了报答此恩,把黄文祥之子黄国栋请进杜公馆,委以日常接待来访宾客之责任。
杜月笙时时记着孩童时寄居我家那些日子里受到的照顾,同我父亲亲如兄弟,无话不谈。早年父亲就读于圣约翰大学专修英文,杜家伯伯收到国外来函,电话邀我父亲去杜公馆翻译(凡是国内一般的书信,不论中外文由秘书处理,国外要件均由父亲翻译)。我每每跟随父亲出入杜公馆。那时公馆的东厢房布置气派,内有大菜台子、杜家伯伯办公的写字台和抽鸦片的烟榻、精致的沙发等。我清楚记得,一个星期日的下午,随父亲同去杜公馆,父亲看完国外来信后,详细解说内容。此时,进来一位身穿西装,头戴礼帽,黑边眼镜,手持手杖,风度翩翩的绅士。父亲见有贵客来访,便起身向杜月笙告辞。杜家伯伯从烟铺上下来,拉住父亲的手,深情地对来客介绍:“你们二位都姓吴,五百年前是一家。”杜为父亲介绍说:“这位就是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他又指着我父亲说:“这位是我在高桥一起长大的吴锦文先生,他现任交通部属下邮政考绩处长。我小时候父母早故,多亏他爸爸收留我。如果没有他父亲允珊伯伯照顾,哪有我今朝的杜月笙。”接着我父亲说:“英雄不论出生,过去的事不必再谈。忘了吧!”杜说:“此恩我一世不会忘记。”三人同坐大沙发上,交谈甚欢。我呆呆地望着,杜公馆总管家万墨林叔叔怕我寂寞,带我荡马路去了。

1948年8月30日,上海市工业会第一届理监事合影(前排右七为招商局常务董事杜月笙,右三为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
杜接待一般的客人,只送到大厅为止,而对我父子二人,杜一直要送到大门口才挥手告别。由于经常出入杜公馆,我们成了往来杜府的常客。自从日寇入侵后,杜从上海暂去香港,经过几番周折才到当时的陪都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杜才归上海。
我当时年岁尚小,有许多事情已经记不完全了。1949年年初,杜月笙突托朱文德来访我家,对父亲说:“杜先生说,看形势上海很难守住了,要你早作准备。”并说:“杜先生把杜美路70号整套房子已经出卖了,得45万美金。”我父亲回答:“请朱先生代我谢谢杜先生关心,此事让我考虑考虑,如果杜先生有了准确去港日期,请他一定要通知我。”片刻后朱说尚有要事去办,不能长谈,告辞而去。
1949年4月中旬,我们接朱文德来电说,杜先生已定在4月27日上午10时在公平路码头登轮船去香港。那天父亲带我同去送行。大约9时不到,杜家伯伯已在码头的候船室中等候我们了。一见面二位老人紧握双手,久久不放,心中都有道不尽言不完的话。杜家伯伯心情沉重地对我父亲讲:“有关我留去之事也考虑再三,因为我的手上有共产党人的鲜血。我想共产党是不会原谅我的,所以我非走不可。老弟啊,这次分别你我恐无再见之日了。”杜回转头来和蔼可亲的对我讲:“杜家伯伯不止一次对侬讲过:将来等侬长大了要帮我杜家办事,这个心愿恐怕不能实现了,今后侬要好好读书,听话。”我回答说:“杜家伯伯侬一定会回来的,我一定听侬话,好好读书,等着侬回来。”一个多小时深沉的谈话使俩老人双双落泪。汽笛声无情的催促着他们紧握在一起的双手无奈地松开。珍重,珍重,不舍得挥手,杜家伯伯登上了甲板从此告别。
时隔月余,万墨林叔叔从香港回来说:“杜先生再三叮嘱,去上海后先拜访锦文兄。”万叔叔又说:“杜与侬码头分手登船后,一直呆呆的站在甲板上望着浦东,直到船出吴淞口远远离去,看不到浦东后才回船舱休息。现在杜先生在香港坚尼地台买了一套房子,从上海迁去的数十人住在一起。先生闭门不出,时时与夫人孟小冬脸朝北方,轻轻地吟唱着京剧《捉放曹》中那句‘一轮明月照窗下’,还常常对着明月轻轻地自言自语,‘浦东,浦东,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浦东的此时也沉浸在明月中吧。明月呀,我杜某人何时能在浦东看到你?’”游子思乡,泪湿春衫。
(整理者沈润章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史学会名誉理事)
责任编辑 肖阿伍
book=21,ebook=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