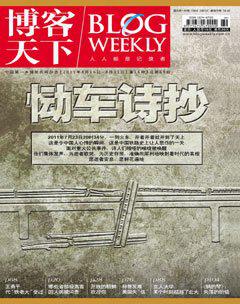文学的现实和未来
王菲宇
在为“博出位:文学,你往何处去”搜集视频素材过程中,工作人员在北大校园内采访到了一位美国留学生。即将进入北大中文系攻读研究生的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了如指掌。当被工作人员问到“你觉得自己是不是文学青年”的时候,他不由得笑了出来:
“文学青年?在今天再用这个词太傻了。”
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听起来相当时髦的称呼,在今天,已经不再流行。曾经在上个世纪燃烧了近20年的“文学热”,今天似乎也只残留下可怜的灰烬。然而不管“文学热”是否退去,今日文学地位是否尴尬,仍有无数的人关心它的命运。这些人也许是文学青年,也许与文学根本八竿子打不着。
具体到7月2日这一天,这群人中的500位,来到了这一期“博出位”现场,与两位似乎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正统作家—慕容雪村和李海鹏—一起进行了一场历时3小时的关于“文学命运”的谈话。
文学已死是个伪问题
对于当年的“文学热”,慕容雪村亲身经历。
“徐星对我来说是文学上的大哥。80年代他写了一个小说《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成为当时的姊妹篇,红极一时。当时红到什么程度呢?我到他家里看,他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差不多有这么多。”说话间慕容雪村用双手比划起厚厚一沓的样子。
写这本书的时候,徐星是一个年轻的烤鸭店清洁工,他没有读过大学,没受过所谓的高等教育,写小说完全是因为有感而发。读到《无主题变奏》的时候,慕容雪村还是一个高中生,他形容刚读到徐星的文字时,有种脑袋被人敲了一下的感觉。“我们有个成语叫做振聋发聩。确实那种感觉是特别的神秘。”2005年,慕容雪村将这篇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翻出来重读,发现感觉依然与当年差不多。“这个小说依然没有过时。我觉得在文学史上,这个作品应该是留下来了。”
与大哥徐星一样,慕容雪村也不是科班出身。但他的成名经历与徐星完全不同。2002年,慕容雪村在天涯论坛上连载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当时他在一家公司里担任高层,写小说是瞒着领导的。那一年正值中国互联网普及的高峰,慕容雪村的小说一炮而红,他本人也与李寻欢、安妮宝贝、今何在一起,被尊为中国网络“四大写手”。
在“文学热”20年后的今天,很多人叫嚣着“文学已死”。在慕容雪村和李海鹏二人看来,这是个伪问题。
“我觉得你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东西死了,但是文学这个东西是很难死的。”在慕容雪村看来,进入到互联网时代,诗人反而多了。“这个时代不是文学已死,而是文学更加平易近人了,这里就有一个重新定位文学的问题。现在的诗人比过去多上几倍,小说也是这样,到起点网、红袖网看看,现在写小说的比80年代多上几十倍、几百倍,这么繁荣你怎么能说文学已死呢?不仅没有死,而且活过来了。”
对于慕容雪村的说法,李海鹏并不完全同意。“所谓的文学已死或者文学不死,不是一般通俗文学的概念。现在之所以能够说文学是不是死了,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实际上是想讨论严肃文学是不是死了。”
谈及严肃文学,李海鹏痛快地表示,在这个时代,它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但困境也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我们说严肃文学的困境在于曲高和寡了,越是严肃的文学,大众的接受度越低。所谓艺术性必然地会和老百姓的阅读口味不一样。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有,全世界都有。”约翰·巴斯曾在自己著名的论文《枯竭的文学》表示,文学已经枯竭了,并预言博尔赫斯的写作路数是未来小说的发展方向。“因为小说基本的要素,是人物、冲突、主题,但一翻过去的小说,所有的主题都被写过了,所有的冲突都被发掘过了。过了很多年,西方的文学并不是像他预言的那样,其实路还是有无限多的,只是越来越难。前人已经有很高的成就,你不能重复,要走新路,不容易。仅仅是这样。”
中国是小说家的乐园
2009年,慕容雪村卧底进入传销集团内部。将自己的经历整理出来之后,2010年底,一部名为《中国,少了一味药》的纪实作品出版。
李海鹏的经历与调查也有扯不断的联系。在专职进行文学创作之前,李海鹏是《南方周末》的首席记者,几篇调查稿件被业界作为教材和范本。这段职业经历让李海鹏理解了现实:“小说和现实的关系—即便我不写—但是对理解国家,理解这个社会,终究是有好处的。你做记者很多年之后,确实会接触到很多日常生活接触不到的层面。一是信息的接触,二是你慢慢有一个分析的方法,将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而作为一位现实题材的作家,在面对每天精彩纷呈的现实的过程中,慕容雪村感到了一种无力的感觉。
“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层出不穷的怪事。现实比我们读到的文学作品还要精彩,2008年我写了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很多人说怎么是这样,超出想象,其实有很多更超出想象的,我都没有敢写。”近来慕容雪村始终在关注郭美美事件的进展,他发现这个事件精彩的程度远超过许多小说。“如果有人用纪实的笔法,从怎么暴露到怎么揭开谜底,这就是一个精彩的小说,精彩程度是我这样的作家想象不到的。”
今年,慕容雪村本来有机会前往澳大利亚居住一段时间。但几经思量,他还是放弃了。“我觉得中国这片土地实在太好了,简直是小说家的乐园,每天能出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对于一个小说的作者尤其是现实题材的作者,活在这个时代,让我特别骄傲。”
在这样一个不缺小说故事的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表现却并不如人意。几年前,德国汉学家顾彬的“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言论曾经掀起轩然大波。顾彬的观点虽然在传播中被媒体刻意歪曲、放大,但从某一方面,也暴露了当代文学差强人意的既存事实。
对于顾彬的观点,李海鹏表示可以理解。“说中国现代文学都是垃圾,差不多吧。事实是这样的,你总要比较,和英国、美国、法国没法比;即便和印度、拉美国家也没法比,也差得太多。这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了,最重要的原因是—虽然听起来不太舒服—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曾经几次元气大伤,例如几十年前,差一点到了被毁灭的程度。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是逐渐在恢复过程当中,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也是正常的。”
或许比起争论“文学是否已死”的问题,思考如何恢复中国文学更有意义。这个功利主义主导的时代,文学的尴尬无处不在。在现实的利益之前,作为精神财产的文学屡屡被质疑存在意义。慕容雪村即亲身遇到这种质疑。“在深圳的咖啡馆里,有一个老板严厉地问我,在这个年代,你写这种东西有什么价值?但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什么用处,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被盖,也不能解决马桶堵塞和电灯泡不亮的问题,但恰恰是这些东西,我说的就是诗歌、小说、音乐、绘画,我们称之为文学和艺术的这些东西,它是人和动物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嘉宾简介
慕容雪村:本名郝群,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作品多次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著有《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多数人死于贪婪》《中国,少了一味药》《原谅我红尘颠倒》等作品。
博客网址:
http://blog.sina.com.cn/hawking
嘉宾简介
李海鹏:朝鲜族,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记者、《第一财经周刊》专栏作家、《GQ》专题总监。出版有随笔集《佛祖在一号线》,近日出版的《晚来寂静》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博客网址:
http://blog.sina.com.cn/lihai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