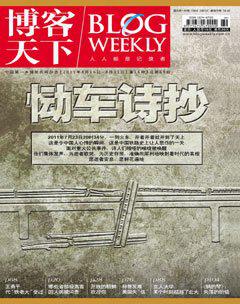武汉“热”与“干”
卜昌炯
很少有哪个城市的人们会像武汉人这样,有着如此统一的爱好。一日之计在于晨,而他们把每天早上的第一顿饭随随便便就交给了热干面。
这个习惯他们已经保持了很多年,并且不打算与外人分享—热干面从诞生至今,几乎没有走出武汉。
不是它认生,一到外地、一遇见外人就表现失常;而是即使它发挥得再出色,也很难抓住陌生人的胃。曾经,一些充满理想的食物推广家们试图把它像山西的刀削面、四川的担担面一样推广至全国各地,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它的地域性实在是太强了。芸芸众生,它只取悦武汉人;美食三千,武汉人也只对它情有独钟(在武汉众多著名小吃中热干面排名第一,超过鸭脖子与豆皮)。
这和热干面本身的材质有很大关系。严格点儿说,它算不上什么美味,很多第一次吃它的人都会觉得干涩、难以下咽,遂再也不想吃第二遍。
但到了武汉人这里,完全变了个样,因为他们从小就吃它,所以更懂它、爱它,长期积累下来了一种互为知音般的情愫—两看相不厌,唯有热干面。
说起来,热干面的诞生也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的故事。上个世纪30年代,汉口长堤街有个叫李包的食贩,以卖凉粉和汤面为生。一天,天气异常炎热,他怕面条发馊变质,便将未卖完的剩面煮熟,捞起来晾在案板上。不料一不小心,案板上的油壶被他弄翻了,洒出很多麻油,醇香四溢。李包见状,很是心疼,为了减少浪费,索性把面条放到撒出来的麻油上拌匀,然后重新摊开晾放。第二天早上,李包将这种拌了油的熟面条放在沸水里烫了烫,用笊篱沥干水分,随手又放了点儿芝麻酱、葱花等作料,卖给食客。不承想,人们吃得津津有味。有人问他卖的是什么面,他见刚出锅的面热气腾腾并且毫无水分,便脱口而出说是“热干面”。
一份让武汉人“醉生梦死”的世俗小吃就这样横空出世了。它的诞生迅速迎合了大武汉长久以来形成的商埠和码头文化。由于它价钱便宜、分量实在、等待时间短且便于携带,一下子成了早出晚归、不可能把生活过得很精致的码头工人和行商小贩们过早(当地人把吃早餐叫过早)的首选,不分四季,风雨无阻。
时至今日,虽然武汉的码头文化已经没落,但这种文化对武汉人生活的影响已经渗透到骨子里。武汉人很少有在家自己做早餐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外面买着吃,并且还要在路上吃。这是武汉市独有的一道人文景观。
所以,走在清晨的武汉大街上,经常能看到一群脚步匆匆的路人,擎着一碗面,边吃边走。不论是小伙子还是姑娘,不论是农民工还是城市白领,此刻他们并无分别,都是热干面的粉丝。
武汉人的生活节奏真的如此紧张吗?可能并非如此,一种生活习惯而已。恰好,热干面将它一直延续了下来。
从小吃热干面长大的武汉人,身上也难免带了一些热干面的习性和品质,即“热”和“干”。
“热”是热情。武汉人的热情不仅体现在待人接物上,更体现在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上。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中间是平地,周围是丘陵—武汉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水深火热的环境中,夏天湿润的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干冷的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被这种气候磨砺出来的武汉人,如果没有一种对生活的热情和韧劲,可能早就被淘汰了。
武汉作家池莉曾经写过一篇名叫《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短篇小说,里面主要讲述的就是一群在酷热环境下生机勃勃地生活着的武汉人:在一个体温计刚拿到室外就爆破了的夏天,一群男男女女在高温下热烈地谈着恋爱,放肆地开着玩笑;在空调还未普及的年代,他们把竹席和饭桌搬到了大街上,在街上吃,在街上睡,上演着一出出地道的生活秀……
池莉以擅长描写武汉市井文化著称,她笔下的武汉人热闹、喧哗,非常地有活力和质感。他们是现实中武汉人的缩影。他们爱生活,更爱武汉。
透过武汉人对生活的这份热爱,还可看到他们骨子里的乐观。最能体现这种精神的莫过于这个夏天刚刚开始时,武汉人迎来的那场大雨。
这场大雨后来下到其他城市时,统统都被称为“百年一遇”,但武汉人根本都不屑这个词。什么叫“百年一遇”?真是没见过世面。
在出门就见大江的武汉人眼里,被暴雨淹没的武汉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水上乐园,它虽然带来了很多不便,但也带来了很多乐趣。“到××来看海”这个流行一时的句式最初是从武汉传开的。他们在洪水中自拍,沿着斜坡冲浪,驾着沙发在马路上“漂流”,有人还在暴雨中看到了商机,骑着三轮车出来搞有偿摆渡……
一向声名在外的武汉公交车司机们也再一次展现了他们“神一般的存在”,在小车纷纷熄火,摩托车、自行车更是迈不开腿的情况下,他们驾着公交车乘风破浪而来,哪怕水已漫过车轮。于是,这场大雨过后,武汉公交车司机们也有了新的传说:他们不仅是上辈子折翼的F1赛车手,还是上辈子折翼的老船长。
“干”是干爽。武汉人不像南方人那么温润,也不像北方人那么粗犷,“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使得武汉人的性格有一种兼容并包之势,同时又自有特色。
他们可能有些吵吵闹闹,但绝不婆婆妈妈。在武汉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学者易中天在《读城记》一书中称爽朗是武汉人性格的核心,“爽朗之于武汉人,犹如精明之于上海人”,它不但意味着一个人够不够意思和有没有意思,而且甚至决定着一个人会不会被人看得起。
武汉人的这种性格渗透在了日常的一言一行中,他们说话办事向来都是直来直去,很少打埋伏,更没那么多小情小调和弯弯绕。他们的口头禅是“搞么事”和“么样搞”,意思相当于“干什么”和“怎么办”,可见他们不怎么会耍花枪,更注重务实。
当然了,武汉人有时候也会爽朗过头。其特征是易怒、脾气大,不爽时爱飙一两句“汉骂”,最常见的词是“婊子养的”和“个板马”。天气热,人心躁—这是外界推测武汉人脾气火爆的最简单逻辑。
一些初到武汉的人经常会被这些极富异地“风情”的对白给吓到,以为他们在吵架。其实也不一定,有些可能是真的在吵,但更多的是为了活跃气氛。这在一些比较开放的家庭中也经常看到。小孩在大人面前说,大人在小孩面前说,都属正常,因为这个时候,它们真的只是语气词而已。
所以,和武汉人打交道,一定不要被第一印象所主导。“与武汉人相处时间短的人,多半会对武汉人持贬意评价;但时间长了就会体会到武汉人性格的可爱。”这是武汉另一位女作家方方给大家的一句善意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