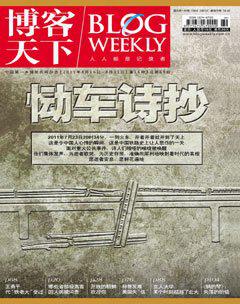香港:购物天堂大缩水
陶冬
笔者的一位朋友去年圣诞节来香港,在Burberry看中一件T恤,穿越人山人海找到售货员,要求试小一码的另一种颜色。售货员推搪说“你先试这种颜色”。朋友坚持要看另一种颜色衬不衬自己,售货员说“那你要等大约半个钟”。朋友掉头便走,今年再也没见她来港购物。
铜锣湾的池记曾是笔者常光顾的餐厅,那里的云吞面、牛腩面想起来便令人流口水。不过,在可预见的将来笔者都不会再去,因为最后一次光顾体验很糟:菜太咸,面是温的,抹光的桌子上仍有一片水迹,端面的手指居然浸在汤里。人潮涌涌和训练不足,令服务质量大幅下降。
汇丰银行名气够大,上次陪朋友去那里的经历却令笔者惊诧不已。内地专程飞来的朋友需转账,因证件不齐被拒。客户经理脸上充满着不屑,既没有任何变通,也不为他们下次来港所需文件画出路线图。笔者看不过眼上前交涉,想要他一张名片,答案居然是:“你不是我的客户,不能给。”当我们愤然离去时,这小子居然隔着楼梯叫喊,“你们不尊重我们的专业精神”。
笔者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每次听到“蝗虫论”都会挺身反击。笔者对香港也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2003年“SARS”之后,香港经济一片萎靡,信心低落。内地游客的自由行,挽救了消费信心,挽救了低端就业市场。内地游客对香港服务业市场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然而,香港服务业的质量也随之逐渐出现了“内地化”的倾向。名牌店里的销售对不讲普通话的顾客“狗眼看人低”,对讲普通话的顾客又降低服务标准。名牌店外也是一样,由于客流过大、管理不严,服务水准比10年前明显下降,购物、饮食的体验与欢愉大打折扣。
笔者那些真正的高端消费者朋友(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内地)来香港的次数愈来愈少了。因为这里只剩下金钱的喧嚣、LOGO的炫耀、暴发户的无理和销售的怠慢。在他们眼中,当高租金吞噬掉具有香港特色的商铺餐厅之时,当销售以顾客的钱袋来判断其价值之时,香港服务业正在迷失自我。他们静静地将购物地转向欧洲,转向网络。
其实香港现在并不便宜。尽管没有进口税、消费税,但租金昂贵,名牌手袋、服装的价格多比欧洲高,而在购物消费时却令人感到进入了菜市场,喧嚣拥挤。于是,劣币驱逐良币。名牌店愈来愈多,服务质量却愈来愈差,真正的高质量消费者开始敬而远之。也许香港商家对此并不介意,有钱便是娘,管他高质量、低质量。其实内地消费者学得快,变得也快。他们对服务质量早晚一定会有要求。
与零售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香港股市。在美、加上市的中国民企深陷“会计门”,股价、股民均受伤匪浅。“会计门”对香港的影响就小得多。这要感谢香港监管当局对质量的坚持,对账目的严格审查。监管者不为生意而降低门槛,不为短期利益而曲意奉承,为上市公司的质量提供了保障。虽然造假很难完全排除,但系统性作弊的风险要小得多,这样的市场令投资者放心,成就了香港股市世界排名第三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