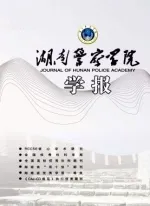群体性诉讼请求权范围的研究
刘 东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群体性诉讼请求权范围的研究
刘 东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群体性诉讼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诉讼的诉讼制度,其不但可以解决多数人纠纷,还能够起到预防和威慑的作用。群体性诉讼之所以有这种预防和威慑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在这种制度中可以提出损害赔偿以外的请求。对国外群体性诉讼的请求权范围加以研究,可以更好的了解该制度的功能,并能够为我国群体性诉讼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提供借鉴,可谓意义重大。
群体性纠纷;诉讼请求;集团诉讼;团体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
一、问题的提出
群体性纠纷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其中影响最大的包括团体诉讼、选定代表人诉讼、集团诉讼已经示范诉讼等等。这些诉讼制度中,美国建立的是对被告方威慑力最强的集团诉讼制度;德国的团体诉讼重在制止侵害的继续或防止其发生;日本则是在扩大共同诉讼制度的适用和借鉴美国集团诉讼的基础上,使其选定当事人这一制度具有了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功能。关于群体性诉讼制度,已经有许多研究成果,不过在诉讼请求范围方面,迄今却罕有涉猎。查阅多位学者的专著或论文,大部分著作中没有涉及诉讼请求范围问题,很少一部分著作虽有提到,亦只是初步的做出介绍,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诉讼请求是诉讼进行的主要推动力,当事人为了使诉讼请求能够实现进行诉讼,法院依据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判决,可以说其在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中的地位都相当重要。诉讼请求由两部分构成,“即原告针对被告的一定法的利益之主张,以及原告针对法院的承认主张并做出判决之要求”。[1]在普通的两造诉讼中,当事人只能通过处分自己的诉讼请求来处分实体上的权利,这种处分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①当事人在起诉时提出诉讼请求,以此来决定法院审理的范围,进而达到保护实体权益的目的;②在诉讼开始以后,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或者其他原因而放弃诉讼请求,达到处分实体权益的目的。可见,在两造诉讼中提出合适的诉讼请求可以最大程度上实现实体上的权利。群体性诉讼是在两造诉讼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造诉讼与群体性诉讼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因为群体性纠纷的解决而特别必要时,对“两造诉讼”的构造作出限制、调整和突破;或者借助诉讼之外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对“两造诉讼”的制度真空予以补充。[2]基于两者密切的关系,适用于两造诉讼的理论和方法当然也适用于群体性诉讼,所以,关于群体性诉讼中诉讼请求的问题具有研究价值。
二、各国群体性诉讼的诉讼请求范围
(一)美国的集团诉讼
美国集团诉讼的内容主要规定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23条中,要求提起集团诉讼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集团人数众多,以至所有集团成员合并进行诉讼实际上不可能;(2)集团的所有成员有着共同的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3)代表人的请求和抗辩是整个集团请求和抗辩的典型;(4)代表人将公正并能充分地保护集团所有成员的利益。[3]同时23条(b)款规定了集团诉讼的维持条件,将集团诉讼分成了三类:即(b)(1)类“必要的集团诉讼”案件、(b)(2)类、“寻求共同保护的集团诉讼”案件以及(b)(3)类“普通集团诉讼”案件;对于(b)(1)类案件,联邦最高法院还以判例形式作了两种分类,它们是必须与不作为请求权相结合的(b)(1)(A)类型集团诉讼,以及必须以证明被告的资产不足以赔偿全部受害人为适用前提的(b)(1)(B)类型集团诉讼。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b)(1)类型集团诉讼相当于人数众多的必要共同诉讼,在这种类型的诉讼中,当事人本来应当全部出庭参加诉讼,只是出于现实考虑才将其归于集团诉讼类型中来,所以当事人可以提出能够在普通诉讼程序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此外法院判例确定的(b)(1)(A)类型集团诉讼的形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即提起集团诉讼的当事人可以请求经济赔偿以及其他救济;从(b)(2)类型集团诉讼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法院既然可以最终做出恰如其分的禁令性补救办法或宣告性补偿办法,当事人就可以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b)(3)类型集团诉讼是在现阶段被运用最多的诉讼制度,并且有大量做出惩罚性赔偿的判例,基于此,当事人也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根据以上分析,美国集团诉讼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任何旨在彻底解决纠纷的请求,包括不作为请求,损害赔偿请求,宣告性补偿请求,惩罚性赔偿请求等等。
(二)德国的团体诉讼
德国的团体诉讼,是一种赋予某些团体诉讼主体资格和团体诉权,使其可以代表团体成员提起、参加诉讼,独立享有和承担诉讼上的权利义务,并可以独立作出实体处分的制度。[4]根据相关法律,根据各种特殊法律取得当事人地位的团体只能就他人违反特定禁止或无效的行为[5],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不作为。据此可以认为德国团体诉讼中,原告一般只能提起不作为请求之诉,这些诉主要属于确认之诉或变更之诉,像一般诉讼中的给付之诉,例如请求损害赔偿是不允许被提起的。如果必须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法律作了变通规定,即团体成员如果受有经济损失,可以以任意的诉讼担当方式授予合法团体以正当当事人资格,由获得授权的团体代替成员进行诉讼,获得判决。这样,法院的判决效力即及于进行诉讼的团体,也及于该团体的成员。
团体诉讼的内容有很多,不过作者只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从中可以看出,德国团体诉讼的原告一般情况下只能向法院提起不作为诉讼,有关损害赔偿的请求,除非有团体成员或被害人的授权,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团体诉讼的诉讼请求内容是禁止某种行为或命令被告停止正在进行的行为。
(三)日本的选定当事人诉讼
选定当事人制度是日本的一项当事人制度,虽然与集团诉讼一样,都为了解决群体性纠纷而设计,但是运用选定当事人制度的条件却比集团诉讼的更加严格。在对选定当事人制度和共同诉讼进行对比后,发现两者的差异并不是很大,甚至可以认为选定当事人制度是共同诉讼的在特殊情形下的延伸。“选定当事人制度较多地具有共同诉讼的一般性,从而兼顾了与民事诉讼原有理论体系的协调”。[6]
选定当事人制度是慢慢的发展起来的,起初只是以必要的共同诉讼表现出来,在这里,必要诉讼中的一人根据诉讼担当可以为其他人进行诉讼,剩余的人必须退出诉讼。这种制度只能解决人数相对固定的纠纷,随着公益性问题的出现,制度的功能必须扩大,利用选定当事人制度解决人数特别众多的纠纷逐渐的有了依据。相应的,其效力可以拘束所有的利害关系者,[7]这点说明了选定当事人制度开始借鉴集团诉讼来解决相关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选定当事人本身的范围,所以值得讨论的仍然是从共同诉讼制度延伸出来的选定当事人制度。
既然选定当事人制度是共同诉讼的延伸,那么共同诉讼中的相关理论可以在选定当事人诉讼中获得适用,例如共同诉讼人的行为理论、判决的扩张效力理论等都可以在选定当事人制度中适用。所以选定当事人制度中有关当事人可以提起的诉讼请求范围问题亦可以借助共同诉讼理论加以解决,具体言之,选定当事人诉讼中的原告可以向法院提起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一般诉讼中可以提出的不作为诉讼请求、损害赔偿请求等都可以出现在诉状上。
三、诉讼请求差异形成的原因分析
上文对几种典型的群体性诉讼制度中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范围作了介绍,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每种制度中的诉讼请求范围都有差异,此外,一种制度在不同情况下的诉讼请求又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可以说,每种制度都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尤其是德国的团体诉讼制度,理论界一直存有批评,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但是,立法机关并没有因为这些缺点的存在而从根本上修改法律,各国的群体性诉讼制度在保有各自特色的前提下获得了稳步的发展。每一种现象的发生都有各种原因,包括内部的原因和外部的原因,各国群体性诉讼制度诉讼请求范围存有差异亦有其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加深对此种制度的认识,接下来笔者将对几种群体性诉讼制度诉讼请求范围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内部原因
1.程序正义的要求
程序正义是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是民事诉讼首要的和最高的价值目标,民事诉讼制度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正义性。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首次对程序正义进行了系统性阐述,并将程序正义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不过这并没有使正义的概念得以明确。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程序正义的标准有了初步的统一的看法,主要包括以下标准:(1)裁判者应当是中立的;(2)程序能确保厉害关系人参加;(3)当事人平等的对话;(4)保障当事人充分的陈述主张;(5)平等的对待当事人;(6)充分的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7)当事人不致受到突袭裁判。[8]
各国群体性诉讼设定诉讼请求范围的时候都考虑到了程序正义理念的落实,美国的法律为集团诉讼的成立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即提起集团诉讼的代表人在诉讼中提出的请求和抗辩,必须是典型的请求和抗辩,之所以对请求权的限制性规定就是为了让那些诉讼参与人可以充分的代表诉讼外的被害人,使没有参加到诉讼中来的人获得类似于程序正义的保障。在具体操作中,(b)(1)类型诉讼是必要共同诉讼的扩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必要集团诉讼人的关系,(b)(3)类型诉讼实质上是普通共同诉讼的扩大,[9]这两种种诉讼运行过程中有共同诉讼制度的保障,当事人请求权的提出不受限制可以保证程序上的正义的实现。(b)(2)类型的诉讼属于寻求禁令型和宣告救济型集团诉讼,这类集团诉讼在实践中常常发挥着社会改革的作用,相当于公益性诉讼,法律将请求范围限定在禁令性和宣告救济性判决之类,而不允许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就是为了防止诉讼实施者任意的处分大众的权利,而将有关损害赔偿的问题留待受害者自己实施,追求程序正义的意图可得而知。
相比于集团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追求程序正义的意图更加明显,其法律规定符合资格的团体一般情况下只能提起不作为之诉,若要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则要获得团体成员的授权。这种制度设计就是为了赋予被害者更多参与诉讼的机会,保障当事人的处分权,避免厉害关系人遭受诉讼突袭。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与美国集团诉讼(b)(1)类型诉讼以及(b)(3)类型诉讼相似,在此不再赘述。
2.既判力理论的要求
终局判决一旦获得确定,就产生了既判力,对法官和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群体性诉讼涉及的当事人众多,法院对群体性诉讼请求做出终局判决后,受到该判决拘束的主体数量众多,他们针对同一问题不能再次起诉。因此,在群体性诉讼中提出一个适当的诉讼请求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如果诉讼请求适当,那么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会获得很好的保护;如果只提出了部分诉讼请求或诉讼请求提出的不彻底,由于利害关系人此后不能再次提起诉讼,他们的权利将会继续受到侵害而得不到保障。
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和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是由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的,对既判力的要求非常严格,为了充分的保护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法律对诉讼请求范围并未做多少限制,就是希望当事人能够穷尽诉讼主张,使权利获得最佳的保护。与美国和日本相反,德国的团体诉讼制度规定在特别法中,符合条件的团体依据特别法提起不作为诉讼以后,其成员的利益如果未得到全面的保护,可以继续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损害赔偿,这就决定了在团体诉讼制度中能够提出的请求一般只限于不作为请求。
3.诉讼效率的要求
诉讼效率也是制度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在保证正义的前提下提高诉讼效率是实务界和理论界共同追求的目标。正义和效率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具体到诉讼请求这一问题上,诉讼请求如果过于复杂,则诉讼过程越长,不利于对当事人权利的及时保护;相反,如果诉讼请求太简单,诉讼效率问题获得了解决,正义问题却浮现了出来。所以,能否提出一个适当的诉讼请求是衡量一种制度是否成功的重要的标志。群体性诉讼关涉到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是整个群体或社会的问题,所以越是能够快速的解决,越能够实现群体诉讼的价值。
德国团体诉讼正是考虑到了这个问题,首先通过特殊立法要求法院作出不作为的诉讼判决,由于团体诉讼制度中不能提起损害赔偿请求,所以一个案件可以较快的获得解决,这对于防止被害人的权利进一步受到侵害有非常大的意义。有关损害赔偿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样即能提高诉讼效率,又能使被害人的权利获得充分的保护,可谓一举两得。美国和日本的诉讼制度虽然不能明显的看出对诉讼效率的考虑,但是诉讼效率对诉讼请求范围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外部原因
1.一国独有法律环境的影响
世界各国之所以形成形式迥异、指导思想不同的法律制度,主要是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已经立法者观念等多方面的影响。前四个因素可以视为该国的法律环境,在此予以探讨,立法者观念由于具有独立的价值,特作专门的探讨。具体到团体诉讼,其制度的设立和运作同样无法逃离法律环境的束缚。群体性诉讼发展至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性问题,各国针对此问题构建了多种诉讼制度,典型的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诉讼制度,此外还有欧洲国家的示范诉讼、澳大利亚的集团诉讼等等。虽然均是为了解决群体性纠纷,但是在制度的设置和运作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就是就是因为法律环境的不同。拿德国来说,团体诉讼是众多群体性法律救济的一种,不过却获得了最快的发展,受到了当局的青睐,这曾经一度成为困扰立法者的问题。后来经过学者的研究,才发现德国一直处于这样的背景当中:(1)现行法律体系的自由主义风格必须维持;(2)经济团体在德国的充分发展。使得立法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团体诉讼,而不是某种行政性的救济方式,[10]所以团体诉讼中可以向法院提出的只能限于不作为请求。
美国法律是英美法系的代表,崇尚从事实出发,在一个案件中彻底的解决与该案件相关的所有纠纷,所以在集团诉讼中很少看到对诉讼请求进行限制的条款,即使有限制也仅限于少数特殊情形。日本法律受到德国法和美国法的双重影响,所有表现出的特点是比团体诉讼制度开放,法律允许所有的救济手段;不过任然比集团诉讼保守,最鲜明之处就是不允许惩罚性赔偿的提出。因此,一国的法律环境对诉讼请求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
2.立法者观念的影响
法律是由具体的个体制定的,这些个体既有专门从事立法的,也有理论界的专家学者,这些人在立法过程中价值观念发生的碰撞,经过反复的对立和妥协,最终制定出一部完整的法律。所以制度的设立无法逃避立法者观念的影响,他们所持的态度总会或多或少的影响法律的走向,有时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
群体性诉讼制度涉及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通过该制度的运行,是为了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还是对加害人进行威慑。如果只是为了赔偿受害人,那么请求权范围可以只限定在损害赔偿上,要是想对加害者进行威慑,则诉讼请求范围可以扩张至惩罚性赔偿。所以,立法者如果持有的观念不同,所创设的法律会截然不同。
总之,群体性诉讼制度诉讼请求的范围由多个因素决定,每个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不相同,但是在每一种诉讼制度中总会有一个因素起决定作用,这是各国群体性诉讼制度请求权范围形成的基本规律。
四、国外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遇到过的环境污染案件、公害案件以及消费者权利遭受侵害的案件,在我们国家也屡见不鲜,特别是伴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新型的金融消费者和证券业消费者群体利益被侵害的案件也多了起来,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影响,还会影响到我国的社会秩序。在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可以用以解决类似国外的群体性纠纷的制度就只有代表人诉讼,而且法律条文只对代表人诉讼的基本要件以及诉讼中的一般问题作了介绍,对于那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范围问题,以及诉讼请求权的范围与代表人诉讼制度功能的关系问题,代表人诉讼制度却并未涉及。笔者以下主要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依据新诉讼标的论,诉讼标的就是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决定着当事人权利请求的范围以及法院进行审判和作出判决的范围,所以诉讼请求范围的大小决定了个案纠纷解决的能力,进一步说,诉讼请求范围的大小决定了某种制度解决纠纷功能的大小。我国虽然在实践中遵循旧实体法说的诉讼标的论,但这种现状并没有影响到诉讼请求范围与制度功能的关系。依据旧实体法说,一个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一个诉讼标的,那么当事人为了使自己的请求获得成立,可能从诉讼的开始到结束引入多个诉讼标的,这样诉讼请求与制度功能之间通过诉讼标的这个媒介联系起来,最终的结果与新诉讼标的论情形是相同的,即诉讼请求范围决定制度的功能。所以,代表人诉讼制度请求权范围越适当,制度本身的功能就越能扩大,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就越全面。
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对代表人诉讼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中原告能够提起代表人诉讼的却寥寥无几。即时最终成功的进入审判阶段,这些案件的诉讼请求也是以纯粹的金钱赔偿为主,附带的不作为之诉或者纯粹的不作为之诉在我国现存的司法体系中没有发展的土壤。当事人只为眼前的直接利益斗争,对于防止以后类似情形的发生却不甚关心,这一方面与经济发达的程度不够有关,也与立法的规定有关。[6]法律的滞后性无法根除,这是由法律的特性决定的,不过当这种滞后已经与现实严重背离,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时,就有必要加以修改了。我国代表人诉讼已经不能全面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了,因为代表人诉讼是共同诉讼的延伸,法律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作了限制,依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条款,损害赔偿以外的请求,例如不作为请求和惩罚性赔偿请求是不被允许的,而这些请求在当事人权利保护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实性情况表明我国民事诉讼法允许提起的诉讼请求已经不能全面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急需作出改变。
上文中已经对诉讼请求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些原因决定了各国群体性诉讼的请求权范围的形成,所以我国民事诉讼法诉讼请求权范围的修改也要受这些原因的制约。首先,程序正义理念必须得到贯彻。若要实现程序正义,当事人提出自己主张的机会要获得保障,并且不会受到裁判突袭。依笔者的观点,与单个利害关系人联系密切的诉讼应当由其自己实施,涉及公益性的诉讼应当由可以代表公众的主体实施,这样的诉讼结果才能不违背程序正义。其次,诉讼效率和既判力理论的制约。当事人在系属于法院的案件中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必须能够全面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保证有关当事人在诉讼后不会因为一事不二诉理论的限制导致剩余的权利无法获得法院的保护;同时,不能漫无目的的提出诉讼请求,造成诉讼拖延,造成急需保护的权利无法获得得到及时的判决。最后,立法者应当重视本国国情,及时改变自己不合时宜的观念,力争设计出一种最适应本国的法律制度。
基于上述因素的考虑,笔者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出以下意见:第一、应在民事诉讼法中添加不作为诉讼类型,并且将不作为之诉按照与金钱赔偿之诉的关系,区分成为完全的不作为之诉和不完全的不作为之诉;第二、对于不作为之诉的适用条件作出规定。比如在完全的不作为之诉中,有关人数的问题可以继续沿用代表人诉讼的规定,不过可以放宽条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以公告代替登记即可;代表人的行为方面可以借鉴集团诉讼的规定,用事后的不提起异议即可确定代表人行为的效力替代当事人事前的授权。对于附带的不作为之诉则仍然适用现行法律的规定。第三、试探性的允许惩罚性赔偿请求。惩罚性赔偿可以起到威慑的作用,防止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可以最大限度上保护受害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在这个方面进行探索,或者在法条中加入总括性的条纹,或者对若干种特殊情形进行归纳,以列举的形式加入法条之中。
五、结论
总之,诉讼请求与权力保护有着密切的关系,诉讼请求适当与否决定着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能否获得充分的保护。根据国外经验,诉讼请求范围的设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立法者应当重视这些因素。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功能,但是在诉讼请求的设计上不够合理,无法全面的保护受害者的权益,需要加以调整,这就需要对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进行修改。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已经公布,为了应对群体性纠纷,草案中特别加入了公益诉讼制度,建议增加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①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八条但是仍然没有涉及到公益诉讼中可以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范围,我们应当借着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完善群体性纠纷解决的制度,以期对被害者权利予以最完善的保护。
[1][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16.
[2]吴泽勇.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原理[J].法学家,2010,(5).
[3]史蒂文·苏本,玛格丽特·伍.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M].蔡彦敏,徐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90
[4]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
[5]G.Baumgatel.Die verbansklage[R].竹下守夫译.民事诉讼法杂志(第24号)1978.154.
[6]肖建华.群体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比较研究[J].比较法研究,1999,(2).
[7][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202.
[8]张卫平.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与选择之根据[J],现代法学,1996,(6).
[9]杨严炎.群体诉讼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7.
[10]吴泽勇.德国团体诉讼的历史考察[J].中外法学,2009,(4).
Key works:mass disputes;claim;group litigation;organization litigation;selected parties litigation
Research on the Scope of Claims of Mass Litigation
LIU Do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Putuo District,Shanghai,200063)
Mass litigation is a legal syste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litigations.It can not only solve the disputes for most people,but also play the role of prevention and deterrence because such a system can be made for other requests besides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Researching on the scope of claim of foreign mass litigation can make people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of the system,and can also provide a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mass litigation system.Therefore,it's of great significance.
D925.11
A
2095-1140(2011)06-0059-05
2010-10-11
刘 东(1987-),男,安徽六安人,华东政法大学法院2010级诉讼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研究。
叶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