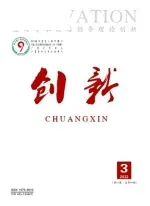再议20世纪前半期汉人村庄研究的缘起
杜靖
再议20世纪前半期汉人村庄研究的缘起
杜靖
对20世纪前半期汉人村庄研究的国内背景因素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就拉得克利夫-布朗和雷蒙德·弗斯对于推进中国村落研究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说明。希望对拙作《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的不足有所弥补。
汉人村庄;研究缘起;20世纪前半期
在笔者对村庄的研究中,就20世纪前半期中国村庄研究的背景和原因,笔者曾提出一个“内在诉求”与“外在诉求”相结合的观点,即:西方欲把中国结构融进以自身为轴心的世界体系之中,因而想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而在中国这一方来说,自身因应对外来冲击而欲救亡图存和自我发展,强调“以农立国”,从而亦想认知乡土社会。在这双重背景下,中国村庄研究的序幕得以拉开。[1]
限于篇幅,笔者未能对国内背景因素详加展开,同时亦未能把国际上个别人类学家对中国村庄研究的直接推动放进去,在此欲补充之。
一、民族救亡图存和自我发展的内在诉求背景
乡村研究的国内背景因素宜分为两个时期来讨论。初期原因是西方的入侵、国内的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造成了对乡村的破坏,有识之士存仁人之心,遂开展乡村教育运动或建设运动,由此不得不先认识乡村。后期推动乡村研究的背景很大程度上与国共两党对乡村的各自倚重、解释和定义有关联。当然,乡村教育运动和乡建运动的后期也有了“国共两党对乡村的各自倚重、解释和定义”的因素在里面。
乡村教育运动的发起人晏阳初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长久以来的积弱积贫,一是西方的入侵。他在《农村运动的使命及其实施的方法与步骤》中说:“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2]他接着说:“自鸦片战争以致现在,已经有九十余年了,甲午之战,到现在又整整40年,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要求。到今日也匆匆18年了,这些关头,国家日日都在危急存亡之秋,国人未尝不忙,忙学东洋,忙学西洋,忙办这样,忙办那样,结果怎样?没有把根本问题认清,瞎忙了几十年,又来了一个‘九一八’的大祸,依然是坐以待毙,束手无策。就是‘九一八’事变,到现在也已经3年了,在这3年当中,又忙了些什么?我看照样抓不着命脉。”[2]晏阳初想通过“农民运动”完成“民族再造”的历史使命。
晏阳初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一文中对乡建运动的原因作了更加凝练的概括:“乡村建设运动当然不是偶然产生的事,它的发生完全是由于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而他们的生活基础是乡村,民族的基本力量都蕴藏在这大多数人——农民——的身上,所以要谋自力更生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而自力更生的途径也必须走乡建的一条路……基于以上两个波动——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就涌生了今日乡村建设。”[3]之所以产生了“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问题,晏阳初认为是“中国近百年来因与西洋文化接触”的结果。所以,他说:“中国今日之所以有问题,可以说完全由外来势力所激起。假如中国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或者还会沉沉长睡下去。自外力闯入以后所发生的剧烈变化,使中国整个的国家日陷于不宁和纷乱的状态,而受祸最烈的莫若乡村。”[3]
晏阳初发现了中国的基本缺点即“愚”、“穷”、“弱”、“私”四种,由此提出“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理念。主张通过平民教育运动,实现救国强国的目的。他提出“社会调查”是改造社会现实的观点,并由此想建立起中国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4]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乡村建设理论”部分分析了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的问题。他细致分析了四种原因:起于乡村救济运动,起于乡村自救运动,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起于重建以新社会构造的要求。第一层具体指“由于近些年的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特别是当时农村经济的破坏。大处说,乡村破坏不外天灾与人祸。天灾即自然灾害,人祸即“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的政治性破坏、“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的经济性破坏和“由礼俗制度学术思想改革”而引起的文化性破坏。当然,三者又紧密相连。梁漱溟认识到:“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亦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这个近百年史,亦可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而且他还就中国乡村破坏进行了历史分期:前半期自清代同光年间起至欧洲大战,后半期自欧洲大战直至1930年代中期。第二层具体是指:“起于中国乡村无限制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就国内而言,乡村破坏问题完全是个政治问题。乡村自救运动,第一步工作就是要防止直接的破坏,对于土匪和杂牌军队的骚扰,必须武装自卫,即地方武装自卫。第三层具体是指:中国没有在近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来也不大可能,中国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道路。显然,梁漱溟是想从复兴农业入手。第四层是从社会组织构造角度来重建中国。[5]
冯友兰在《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一文中指出:“于是梁先生就提出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这就是他的‘村治’的办法和理论,其本质就是在乡村中建立地主武装,保护封建秩序,又企图用一套所谓教育和合作制度,麻醉农民,以对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革命。”[6]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梁漱溟当年推动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不过,从冯友兰的这段话里也可以揣摩出另外的意思,即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均试图把握中国乡村的命运。
杜赞奇(Prasenjti Duara)[7]通过对“掠夺型经纪”概念的分析,意在揭明各种现代化力量试图从乡村世界组织资源来规划中国,造成了乡村的凋敝。他说:“自20世纪之初就开始的国家权力扩张,到40年代时却使华北乡村社会改观不小——事实上,它改变了乡村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及社会联系。”[7]从杜赞奇的论述来看,国家政权的扩张和“下乡”渗透,是为了军事和民政扩大财源,从而酿成了乡村社会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的斗争不断发生。[7]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些属于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朗(Olga Lang)说:“(当时)中国农村面对的主要问题与以往相比,并不是新问题。中国农民仍然拥有很少的土地和过度的税收与租典费用。”[8]
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均曾不同程度地推行过土改运动。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把“平均地权”作为国民党提倡的民生主义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一。伍朝枢说:“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缴,以均地权。”[9]1927~1937年国民政府又出台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意欲推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但事实上,国民政府除了在大陆局部地区,如江苏搞过土地改革外,其他地方始终未曾有多少实际有效的行动。如果沿着杜赞奇的思路来想,无疑国民政府在推动国家政权建设和剿共方面为了动员力量和资源而构成了对乡村的破坏。正如费孝通所言,它总是“把绝大部分(乡村)收入都耗费于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和措施来进行(乡村)改革”。[9]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中最早研究农民土地及阶级问题的人。[10]这构成了毛泽东乡村调查及土地革命实践的灵感来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1]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2]都是从土地调查入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下,毛泽东发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中的“阶级”问题,于是在他的大半生里都比较重视土地改革。当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农村作为革命的立足点,乃因为在革命初期与国民党在城市中的斗争处于不利地位而被迫转入乡村的。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乡村来改造乡村,并从乡村组织各种力量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在乡村是一种“匪乱”。朗(Olga Lang)说:“30年代大大小难以数计的内部战争,与贫乏爆发的洪水、干旱和饥饿,以及世界性经济危机,农产品价格下跌和乡村民族工业的破产,加重了农民生活的艰难。”[8]因而基于“以农立国”的信念和对“匪乱”的焦虑,始有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实验和乡建运动。这在梁漱溟的山东邹平乡村实验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费孝通认识到,中国土地制度及资源的不足也酿成了红枪会和共产党运动。[9]当然,诚如上述所云,他对国民党造成的乡村破坏也进行了谴责。《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的研究之所以聚焦于土地问题和乡村工业问题与上述背景不可分割。因而,笔者主张: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类学的乡村研究必须放在上述背景下来理解。
二、拉得克利夫-布朗和雷蒙德·弗斯对中国乡村研究的早期助推
单就西方学术对燕京学派乡村研究的影响而言,并非仅仅停留在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和英国功能论的一般理论主张上,更重要的则来自西方人类学家对中国乡村研究的直接呼吁和推动上。其中,拉得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和雷蒙德·弗斯(W.Raymond Firth)是最重要且最直接的两位英国人类学巨匠。
在吴文藻的规划和支持下,自1935年10月起拉得克利夫-布朗用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在燕京大学开设“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研讨班。修习这两门课程的学生达百余名。其间,布朗撰写了《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13]这篇文章贯穿了他自己的功能主义理论。拉得克利夫-布朗强调:“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使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14]拉得克利夫-布朗的这番话对于推动中外学者的中国乡村研究之影响是绝对不可以低估的。
当然,也不能低估雷蒙德·弗斯的作用。雷蒙德·弗斯是马林诺夫斯基(B.Kaspar Malinowski)大弟子,也是费孝通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具体指导老师。他在1938年的《社会学界》上发表了《中国农村社会团结性研究:一个方法论的建议》一文。[15]在这篇提出“人类学的伦敦学派”(the London school of anthropology)的文章中,雷蒙德·弗斯使用了“微观社会学”概念,以此概括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研究的贡献。1944年雷蒙德·弗斯在Man这份著名的人类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再次强调“社会人类学的最有价值的贡献也许仍旧停留在微观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上”。[16]
正是由于这两位西方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大师对中国村庄的重视和呼吁,才使得中国人类学家在当时及日后格外看重通过村庄以认知中国的学术道路,他们同样对国际上的中国乡村经验研究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杜靖.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汉人村庄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11,(2).
[2]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及其实施的方法与步骤[C]//陆学艺,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汇编(原载于《民间》第一卷十一期,1934).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216-224.
[3]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C]//陆学艺,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汇编(原载于《十年来的中国》,1937).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224-233.
[4]陆学艺,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汇编[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207.
[5]梁漱溟.乡村建设·卷二“乡村建设理论”[C]//陆学艺,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汇编(原载于《乡村建设》第五卷第一、二期,1935).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242-255.
[6]冯友兰.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Z].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1391395&boardid=1&page =1&1=1#1391395,2006-12-1(原载于《梁漱溟思想批判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7][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8-61.
[8]Olga Lang.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68-69.
[9]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66,236-239.
[10]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J].前锋,1923,创刊号.
[11]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C].陆学艺,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民国卷(下).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158-178.
[12]毛泽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C].陆学艺,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民国卷(下).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184-185.
[13]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141.
[14][英]拉德克利夫-布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J].吴文藻,译.社会学界,1936,(9).
[15][英]雷蒙德·弗斯.中国农村社会团结性研究:一个方法论的建议[J].费孝通,译.社会学界,1936,(9).
[16]W.Raymond Firth.The futur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J].Man,1944,(44).
Reconsideration on the cause of Han people villages researc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 Jing
This article makes comparatively careful analyses of the domestic background of the Han people village researc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It also introduces the contribution of Radcliffe-Brown and Raymond Firth in promoting the village research in China.It is hoped that this article 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s of my article“The Village as a Concept and the Concept of Village”.
Han people village;origin of study;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C912.2
A
1673-8616(2011)05-0118-03
2011-05-15
杜靖,青岛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山东青岛,266071)。
[责任编辑:李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