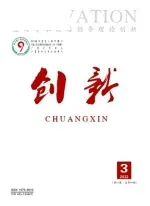从符号看人类意识的超越性
——以自我意识为视角
尹训红
从符号看人类意识的超越性
——以自我意识为视角
尹训红
借助于符号及其特性,人类意识得以发挥其超越性,在承继过去前人意识结晶的基础上,超越现实构筑一个“理想世界”来满足对自身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追求,从而使得人类意识跨越难以步入的过去与未来,把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密切连接在了一起。在此过程中,人最终实现了个体性与社会性、历史性与现实性以及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统一。
符号;自我意识;理想世界;超越性
人,人类意识,是同生共存的,符号则是促使二者在历史中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桥梁。人类意识作为一个存在领域,并不是现成存在的,而是人在其实践活动中逐步生成的。在实际的劳作中,当生存的需要促使人产生一定的意识萌芽时,处于劳作中的人便产生了使用符号的需要。而符号的产生使人从自然界中脱离出来,成为自主有理性的存在和认识、改造世界的主体,这时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出现了。人不等于意识,意识不等于符号,但意识却是人的灵魂,符号却是使人类意识凸显与发挥作用的载体。探究人类意识,必然涉及符号,涉及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发展历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透析伴随着实践活动成长起来的人及人类意识。
孔德说:“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历史。”他针对所处时代,将心灵定位为独立自在的、先天的认识载体。他在《致瓦拉的信》中指出:“所谓对心灵所做的观察,都是纯粹的幻觉。我们称为逻辑、形而上学、思想意识的所有那些东西,不是理论谬论就是毫无根据的幻想和梦想。”[1]8而由符号构成的语言以及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等文化(形式),“它们作为实践活动的内在环节和产物,虽不是意识本身,但却在形式方面为意识(在限于‘意识界’范围内的意义上,亦即在‘世界’的‘属人’性质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意识’作为物质的反映的意义上)的实现提供了基本的质料内容……意识的存在和实现,(须臾)不能离开它(们)的支撑作用。”[2]它们作为人类思想(意识)记录本,不仅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记载了人类在认识与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惶惑、探索、进步,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人类精神现象的新视角,让我们能够去探索抽象意识的诸特征及其本质。
一、人类意识的产生与符号的出现
人类意识的产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是脑与神经系统的完善,二是实践活动中实际的需求。其中,实践活动是人类意识得以产生的决定条件。
马克思从人的现实存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提出“人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3]可见,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人是一个自然的物种,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的一定阶段上,当劳动的需要促使了语言的产生,借助于语言符号的人成为真正区别于动物的存在时,人才成为人;而新生的个体,只有被作为人类意识的产物的文化所熏染,从而成为文化性的存在时,新生个体才真正成为人。原始人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起先并没有认识、改造世界的想法,也没有协同劳动以战胜自然的欲望,只是随自然而生而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生存的需要使他们产生了最初的意识,产生了最初的语言。“它们(语言)是人类情感的无意识表露,是感叹,是突迸而出的呼叫”,[1]160“是人类心灵运用清晰的发音表述思想的不断反复的著作”。[1]168劳动的特点决定了有声语言是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表达他们意识的符号。马克思说:“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因为“‘纯粹’的意识、精神是无法单独存在的。它们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4]81赫尔德指出:“那么靠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这种清晰的认识发生呢?通过人必须加以抽象的一个特征,而这个特征,作为意识的一个分子,清晰地呈现出自身。好了,让我们大声说:我们找到了!意识的这个最初的字母就是灵魂的语言。”[5]从这时起,语言这种符号就与人类的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除了有声语言之外,又有很多的符号形式(如神话、艺术、宗教、科学等文化形式)产生,与语言一起,共同执行着表达人类意识这一任务,并促使着人类意识不断向前发展,使人类意识不仅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指导实践的功能,而且使人类意识可以发挥超越性,跨越世世代代,去指导人类的实践,描述未来的图景。
二、符号的作用与符号对思想的指称性
人,因为具备理性和劳动能力,从而成为认识、改造世界的主体。而人之所以能成为有理性、能劳动的主体,无疑同人所具有的符号能力紧密相关。因为,“人只有通过符号,才能达到对具体事物的抽象,从而达到对客体的理性认识,以及对自身的理性认识,才能成为有理性的人;并且只有在理性的水平上,才能将自己作为主体和外界客体区分开来,形成人的主体意识,产生能动地顺应与变革客体的理性目的,从而自觉地建立起主观与客观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符号能力与符号行为成为人与动物、成熟的人与尚未成熟的人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无疑可以说人是符号的动物。”[6]5
借助于实践劳动的需求而产生的语言符号,不但使人们谋取生活资料的活动成为了真正的人类意义上的社会劳动,而且语言等符号所构筑的诸文化形式,还使人的社会性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为人的意识从个体性上升到社会性做好了铺垫。我们知道,动物也有社会性的行动,如蜜蜂、蚂蚁在生存中的劳动分工。而人类社会,除上面所见于动物世界的简易分工之外,还是一个思想和情感的社会。“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等就是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的组成部分和构成条件,它们是将我们在有机自然界中所看到的社会生活形式发展到一种新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手段。”[1]306
从符号学来看,符号能够指称对象,这种关系是一种人为约定的关系,也即是人们观念地把握着的一种联系。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人们有意识地把符号与对象连接起来,“从而在思维中用符号的映像去代换对象的映像,或者用对象的映像去代换符号的映像,实现两种不同映像的转化”。[6]42“联系着人的思想来看,符号所指称的对象一定是在人的思想中所把握的对象,或者说是进入到人的意识中的对象,这也就是作为思想内容的对象。所以,当符号作为对象的指称物时,实质上就是作为人们在思想中把握了这一对象的标志,因而也就是作为人们关于这一对象的思想内容的表达者。由此,从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过渡到了符号与思想的关系。”[6]42其实,“人的思想就是一种信息形态,人的思维活动就是一种信息符号加工活动”。故可以说符号是思想的表达物,是外化思想的工具,是思想(意识)的呈现载体。“符号所携带的信息,就是人的思想、认识等。”[6]44
在个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中,能使用符号,是人认识世界过程中的一个飞跃。当洱伦·凯勒从信号和手势的运用到能使用符号时,在她身上发生了决定性的一种变化,她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而达到这样一种发现,她必须能理解到:凡物都有一个名称——符号的功能并不局限于特殊的状况,而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这个原理包含了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词的用途不仅是作为机械式的信号或暗号,而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工具。
由此,语言等符号形式作为意识的“外壳”,作为“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5]81它跟随“‘内核’出现于它所在的场所,和‘内核’作为一个整体同其他因素发生关系。”[6]240它们作为“现实的意识”,一方面,它们把个人的当下的意识变成可以沟通和交流的言语行为,使人类意识得以外化为现实的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作为一种中介,使人类的实践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它们不仅能够把人的世世代代的意识活动的产物“贮存”于历史文化的“水库”之中,使人的意识得以固化与传承,而且使抽象的意识超越和突破时空的限制,在现实世界中指导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三,借助于它们,人还能够在意识世界中超越现实构筑一个“理想世界”以满足人们对自身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追求,同时又能把人对未来的猜测与预想,逐步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变为现实。这样,借助于符号及其特性,人类意识得以发挥其超越性,跨越难以步入的过去与未来,将人的过去、未来的意识,一定程度上呈现在了“现在”,从而把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密切连接在了一起。
三、人类意识(主要指自我意识)的超越性
人类意识(主要指自我意识)的超越性,不仅表现为它借助语言等符号形式,来实现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而且更主要地是体现在他们通过各种符号形式实现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超越而创造出的“理想世界”。
上文我们所讲到的人类把握世界的由符号构成的各种文化形式,如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等,不仅使人类的意识得以记载与传承,而且它们本身的存在就体现了人类意识对时空的超越和对自身的的一种连续性。人类意识是以符号及其构成的诸文化形式为外壳的。可以说人类意识正是由于借用了符号这一具体的指称物,才使它的超越性得以发挥。我们首先看一下符号感知的特点。
(一)符号感知的特点
第一,符号感知活动,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由具体映像到抽象感性。这样,就使人类的认识在具体对象、符号对象与具体感性之间架起了桥梁。具体对象、符号与符号所代表的对象的意义就连成了一个整体,这样人就不用再直接地面对实在,可以直接在抽象意义的层面上来思考。因为,“一个符号不是作为物理世界的一部分的那种现实存在,而是具有一个‘意义’”。[1]78
第二,符号感知活动,使主体比直接面对对象进行感知时具有更广的发挥空间。符号的引入,使人与动物相比,多了一个被称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动物在反应的过程中,也具有迂回能力,也能学会使用工具甚至能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发明工具,但这只是一种实践中的想象力和智慧,只有人才发明了一种新的形式: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智慧。“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与其他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更为宽广的实在之中,而且可以说,他还生活在新的实在之维中……所以,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1]68-73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不仅人的经验、知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感知者主观的能力,如想象、联想等都能进入到人的认识活动中来。这就使人的意识能够超越具体的对象、超越时空发挥作用。
符号感知的这些特点,成就了人类意识的超越性。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的想象某种东西”[4]81。它超越了“意识对象”的限制,把意识所想象的对象当作真实的“意识对象”。
(二)自我意识与其所构筑的“理想世界”
人类的意识,不仅包括把“世界”当作自己的“对象”的“对象意识”,而且还有关于自己的感觉和知觉、欲望和目的、情感和意志、思想和理性的“自我意识”。在人的生活中,这两类意识的共同存在,才完整阐释了一个人的真正生活世界。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认识、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还时时不忘对自己内心的关注和探索。“人类意识自从萌发之时起,我们就发现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显著。人的天生的好奇心慢慢开始改变了方向。我们可以在人类的一切文化形式中看到这种过程。在对宇宙的最早的神话学解释中,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难分难解的交织在一起。”[1]356
在这种“自我意识”中,人类能够“超越”自己的狭隘的、有限的存在,在自己的“意识世界”中为自己创造无限广阔和丰富的现实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即使在实践方面,他也并不是生活在一个一成不变的领域之中,所面对的世界也不是以他的直接需要和想法而呈现。“人总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觉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正如埃皮克蒂塔所说的:‘使人扰乱和惊骇的,不是物,而是人对物的意见和幻想。’”[1]36应该说,人正是立足于实践领域中自己的感受,才在自我意识中以自己的“联想”、“想象”、“思想”、“理想”“灵感”和“直觉”,创造了人的“神话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和“哲学的世界”等等,从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而这个“理想世界”正是人类意识超越当时的生活的写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作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整体的人类文化中看到。“语言、艺术、宗教、科学等是这一历程不同阶段的产物。在这所有的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1]36所以,“人的世界,是人类意识创造的五彩缤纷的世界;人的意识,是把世界创造的五彩缤纷的‘超越性’的意识。”[7]65
“神话”对“自然世界”的超越。人类意识的超越性,首先表现为人的意识所创造的“神话”对自然世界的超越。神话作为人感知世界的一种不同的方式,它以把人和世界双重幻化的方式,赋予自然万物以生命的意义从而超越了天与人、人与物的隔断,表现出人们认识、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一种理想与追求。
宗教对“世俗世界”的超越。宗教的世界,本质在于对神的信仰。当人们感到对自然界异己的力量不能掌握并因而无法依赖时,便会转向对超越自然的宗教世界的信仰和依赖。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就宗教的文化价值而言,它是人类所创造的‘意义世界’,表现了人对生命意义的寻求”。[7]203-210
艺术对“无情世界”的超越。艺术的世界,是人类意识所创造的表现人的情感深度的世界。它是对“无情世界的超越”。艺术为人类展现了一个审美的世界,一个表现人的感觉深度的世界,一个深化了人的感觉与体验的世界。在艺术的世界里,人的生活获得了美的意义与价值。[7]203-210
伦理对“个体世界”的超越。人们以伦理的方式把握世界,就形成了以某种价值观为核心,以相应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为内容的伦理文化。一个社会的伦理文化和伦理精神的扭曲,都会造成人的生活意义的扭曲、变形和失落。[7]203-210
科学对“经验世界”的超越。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它是运用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方法去探索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奥秘”,获得关于世界的规律性认识。它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概念系统的形成和确定、扩展和深化、更新和革命的过程。科学发展过程中所编织的科学概念和科学范畴之网,构成了越来越深刻的科学世界图景,也构成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愈来愈坚实的阶梯和支撑点。
(三)实践活动与“世界图景”、“理想世界”的关系
我们所构建的“世界图景”、“理想世界”,既是人对当时世界的把握,又是人对未来世界的展望与探求,包含着人们的希望与理想。人是实践性的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就是把人的目的性要求现实化,把人的头脑中所构建的关于未来的图景不断实现的过程。人类的意识引导着人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又实现着人类意识对于未来的设想和牵制着人类意识超越性的程度,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在实践活动中,人类意识的超越性与现实性得到了统一。
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把人构筑的“世界图景”、“理想世界”现实化的过程,不仅是改变生活环境的过程,使自然“人化”的过程,把“人属的世界”变成“属人的世界”的过程,而且是改变人类自身的过程,更是把“属人的世界”变成“文化世界”的过程。这样,自在的世界就变成了一个属人的世界,一个文化的世界,一个意义的世界,即人的生活世界、人的意识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是人类意识的结晶,是历史的产物。探究这个世界及其构成形式,是我们研究人类意识诸特性及其本质的新视角。
[1][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高申春.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从西方心理学历史逻辑透视社会学习理论[D].长春:吉林大学,200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4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德]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姚小平,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27.
[6]肖峰.从哲学看符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7]孙正聿.哲学修养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AnAnalysisoftheTranscendenceofHumanConsciousnessinTermsofSymbolsfromthePerspectivesof Self-awareness
YIN Xun-hong
With the aid of symbol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human consciousness can achieve transcendence.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consciousness wisdom of predecessors,people can create an“ideal world”beyond reality in order to pursue the valu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which enables human consciousness to cross over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o link together the past,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being.During this process,people finally achieve the unity betwee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ity,historicity and actuality,as well as self-awareness and social awareness.
symbol;self-awareness;ideal world;transcendence
G0
A
1673-8616(2011)05-0103-04
2011-04-09
陕西理工学院人才引进项目(SLGQD0775)的阶段性成果
尹训红,陕西理工学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教研室讲师、硕士(陕西汉中,723000)。
[实习编辑: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