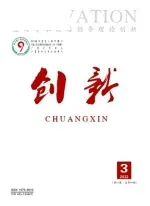论版权在数码音乐时代的发展趋势
黄虚峰
论版权在数码音乐时代的发展趋势
黄虚峰
在互联网和数码技术的联合冲击下,现代音乐产业结束了实体唱片时期而进入数码音乐时代。作为现代音乐产业的基础和保护神,版权需要调整以适应新环境。在网络环境下,应重新审视复制和表演的概念,解决好发行权中有关首次销售条款的解释的不适用问题。保护好音乐产业的创作环节——尊重音乐创作者和编辑的智力劳动。
版权;互联网;数码音乐;音乐产业
1990年代起,全球音乐产业受到互联网和数码技术的冲击。借助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数码音乐改变了人们聆听音乐的方式,也改变了音乐产业和版权的现状。数码技术的出现,使录音制品(CD、磁带、密纹唱片)在美国的销售量在2000年下降了3.7个百分点,2001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2002年下降了9.9个百分点,2003年又下降了8.7个百分点。[1]21面对数码技术的挑战,唱片公司曾用一连串的法律诉讼把以Napster为代表的盗版网络音乐打得一时喘不过气来。2000年Napster案(A&M Records V.Napster),美国的地区法院裁定:Napster文件共享公司因提供用户使用共享软件而构成侵权。这项裁定在上诉法院获得支持,不久Napster破产。2005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在米高梅公司诉Grokster(MGM Studios,Inc.v.Grokster,Ltd)案中的判决,认为:提供用于侵权设计的设计者,表现出通过清晰的表述或其他肯定性步骤鼓励侵权,对第三方造成的侵权结果负有法律责任。[2]211
但无论唱片公司怎样努力想挽回颓势,实体唱片都已成明日黄花。世界音乐产业进入数码音乐时期。现代音乐产业建立在版权基础之上,随着实体唱片业的式微,版权的作用甚至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如何让版权适应新环境的需要成为21世纪初版权面临的挑战。
一、数码技术与网络联合冲击下的音乐产业
20世纪美国音乐产业的主要呈现方式是以唱片公司为核心的涵盖唱片的创作、录制、灌制、发行和销售的一条龙产业化运作。作为音乐家和消费者两端的中介,唱片公司发挥着物化、宣传和营销三大功能。然而,在数码技术与网络的联合冲击下,唱片公司的三大功能被弱化或解除,导致唱片公司面临生存的不确定状态。
(一)数码技术与网络的联合几乎解除了唱片公司的音乐物化功能
所谓音乐的物化,就是将无形的音乐内容以看得见的物品形式呈现,比如钢琴纸卷、唱片、CD等。但是,由于音乐数码化以及互联网的普及,音乐的“物化”环节失去了意义。音乐数码文件可以脱离实物载体进行无限制的无损复制,并通过互联网以光的速度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一切都是以近乎零的成本进行,同时复制和分发操作的投资和技术门槛很低,个人电脑用户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
随着音乐的物化环节失去意义,唱片公司之于消费者和之于创作者的物化功能受到考验。之于消费者,以前,追求音质的消费者不会将唱片公司的原装产品弃之不顾,因为毕竟磁带复制也是有损音质的模拟复制,但是现在消费者可以通过数码复制得到“高保真”音质的音乐作品复制件。对于创作者,“半个世纪以来,音乐艺人进军大众市场的唯一途径就是与‘大型唱片公司’签约。现在,艺人们自己就能够制作出高质量的音乐唱片”。[1]13制作唱片最实质、最主要的成本来源是购买或租用必要录音设备的费用。1980年的时候,这些设备大约价值50000美元;今天,同样的功能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加上价值不超过1000美元的附属软硬件设备就可以实现。[1]12以前,唱片公司会承担一些音乐创作的组织功能——将曲作者、词作者、演奏者和演唱者等组织起来共同完成一首歌曲的创作,或者找到演员和摄影师完成MV的制作。现在,一些歌可以是通过网络通讯和文件传输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朋友共同完成。音乐制作环节的成本和制作组织形式的变革,使得越来越多的艺人从对唱片公司的制作依赖中独立出来。
(二)数码技术与网络的联合分散了唱片公司在音乐宣传上的作用
如何一夜之间成为闻名的音乐人在数码时代以前,通行的做法有:挤进“五大”厂牌的龙门;在最火爆的娱乐频道上镜;花钱买断广播电台的音乐专栏;飞到各地上采访、开演唱会;与大牌艺人闹绯闻。然而,上述唱片公司在艺人开发和唱片推广上的宣传手段也正在被网络时代分散。Yael Naim是苹果广告歌曲《New Soul》的演唱者,这首歌曲在短短一个月内就登上了美国告示牌(Billboard Top100)并排名第九,歌曲的推广中看不到唱片公司的影子。Yael Naim是数码音乐时代的独立音乐人。一夜成名之前,她在MySpace和last.fm上宣传自己,在iTunes音乐店里出售自己的作品,通过网络实现病毒营销,最后依靠数字音乐销售的佳绩登上热门榜单。
(三)数码技术和网络的联合削弱了唱片公司的音乐营销功能
控制营销渠道是五大唱片公司实现音乐产业垄断的关键。1970年代,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首的大型唱片公司开始建立自己的更有效率的销售体系。到了1980年代,这种新的销售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个人拥有的夫妻音像店逐渐消失,代之以受控唱片集团的音像连锁店,小型唱片公司为了销售唱片不得不与大型唱片公司洽谈签约。市场的垄断带来价格的垄断,一张唱片卖到18美元。长期以来市场容忍垄断的理由只有一个——目前没有比垄断者更好的替代品。但现在互联网让传统的实体营销环节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使音乐消费者处处感受到实惠。其一,在实体唱片商店购买的一张售价18美元的CD,如果通过互联网以数码文件形式发行,将能节省以下费用:零售商店收取的7美元、光盘生产商收取的1.50美元、发行商收取的1.50美元中的一部分、唱片公司收取的8.00美元中的一大块。其二,互联网传播方式允许向消费者提供单首曲子,而不再是通常CD专辑中的全部歌曲合集(里面通常含有消费者不感兴趣的“凑数”歌曲)。[1]14
随着传统音乐销售渠道的衰落,很多非唱片界的公司开始插足音乐生意并分散唱片公司的角色:一是电信运营商(韩国SK电讯提供的MelOn音乐业务成为韩国首要的音乐发行方式);二是终端生产商(Nokia、Motorola、iPod等都有相应的数字音乐业务);三是音乐销售渠道(Amazon不仅出售数字音乐,还通过购买艾米街网站拥有了独立音乐发行平台);四是互联网上涌现的众多独立音乐人代理平台。
综上所述,数码技术和网络的联合冲击,导致的已经不是唱片销售量下滑之类的业务问题,而是唱片公司面临被终结的时刻如何让自己华丽转身的选择问题。作为唱片时期音乐产业的核心,唱片公司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以后那些在数码文件时代中蜕变的唱片公司也许都该称“数码文件音乐公司”了。那么,什么是音乐产业的未来?Napster们的挑战揭示了答案:网络音乐和免费下载。对唱片公司来说,转向网络不难。因为它们手里掌握着网络音乐新锐们缺乏的东西——新鲜、丰富、全面的曲目库。难的是如何让终端消费者免费下载音乐又能赚钱,即如何建立数码文件时代的音乐产业新型商业模式。曾经售价99美分一首歌的网上音乐销售方式并非奏效,但不收费又如何保证正版音乐在网络上赢利,从而让盗版音乐网站自动消失呢?目前,数字音乐的经营方式包括简单付费下载、直接订购以及广告支持收费。国际唱片业协会主席约翰·肯尼迪透露,一项调查显示,有4500万的消费者愿意把广告作为免费听音乐支出,超过愿意直接为音乐付费的消费者9倍。德国源泉无线传媒集团总裁迈蒙·莱恩这样区分两者的不同:“盗版数字音乐是完全免费的,没有授权、品质保证;不过当正版的数字音乐可以用‘免费的感觉’提供给消费者,自然就有钱可赚,资金流动起来就能激活产业。”[3]看来,广告支持收费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买单者从消费者变为广告主,事实上它不免费,但对消费者来说,它能提供免费的感觉。
二、数码音乐时代的版权
版权被公众理解为娱乐产业用来控制音乐和其他具有创造力作品的工具。因此,当音乐产业陷入网络冲击下的困境时,有关版权前途的争论持续不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来自“感恩至死”乐队曾经的词作者约翰·佩里·巴娄。他的文章《点子经济》在1994年初由《连线》杂志连载。以下部分让人印象深刻:如果我们的知识产权可以无限复制,并且可以在我们不知不觉中立即免费传遍全球,我们并未丧失对它的拥有权,但我们又能如何保护它?我们又如何从自己的脑力劳动中获得收益?假如我们得不到报偿,又如何能保证持续创造并传播这种产品?既然我们对一个崭新而深刻的挑战还拿不出解决方案,而且我们又无法减缓一切无形事物的数字化进程,因而我们是在乘坐一艘即将沉没的船驶向未来。[4]21-22
巴娄的言论引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数字网络时代,版权是否已经过时?美国著名的版权法专家大卫·尼莫(David Nimmer)认为,新的传输方式和困难预示着我们熟知的传统意义上的版权的终结,或预示着版权将被商业机构所取代。[5]
美国贝尔蒙特大学(Belmont University)娱乐与音乐商业学院的版权法教授戴维德·摩沙(David J. Mose)则提出,“仅仅因为一种传媒可以用数码方式储存起来并不能说明版权法就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假如所有的法律在应用过程中一旦遇到新环境的挑战就必须废弃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会陷于混乱之中。”[2]191版权就是在接受新技术的挑战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演变的。版权法的适用性就体现在——随着新的法律规定的制定、法律范例的健全以及反盗版技术在受版权保护音乐作品上的运用而调整。同样,版权要在互联网时代继续成为音乐产业的保护神,必须做到以下两点:
(一)版权在互联网中的适用
新技术的发展对版权来说一直是一个挑战。正如美国专利商标局长布鲁斯·莱曼(Bruce Lehman)在1995年7月阿姆斯特丹会议上的发言,他认为数字技术对于版权所有人控制其作品的使用,“既不是第一个,也可能不是最后一个”挑战。[6]这反过来也印证了版权具有的适用性。让自己在网络环境下继续适用于音乐产业,版权遇到的最大问题在于解决如何应用的问题。
1.网络环境下重新审视复制和表演的概念
在音乐作品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技术以数码形式发布以前,复制和表演的概念是清楚的。但用来解释互联网上传播音乐的行为时,却遇到了麻烦。版权法认为,只要文件被传输,就构成表演行为。但是,当音乐在互联网上传输的时候,通常就自动产生了复制的行为。因为音乐要以数码文件的形式被复制到接收方的电脑的随机存取存储器(RAM)上才可播放。一次行为同时牵涉到两种权利,给版权应用带来了复杂的问题。因为版权持有人假如已经得到了表演版权税,那么,再收取复制版权税的话,在本质上版权持有人是试图在同一种行为中收取双重的费用。反之亦然。然而无论是发放复制许可权还是控制表演许可权的机构都不愿意放弃版权收入的一个潜在有利资源。
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途径:第一,就是修改版权法案有关复制和表演的定义,明确规定哪些方式的传输属于复制,哪些方式的传输属于表演。比方说,仅仅提供在线聆听的使用属于表演,由表演权控制机构去跟踪;提供试听但最终服务于下载业务(产生了永久性拷贝)的使用属于复制,由复制权控制机构去跟踪。第二,是简化网络传播许可证发放的程序,这需要许可证发放机构们的协调,关键是简化程序的同时不能由此减少版权所有者的版税收入。
2.网络环境下解决发行权中有关首次销售条款的解释的不适用问题
根据首次销售条款,假如一个人合法地获得一张包含有受版权保护作品的唱片或者复制品,他无需经过版权持有者的同意,就可以将唱片或者复制品销售或者分发给其他人。前提是:这个人不可以复制这张唱片,或者把唱片的复制品分发给其他的人。
对应网络环境下下载音乐文件的行为,首次销售条款的应用应该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人合法地第一次下载了一个音乐文件,首次销售条款就允许其把下载到硬盘上的音乐资料转送给他人。前提是:把他的电脑硬盘从电脑上拆卸下来送给朋友。或者在传输文件给朋友以后把储存在电脑硬盘或者其他储存器里的数码文件的原件删除掉。显然,对这个人来说,前提里的要求都是不现实的。此外,要构成一个发行产品的行为,就必须有把一件物体交给对方的过程。在网络上,发行产品的概念有点模糊。当一个受版权保护的音乐文件在网上被传输时,这个过程似乎已经构成了一个发行产品的过程,但与其说是发行,不如说是复制。因为在网上传输的并非是一个有形的物体,而且传输唱片的人依然还拥有唱片的原件,接收方收到的仅仅是原件的复制件而已。
(二)保护音乐产业中的创造性劳动
音乐产业中的创造性劳动包括两部分:创作者的创作和中介机构的编辑。从乐谱时期、实体唱片时期再到数码文件时期,音乐产业经历了100多年的变动。但是,有些东西没有变动,而版权保护的初衷是针对以下没有变动的部分。
1.创作者的创作
在唱片工业协会与Napster交战的日子里,有一些艺术家抛弃唱片公司,站在另一个阵营。他们的理由是:唱片公司以往的行径如同强盗,让他们心碎。摇滚艺术家考特尼·洛夫发言说:“什么是盗版?盗版就是一种偷盗艺术家作品而无意花钱购买的行为。我指的并不是像Napster这类软件。我谈的是大唱片公司的合同。”[4]180也有一些艺术家同意考特尼·洛夫对唱片公司的看法,比如美国爵士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赫比·汉考克也认为唱片业在“捍卫艺术家的权利”的幌子下偷窃艺术家作品。然而,他同时指出,“Napster网站比唱片公司更糟。”
经济收入是艺术家创作音乐的保障,在没有音乐版权保障的时代,贝多芬的经济来源于贵族资助或一次性买断自己的作品,在有版权的日子里,美国电声摇滚之父马迪·沃斯特依靠版税收入摆脱做芝加哥搬运工人的苦役专心创作。但是,失去贵族资助的晚年贝多芬穷困潦倒,而有版税收入的马迪·沃斯特晚年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给东家——切斯唱片公司做粉刷工!在版权为基础的唱片工业时期,人们看到的版权是站在唱片公司的身后而不是艺术家的身后,看来,版权在唱片时期的音乐产业里,表现的确差强人意,以致有人在质疑唱片公司的存在合理性的同时也质疑版权存在的合理性。
版权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市场方式给予著作者一定的经济补偿,激励他们继续创造和传播智力作品。哈佛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首席教授威廉·W·费舍尔在《说话算数——技术、法律以及娱乐的未来》一书中提出了最佳思路,即用政府管理下的奖励体系来代替目前的“版权+加密”的保护模式,具体阐述如下:作者创作的歌曲或电影被他人聆听或观看,作者如欲取得相应的报酬,首先应将作品向版权局注册登记。注册过程中,会给作品取一个独一无二的文件名,以便用来跟踪作品数字化版本的传播。政府可以通过向有关设备和服务征税的方式获得充足的收入,以此来补偿注册者将其作品公之于众的贡献。借助美国和欧洲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以及电视收视率服务行业的先进做法,政府机关可以对每首歌曲或每部电影的消费次数做出估计。政府机关以此作为依据,定期向注册者分配相应的税收收益份额。一旦此体系得以实施,我们就要修改版权法,废除当前对非授权复制、发行、改编和表演所作的各种限制,这样,音乐和电影就能被免费合法地获取。[1]184
2.中介机构的编辑
网络时代的特点是“人人都是创作者”。只要有一台电脑和一套数码音响设备,任何人都能制作出专业级的唱片,甚至不需要生产厂房就能电子化发行这些作品的拷贝。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词曲作家或唱片音乐家的时候,人们会比传统时代更需要中介的“过滤器”作用。在传统音乐时代,音乐出版商、唱片公司、歌手的经理人等中介机构正是这样的过滤器,他们进行的编辑、挑选、再加工等创造性劳动,使消费者能够获得现成的音乐。这部分工作在网络时代仍然具有必要性,这些中介机构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得到回报。音乐产业无论怎样发展、演变,人们对音乐的永恒需要导致对创作者的创作和中介者的编辑的永恒需要,所以只要版权保护的是音乐产业中永恒的创造性的劳动部分,那么对“永恒”的保护最终也成就自己的“永恒”。只有这样,版权才不会因互联网和音乐的数码技术而过时。
[1][美]威廉W.费舍尔.说话算数——技术、法律以及娱乐的未来[M].上海:三联书店,2008.
[2]David J,Moser.Moser on Music Copyright[M]. Boston:Thomson Course technology PTR,2006.
[3]夏琦.传统唱片市场日趋缩小数字音乐成主流维权难[EB/OL].[2011-06-25].http://www.artsbj.com/Html/observe/zhpl/wypl/yinle/4222666405.html.
[4][美]约翰·奥尔德曼.网乐轰鸣[M].中信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5]David Nimmer.The End of Copyright[J].Vanderbilt Law Review,October 1995,p.1420.
[6][美]保罗·戈斯汀.著作权之道——从谷登堡到数字点播机[M].金海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D913.4
A
1673-8616(2011)05-0074-04
2011-07-10
黄虚峰,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后(上海,201620)。
[责任编辑:文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