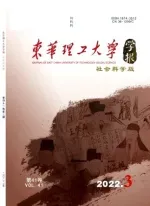论清代的《楚辞》文本传播与接受
黄建荣, 李蕊芹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江西抚州344000)
论清代的《楚辞》文本传播与接受
黄建荣, 李蕊芹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江西抚州344000)
在楚辞学史的学术背景下,对清代《楚辞》文本传播大致情况进行了简要描述。从文人接受的角度,以五家《楚辞》文本为重点考察对象,具体分析清代文人在屈原人格精神、楚辞音义主旨及楚辞艺术美学等方面的接受情况,从而体现出清代文人在楚辞接受史上的突出贡献,总结出清代文人楚辞接受在研究重点、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三方面的新特点。
楚辞;清代文人;文本传播;接受
近些年来,从传播与接受角度研究楚辞的论文虽有一些,但专门探讨清代《楚辞》文本传播与接受的还甚少,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1 清代的《楚辞》文本传播
从与原著的相关度划分文学经典的传播,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文本传播,一是改编传播。文本传播既包括某一具体版本的刊刻及在后代的流传情况,又包括后代文人对原作的注解而形成的新注本。改编传播往往因时代的不同分别有戏曲、说唱、网络、影视等多种形式。《楚辞》也不例外,自汉代以来就传唱不绝,尤其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出现过多种有关《楚辞》注释和研究的文本,这些文本一方面作为《楚辞》的重要传播方式,一方面也是文人接受《楚辞》的重要方式。大致说来,《楚辞》和与之相关文本的出现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唐,代表作有王逸的《楚辞章句》;第二阶段为宋元明,代表作有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汪瑗的《楚辞集解》等;第三阶段为清代,代表作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和戴震的《屈原赋注》。
就清代而言,《楚辞》的注释和研究达到高峰期,故与其相关的文本也是历代数量最多的。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总目》共列出六十六家的七十三部著述,洪湛侯主编的《楚辞要籍解题》作重点介绍的有二十七家,李中华、朱炳祥的《楚辞学史》重点介绍的有十七家,潘啸龙、毛庆主编的《楚辞学文库·楚辞著作提要》附录的《楚辞书目》列出七十三家,其中撰写出提要的为四十四家。这诸多的注本,实际上就是一系列与《楚辞》相关的文本,它们对整个清代的《楚辞》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大致说来,清代的《楚辞》有关文本又可分为明末清初、清初至康熙、清中叶、道光至清末四个阶段。
明末清初时期,由于民族矛盾尖锐,抗清之斗争此起彼伏,学者们大都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变迁而不愿出仕清王朝,因而《楚辞》文本的共同特征就是紧跟时代,将明朝的沦亡之痛和个人的身世感慨融于其中,重要文本有李陈玉的《楚辞笺注》、钱澄之的《屈诂》等,代表作则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清初至康熙年间,随着清政权的巩固和对程朱理学的大力倡导,一些正统的“理学名臣”和“醇儒”也涉足《楚辞》的注释和研究,而沿袭传统路数为主治《楚辞》的学者也有不少,这就使得当时的《楚辞》文本呈现出两种类型并行的情况:一是以阐述性理道德观念、提倡清白廉洁节操为宗旨,如李光地的《离骚经九歌解义》和方苞的《离骚正义》;一是其他学者的《楚辞》注本,主要有毛奇龄的《天问补注》、王萌的《楚辞评注》、林云铭的《楚辞灯》、高秋月和曹同春的《楚辞约注》、徐焕龙的《屈辞洗髓》、王邦采的《离骚汇订》和《屈子杂文笺略》等,其中林云铭的《楚辞灯》在康熙年间较有影响。
清中叶的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天下较为稳定,由于统治者对文人学士采取“恩威并重”的双重措施,使得清初学者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被削弱,学者们多埋头于故纸堆中,重考据训诂之风成为学术主流,其突出代表是乾嘉学派。同时,本时期也仍有一些学者承袭明末以来学风,偏重以文学的角度来分析集部作家和作品、阐释作品大义。与此相应的是,这一时期的《楚辞》注释和研究文本也就出现了两大类别:一种是治学严谨、学风朴实的注家和以传统训诂为主体的文本,如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胡文英的《屈骚指掌》、朱骏声的《离骚赋补注》、丁晏的《天问笺》等,其中蒋骥和戴震两人的文本,历来被认为是乾嘉时期的代表作;一种是承袭明末以来较重视别立新说学风的注家和以文学分析为主体的文本,如吴世尚的《楚辞疏》、屈复的《楚辞新注》、奚禄诒的《楚辞详解》、刘梦鹏的《屈子章句》、陈远新的《屈子说志》、陈本礼的《屈辞精义》、龚景瀚的《离骚笺》等等。
道光至清末,鸦片战争爆发,时局激烈动荡,传统学术思想受到冲击,乾嘉学派开始走向衰落;学者思维活跃,追求思辨,求新求异,讲究微言大义的今文(公羊)学派兴起;与此同时,乾嘉学派虽走向衰落,但仍有一定的学术影响。这两种情况也反映在《楚辞》的注释和研究文本中:一方面出现以疑古求异为主的《楚辞》注本,典型的如王闿运的《楚辞释》和廖平的《楚辞讲义》;另一方面是仍存在重考据而不尚空谈的《楚辞》注本,典型的如俞樾的《读楚辞》、《楚辞人名考》和马其昶的《屈赋微》。
据上所述,可知清代与《楚辞》相关的注释和研究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学术风气的影响,同时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这无疑使得清代的《楚辞》的文本传播更为广泛。
2 屈原人格精神的完善与提升
屈原人格精神包括多个方面,如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浪漫气质等等,但这种人格精神的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核心,一种审美文化的代表,却离不开历代文人的反复审视,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清代文人对其进行完善与提升也功不可没。
对屈原人格精神的挖掘自汉代发端。从贾谊作《吊屈原赋》到刘安作《离骚传》,从司马迁为屈原立传到王逸作《楚辞章句》,代表汉代文人接受楚辞及屈原的三种方式。其内容大致分为两端,一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做出的评价,一是从文学艺术角度做出的评价。文学角度的评价即班固所说的“妙才”,正是对屈原诗人气质的赞赏,其才情很快便受到讲求个性的魏晋文人追捧仿效。这是从超乎功利的审美角度对屈原独特的个性和精神风范进行的评判,自此以后,屈原便成为后代富有浪漫气质文人的理想典范。审美评判之外则是伦理道德评判,由于文人自身遭遇不同,关注的视角不同,结论也是褒贬不一。如贾生流放长沙作《吊屈原赋》,司马迁受腐刑为屈原作传:“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1934在对屈原的表彰与同情中寄寓了对自身不公正遭遇的愤怒。而班固则认为:“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离骚序》)。这种批判的声音在后代虽然不绝如缕,如颜之推《颜氏家训》说:“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徘优……”[2]237将屈原归入“轻薄”一类。北魏刘献之的批判则更为激烈:“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3]1448!但随着历史的进程,屈原高洁的人格精神逐渐成为文人接受的主流意见。
屈原独立不迁的高洁品质背后往往是忠而见谗的不幸遭遇,因此常常引起后代文人无限的同情感慨,如上所述之贾谊、司马迁等。时至明末清初,这种时命之慨又与家国之痛合为一体,显得更为深沉。如明末清初李陈玉,在其《楚辞笺注·自序》里谈及作此书的原因时明确说到:“自古聪明圣智之士,不见之功业,必见之文章……向令屈子遭时遇主,则其文章全发舒于丝纶谋议之地,后世乌从而知之,惟其有才而无命,有学而无时也。是以长留后世之悲歌,而亦无所见其不幸焉。呜呼,使余而亦为训诂之文者,岂非屈子时命之累,更数千年尚相波及也哉!”[4]3显然是借申述屈子之意来寄寓自己的家国之痛和终生未能一展抱负的感慨。李氏之门人所作之序,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抱负、遭遇,以及与屈子思想和情感的相通之处。如钱继章《后序》云:“伤哉,先生之志乎!先生家藏万卷,胸具五岳,拭其廉锷,可以大用于世……迨懋翁闯逆之难,先生北望陵阙,流涕泛澜,屈平之《涉江》而《哀郢》也。既而遯迹空山,寒林吊影,乱峰几簇,哀猿四号,抱膝拥书,灯昏漏断,屈平之《抽思》而《惜诵》也。先生之志,非犹屈平之志乎?……先生壮年筮仕,逮老而未获一展,终身岩穴,穷愁著书,其遇虽不同,而似有同者,宜其精神注射旷百世而相感者哉!”[4]5又魏学渠《序》曰:“先生慷慨弃家入山,往来楚、粤间,行吟泽畔,憔悴躑躅,犹屈子之志也。……有《离骚》笺注数卷,其词非前人所能道,然而涉忧患,寓哀感,犹屈子之志也。……梓人亦曰:先生之志,屈子之志也。其所为笺注者,恻愴悲思,结撰变化,犹夫《离骚》之辞,托于美人香草、《山鬼》、《渔父》,缥缈怳忽,而情深以正也。”[4]6再如钱澄之《屈诂·自序》所云:“屈子忠于君,以谗见疏,忧君念国,发而为词,反复缠绵,不能自胜。至于沉湘以死,此其性情深至,岂直与凡伯、家父同日语哉!”[5]3借表彰屈子之气节来抒发明亡后的个人忧愤之感。
王夫之更是明确将屈原忠君爱国精神提升到一个民族的亡天下之痛。在此之前,文人更多强调屈原忠君的一面,如王逸称屈原是“执履忠贞”的“俊彦之英”,如《哀郢》是“此章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思见君而不得”;《惜诵》是“此章言己以忠信事君,可质于神明”;《思美人》是“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达”等,反复强调“忠君”这一核心精神。后代文人也有异议,如汪瑗《楚辞集解》认为屈原实有离开楚国之意,屈原非圣人,不会自沉于水,痛斥司马迁等谓屈原自沉之说为诬词等。但更多是因袭“忠君”之说。屈原爱国精神的提出较晚,虽然贾谊、司马迁对屈原眷恋楚国之情已略有言及,但真正最早将屈原的“忠君”与“爱国”联系起来的学者是洪兴祖,洪兴祖所处的北南宋之交的时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宋王朝岌岌可危,他本人也因冒犯秦桧而遭贬职,真可谓国家危亡、个人怨愤交织于心,于是借屈原之事抒己之怀,他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叙》中把屈原投江自沉的原因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二是“去则国而从亡”,不忍离去。前者为忠君,后者为爱国,因为具有忠君爱国的精神品质,所以“屈原虽死,犹不死也”。尽管洪兴祖并没有直接标明屈原的“爱国”精神,但他对屈原的“恋乡”情结予以突出和扩张,在屈原接受史上第一次将其提升到恋“国”的高度来认识,并赋予屈子“自沉”以浓重的“殉宗国”色彩,从“乡”到“国”,屈原人格中的爱国层面初具雏形[6]。自此,以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屈原人格日益深入人心,并在外患迭起的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宣传和张扬,渐次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如清初王夫之进一步强调屈原的“忠”是忠于国家,如《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以下二十余句,集中表现屈原的政治理想。王夫之云:“春秋代序,喻国之盛则有衰。草木零落,喻楚承积强之后。……以上言之所必谏之故,以国势之将危也。以上自述其违众忧国以强谏之情。”[7]215“忠”在为国的意思十分明显,这就从爱国的高度肯定了屈原的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夫之将屈原的爱国之情已上升到民族情感的高度,不再是仅仅对一片故土的热恋,而是对一个具体共同政治伦理基础的祖国之爱。王夫之说自己与屈原“时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注屈以寄托他的民族感情。如《楚辞通释》中说:“原之沉湘,虽在顷襄之世、迁窜之后,而知几自审,当怀王之时,矢志已夙密,于此见之。君子之进退生死,因时以决,若其要终自靖,则非一朝一夕之树立,唯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7]219再一次强化了屈原的爱国精神,完成对屈原人格精神的提升与完善。而这种认识在屈原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的,其原因如学者所说,“先秦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并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而也就不存在‘爱国’的观念和精神,因为在‘天下共主’(周天子)依然有着巨大影响的春秋战国,在‘楚材晋用’现象极为普遍的社会背景中,确实缺乏产生‘爱国’精神的文化土壤。”[6]司马迁在为屈原作传时也提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1]1935正是这一情况的反映。与此同时,王氏还把屈原的爱国精神与忧民之情联系起来。《哀郢序》云:“《哀郢》,哀故都之弃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离散,顷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原之被谗,盖以不欲迁都而见憎益甚,然且不自哀,而为楚之社稷人民哀,怨悱而不伤,忠臣之极致也。”[7]313在此,王氏揭示了屈原爱国与忧民的一致性,热情歌颂了屈原忠于祖国,关怀人民,而不斤斤“自哀”的伟大精神。
因此,从对屈原品行的褒贬不一到一致赞扬,从伦理道德评判到审美气质的仿效,从对屈原忠君精神的强调到对屈原爱国精神的高扬,可见屈原人格精神的内涵伴随着《离骚》的传播,是在历代文人的接受过程中逐渐形成、确立的。尤其到清初王夫之,将屈原的爱国情怀上升到民族的高度,并与忧民之情相联系,使屈原的人格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强化。
3 《楚辞》音义主旨的发掘与辩驳
先秦文学因年代的久远,语言的变迁,传播中的讹误,导致人们的阅读障碍,再加上《楚辞》背后独特的楚地文化,更使后人在阅读上难以尽其旨义。诚如闻一多在《楚辞补注》中所说:“较古的文学作品难读,全因为历史文化的久远与语言文字的变化;对《楚辞》这类上古文学进行注释,不能不进行文化的梳理与澄清,不能不运用考据和训诂的方法。”[8]1因此,历代文人对《楚辞》进行了详尽的、多说并存的注释、训诂、考据与辨析。据现有材料,刘安最早为《离骚》作注,可惜所存字数寥寥无几。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此后《楚辞》注本数不胜数,算到戴震《屈原赋注》大约有九十来部。从研究方法或关注对象的不同来划分,大致可分两大类,一是以王逸、洪兴祖为代表的注家,重视语言文字、名物训诂,二是以林云铭、蒋骥为代表的学者,重视文学价值,着重对作品段落、文义、题旨及意境、语言与艺术技巧方面分析。而戴震《屈原赋注》则一方面重视语言文字、名实考证,另一方面也注意作品内容的探讨。因此,本小节以戴震《屈原赋注》为《楚辞》注本的一个归结来重点讨论,兼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分析清代文人接受《楚辞》的特点及成就。
凭着深厚的朴学功力,戴震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字义、名物和典章制度的考释上,他能运用在当时先进有效的训诂方法,又能利用渊博的自然科学知识,故释义多平允得当。其训诂方法,戴震的《屈原赋注》一文概括为:因声求义、方言学、内证法、征引古人[9]。再加上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云:“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以辨物正名为基,以同条共贯为纬。”[10]748,因此《屈原赋注》对前代注释拨正之处不胜枚举。如《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屈原赋注》初稿云:“王注指禹汤文,朱子又疑为三皇或少昊、撷项、高辛。余以下前王证之,屈子所言当先及本国,其但一云三后者,犹周家言三后在天即指太王、王季、文王。在楚言楚,其熊绎、若敖、吩冒三君乎?”[11]537又《赋注》说:“三后,谓楚之先君贤而昭著者,故径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12]614否定了前人旧说。又如《离骚》:“岂予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王逸注:“绩,功也,言我欲谏争者,非难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戴注:“车覆曰败绩,《礼记·檀弓》篇‘马惊败绩’,《春秋传》‘败绩压覆是惧’是其证。”闻一多、郭在贻、胡念贻等皆论证戴说为是。姜亮夫先生也曾指出:“戴震是语言学家,他的注在语言文字方面有许多新发现,超过了洪兴祖的《补注》。”[13]6戴震尤其善于借用自然科学知识去注释,在《楚辞》注释史上是一个创举,主要表现在对《天问》的注释中。如释月之圆缺:“月之行,下于日,其浑圆之体,常以半圆向日而有光。人自地视之,于望得见其向日之半,故光盛满。晦朔则光全在上而下暗,余皆侧见而阙。”[12]695其他如释地球状、寒暑变化等等,也多能给予科学的解释。因此李开先生指出,“有的注释使人感到,作者简直是在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写‘天对’”[14]185。虽然在方法上极为创新,但《天问》的有关天文、地理内容的注释较为详细,而有关古史、人事内容则注释极为简略,此为其不足之处。
《屈原赋注》不仅训释了文字章句,而且对文篇旨义也有探求,因而使那些偏重故实而流于繁琐考据、局限文字训诂而忽略内容阐发的著作相形见绌。如“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旧注释“攘诟”,或谓“除去耻辱,诛谗佞之人”,或谓“遭遇耻辱,以理解遣,若却之而不受于怀”,或谓“诟辱之加,取为己有”,众说纷纭。戴震则自创一解,认为“攘,读为让”,“言宁受一时之尤诟。”依此,“抑志”义同“屈心”,“攘诟”义同“忍尤”,既合句意,又契文例。对于作品主旨,戴震也往往以简明的题解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天问》,王逸注为“问天”,注家多默契王说。戴震认为:“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而曲学异端往往鹜为宏大不经之语,及夫好诡异而善野言以凿空为道古,设难诘之。遇事称文,不以类次,聊舒愤懑也。”[12]649此见独具慧眼。其它如“昭诚敬作《东皇太一》,怀幽思作《云中君》”,“致怨慕作《湘君》、《湘夫人》”,“正于天作《大司命》、《少司命》”等,都为前人所未道,颇有参考价值。当然,因受儒学影响较多,戴震在音义训诂、名物考释和文义主旨阐释上也有偏失和不足,甚至到牵强附会的程度。
另外,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也值得重视。蒋氏自序中称自己“生平诗古文词时有论撰,经史子集之书评注者亦不少,率以束于业举,牵于疾病,未获成编,独于离骚,功力颇深”[15]5(《后序》)。尤其是考订《楚辞》地理,与屈子两朝迁谪行踪,绘成地图五幅:即《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另外对屈原作品创作时地的考索,亦具说服力,也最得四库馆臣们垂青。并单设《说韵》,研讨《楚辞》的声韵,征引详博。在作品义理方面,也多新见,如对《离骚》两次神游,究竟有何不同,前人很少注意,蒋氏先在动作上提出三点:前次向重华陈辞,然后率然上征;后次则是择定吉日,有充分准备,此为一。单前次先驱奔属,行色匆匆;后次则鸣銮齐轪,从容不迫,此为二。前次东西上下,随去随回;后次则婉转而行,穷征极游,此为三。接着在心理上提出两点:前次仅是率意观览,故出发时心情甚为轻松。后次是想委身人君,故所持态度比较慎重。此为一。前次是未知有合而上下求合,故心情极为迫切。后次则确信期必有合而前往遇合,故心情又较安适。此为二[15]36-37。这种分析,探幽抉微,耐人寻味。
戴震、蒋骥二人的《楚辞》研究成果既有文章字义、名物和典章制度的考释,又有作品义理的阐释,从研究的宽度和深度来看可谓一个新特点,在具体研究中对前人也多纠正。
4 《楚辞》艺术美学的审视
汉代文人对《楚辞》的关注主要着眼于其思想内涵,对于《楚辞》的艺术特质,汉人也偶有论及。如班固《离骚序》称其“弘博丽雅”;王逸称赞《楚辞》“华藻”、“金相玉质,百世无匹”(《<楚辞>章句·离骚后叙》)。而随着历史的变革,《楚辞》所特有的文学特质逐渐受到文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清代文人对《楚辞》的艺术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最先从文学角度研究《楚辞》的是魏晋南北朝文人,此时期的作家,正如罗宗强所言,已经“从定儒学于一尊时的那个理性的心灵世界,走到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情世界中来了”[16]361。这样的时代风气,导致了人们接受心理和审美意识的深刻变化。他们不再特别关注《楚辞》的讽谏教化的社会性之“义”,而更看重《楚辞》所独有的美学气质,如认为《楚辞》基本艺术特征是“华美艳丽”。曹丕、皇甫谧认为包括《楚辞》在内的辞赋,具有“丽”、“美”的特征;裴子野《雕虫论》谓“悱侧芬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和其音”;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17]47将《楚辞》的总体风格归结为“惊采绝艳”,并从“宗经”的卫道立场,批评“楚艳汉侈,流弊不还”[17]21。尽管褒贬不同,但在将“华美艳丽”作为《楚辞》的艺术特征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对《楚辞》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的认识上,刘勰却显保守,如称屈赋曰:“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17]48视屈赋的上天入地之说为怪异之谈。理学家朱熹则以理学家的眼光来审视屈原辞赋,谓其类于郑卫之风。戴震《屈原赋注》曰:“余读屈子书,久乃得其梗概……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说《楚辞》者,既碎义逃难,未能考识精核,且弥失其所以著书之指。今取屈子书注之,触事广类,俾与遗经雅记合致同趣,然后赡涉之士,讽诵乎章句,可明其学,睹其心,不受后人皮傅,用相眩疑。书稿既就,名曰《屈原赋》,从《汉志》也。”[12]611尽管学者多从“以骚配经”的角度来解说戴震的儒家思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戴震正是能够正视屈赋的浪漫手法,才能够透过屈赋中的怪异之谈,认为其心、其学、其言皆“至纯”,将艺术手法和儒家大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文人对《楚辞》艺术接受的终结之谈。而蒋骥更是突破传统儒家经学影响下的文艺思想,有意识、有目的地去探寻《楚辞》在艺术表现上的“绝奇处”。如他认为“《楚辞》章法绝奇”,“纯用客意飞舞腾挪,写来如火如锦,使人目迷心眩,杳不知盯畦所在”,并称赞这种艺术特色是“千古未有之格”,叹惋它是说骚者“千年未揭之秘”[15]58。
再如对作品结构的划分,王夫之分析作品内容时,遵循“以意为主”的原则。他在《楚辞通释·序例》中说:“自《周易·彖》以韵制言,雅颂风胥待以成响。然韵因于抗坠,而意有其屈伸。交错成章,相为连缀。意已尽而韵引之以有余,韵且变而意延之未艾。此古今艺苑妙合之枢机也。因韵转而割为局段,则意之盩戾者多矣。今此分节立释,一唯其意之起止。而余韵于下,以引读者不倦之情。若吟讽欲其成音,则自随韵为于喁,不待学也。韵意不容双转,为词赋诗歌万不可逆之理。”[7]209因此,他在分析结构时,完全依据文意的起止来分段,而不把文中的转韵视为一段意思的结束。蒋骥在分析结构时,则是通过对文章整体的细察,勾连全文的脉络。在分析《离骚》时,他认为这篇作品“以好修为纲领,以彭咸为结穴”[17]。自篇首至“众芳芜秽”一段,是诗人叙自己因好修而获罪;自“众皆竞进”至“前圣所厚”,是叙获罪以后而不改其修,其中“依彭咸”一句是全段诗的主轴,大部是以死自誓,然而叙写的语言则各有次第。“众皆竞进”以下,是写诗人初获罪时的心情和态度,因坚持好修不改,故曰“颇领”;“长太息”以下,是写获罪中期的心情和态度,其中以“多艰”为目,故曰“九死”;“怨灵修”以下,是写他获罪后期的心情和态度,其中以“终不察”为目,故曰“溢死流亡”。自“悔相道”以下,又觉得徒死无益,便转生一念,想求君于四方,开下半篇之局,然而好修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戴震以“昔三后之纯粹兮”以下,皆言导夫先路之事,故以信谗齌怒以上为一节。“予固知蹇蹇之为患兮”以下,皆明己素志之事,与长太息以下,言己不随流俗之意不同。故从“愿依彭咸之遗则”分节,然此节重在怨君不明,使谗言得行,已志终湮,合之为一,文意较完。这是着眼于作者情感流露和事情发展线索所作的结构划分,受到学者的好评。刘永济《〈离骚〉节旨诸家异同表》一文,汇总清代七家对《离骚》组织结构的分析,对比参验考订,从文学欣赏及诗篇的内在理路方面评论诸家论骚之意,认为:“屈子答意,戴说得之。敷衽陈辞以下,当是屈子回忆被谗以后,再三求悟君心之事。言中必有物,特史文不详耳。”[18]42
综上所述,清代文人对楚辞的接受表现出新的特点:(1)在研究重点上从汉代对屈原人格精神的推崇转向楚辞的艺术研究尤其是结构研究;(2)在研究方法上从前代的训诂考据转向训诂考据与义理阐释并重;(3)在研究态度上从成一家之言到多说并存兼容并收。这些接受内容及特点的形成与文人自身的经历有关,也与历史的进程有关,如清初王夫之的民族思想促使他高扬屈原的爱国精神。也与学术思潮有关,如清代朴学对戴震、蒋骥楚辞训诂考据研究的影响。还与学术研究的规律有关,如正是在历代楚辞学的基础上,清代文人才能推陈出新,将楚辞艺术研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1]司马迁.史记·贾生屈原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文章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房玄龄,等.晋书·华谭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李陈玉.楚辞笺注·自序[M].康熙十一年魏学渠刻本.
[5]钱澄之.庄屈合诂[M].殷呈祥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98.
[6]郭建勋.从“恋乡”到“爱国”[N].光明日报,2004-11-24(02).
[7]王夫之.船山全书·楚辞通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6.
[8]闻一多.楚辞补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2.
[9]郭全芝.戴震的屈原赋注[J].成都:江淮论坛,2001(3).
[10]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1]戴震.屈原赋注初稿[M].合肥:黄山书社,1994.
[12]戴震.屈原赋注[M].合肥:黄山书社,1994.
[13]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
[14]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
[15]蒋骥.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16]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17]刘勰著.文心雕龙·辨骚[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8]刘永济.屈赋通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Research about Chuci Text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HUANG Jian-rong,LI Rui-qin
(College of Chinese Law and Arts,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Fuzhou 344000,China)
Firstly,in Chuci academic background,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huci text briefly.Secondly,from the angle of literary acceptance,this article takes five Chuci texts as the priority research objects to analyze concretely,the Qing dynasty Literati’s acceptance of Quyuan’s personality,Chuci terms and art aesthetics,and sums up the Qing dynasty Literati’s con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ir research focus,methods and attitude in Chuci acceptance.
Chuci;the Qing dynasty Literati;dissemination of the text;acceptance
I206
A
1674-3512(2011)02-0121-06
2011-02-28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楚辞》的古代传播研究”(wx0812)研究成果之一。
黄建荣(1954—),男,江西临川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楚辞学、训诂学、民俗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