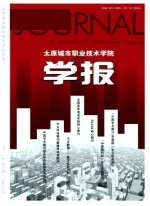分权与制衡
——英语国家代表性权力运行特征分析
钱 牧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0)
分权与制衡
——英语国家代表性权力运行特征分析
钱 牧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0)
英美两国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英语国家,它们在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起分权与制衡型体制的国家。由于两国在政治、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方面的特征,它们的分权制衡体制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试图通过作比较的途径,来分析其分权制衡体制的利弊,以期为我国的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英国;美国;分权;制衡
众所周知,英语是当今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初步统计,世界上说英语的国家大概有170多个。而在这些国家中,英国与美国又是最典型的代表。英国曾经在将尽三个世纪中扮演着霸主的角色(17、18和19世纪),而美国则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家权力运作体系也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绝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家权力体系也是以英国或美国的模式为蓝本建立起来的,以英国体制为基础的主要国家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印度等;而以美国体制为基础的英语国家有:巴基斯坦、南非和众多东南亚地区国家。而此二国的国家权力运作又是以分权与制衡为其典型性特征。
一、分权与制衡的理论基础
英国的分权与制衡学说以洛克为代表,他开创了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之先河,他在总结了西方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之上,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分权与制衡的学说。美国的分权与制衡学说以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为代表,他们在总结洛克的学说与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国家权力三权分立理论。
(一)洛克的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洛克认为,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对外权,同时洛克认为在这三种权利中,立法权居于核心地位,它制约着行政权与对外权。就此而言,这并非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因为在这种权力架构中,立法权居于首位,而行政权居于从属地位,司法权附属于行政权,它们都不能凌驾于立法权之上。其具体特征如下:
1.立法权居于首要地位,它产生行政权,但立法权的行使也是受一定限制的。首先,立法权行使的目的必须基于公共利益;其次,立法权的行使并不意味着立法者的任意与专断,而应依法行使。
2.行政权是执行立法机关所通过法律之权力,由国王行使,立法权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性,其权力并非经常性行使,而如果把行政与立法权合并由同一主体行使的话,则为该权利主体的任意与专断创造了条件。因此,此二者必须分立。
3.对外权并非一种独立意义上的权能,它与行政权几乎是结合在一起的,可以也往往由同一主体行使,因为,对外权包括联盟与联合,战争与和平,以及与国外一切人士或社会为一切事物之权力,是相对于行政权管理国内事务而言的。
4.司法权未出现在这一权力架构中。洛克的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并未提及司法权,究其原因,除了笔者的思想认识因素以外,还与当时英国的政治、历史状况有关。在当时,司法机关的地位尚不明确,较之立法与行政机关而言,尚不具备独立的权能。
洛克所设计的政体模式是君主立宪制,其基本架构是人民权利基础上的两个权力层级,即立法权与行政权(含对外权)。洛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为以后的相关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其以人民主权为基础倡导的议会至上原则,较之封建专制统治观念而言,是巨大的进步。洛克的现实主义态度使得他的理论不再停留在理论的抽象层面,从而赋予了自由主义以坚实的基础。反过来,这些制度的有效运行也深化了作为道德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理念特征。当然,洛克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所提出的这一理论也必然带有局限性,一方面,该理论并不完整,不构成完全意义上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体系;另一方面,他主张行政权行使主体是国王,也体现出向封建王权妥协的一面。
(二)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权力监督与制衡理论
杰斐逊毕生以追求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为其梦想:
首先,他认为,为防止专制体制中暴政的出现,国家权力需交由不同的主体行使,彼此之间保持一种制衡关系。
其次,立法、行政与司法权三者地位平等,若任何一种权力获得高于其他两种权力的地位,暴政便有可能产生。在强调权力分立的同时,杰斐逊还特别强调对于行政权制约的必要性,因为行政权覆盖面广,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也更为紧密,也最容易被滥用并对公民权利造成损害。为此,他提出了限制总统任期的制度,即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再次,杰斐逊还主张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分权,从而与前述构成了他独特的双重分权思想。他认为,联邦与州及地方之间,应有各自的权力范围,并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行使相应权力,相互之间不得侵犯与干预。杰斐逊反对把大权集中于联邦政府的做法,认为这样会造成其权力的膨胀。杰斐逊对联邦与州的权力的大致划分是:联邦行使国防、外交及协调州际关系的权力,州掌控公民权、法务等权力,州内的具体事务由州政府管理。
汉密尔顿是美国建国初期著名的保守派政治思想家,他所提出的联邦制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并成为美国宪政体制建立的基础,其具体特征如下:
1.为防止出现统治阶级的专制与暴政,国家权力(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应交由不同的主体行使,彼此之间保持牵制与制衡。为此他提出“只要各个权力部门在主要方面保持分离,就并不排除为了特定的目的进行局部的混合。此种局部的混合,在某些情况下,不但并非不当,而且对于各个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还是必要的。”
2.立法权由国会行使,国会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基于此,汉密尔顿认为对于立法权的制约是三权分立的重点,一方面,人民容易受不良人士以及野心家的蛊惑,另一方面,立法权是其他权力行使的基础与依据,因此必须防止其走向恶性膨胀。为此,他提出了内外两方面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国会内部分为参众两院,彼此之间保持牵制,其中参议院由上层精英人士组成,以制约由普通大众组成的众议院;另一方面,赋予总统对国会立法的否决权。汉密尔顿指出:“这是行政部门对立法机关的一种自卫权,是行政部门的挡箭牌,而且也是使立法部门更加完善起来的控制栓。”行政权由总统行使。汉密尔顿说:“无论我们可能如何坚持行政部门应该无条件顺从人民的意向,我们却不应该主张他同样迎合立法机构中的情绪。”因此,与杰斐逊主张限制行政权不同汉密尔顿主张扩大行政权以牵制立法权。
3.司法权由法院行使,由于一些重要事项的决定权集中于立法与行政权,相对而言,司法权相对较弱,因此,汉密尔顿尤为注重保障司法权。为此,宪法赋予其违宪审查权及宪法解释权,它有权裁定国会的立法及总统的行政行为违宪,并使之失效。同时,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以加强对司法权的保障。
杰斐逊的权力分立与制衡理论既包含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的横向分权理论,还包括联邦与州分权的纵向分权理论,从而构成一套双重分权制衡理论。这是其显著特点。这也成为美国联邦宪法建立国家政权机关的依据。这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代议民主制资产阶级共和国,也为世界人民建立民主共和国做出了贡献。
汉密尔顿的政治理念对美国政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设计的代议民主共和制下的政治体制奠定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基础。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和三权分立的原则在日后的政治体制发展中不断得到贯彻和完善,成为美国联邦政府体制的基础。
二、分权与制衡的具体政治实践
分权与制衡理论是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后,他们也依据这种理论设计了国家的宪政体制。在当今世界,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集权型体制的国家已为数不多。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分权型体制,这一体制也是与权力监督与制约的理念相适应的。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一)三权分立式的分权体制
这种分权体制以美国为代表,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分别由国会、总统与法院行使。三者之间保持彼此牵制,互不隶属。其具体关系简述如下:
1.国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关系
国会通过的法案,经总统签署以后,成为正式法律,总统必须执行。总统亦可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对于总统的否决,国会要么重新修改,以使得总统签署通过;要么以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多数通过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的否决一旦被推翻,该法案自动生效成为法律而无需总统签署。总统无权解散国会,国会亦无权罢免总统,但可依法定程序弹劾总统。
2.国会与法院之间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关系
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有权依法定程序裁定国会所制定通过之法律违宪,从而使之失效。同时,根据美国联邦宪法,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由总统提名,然后交参议院通过,参议院有权否决总统提名。
3.总统与法院之间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关系
总统有权提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之人选,而联邦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亦覆盖至总统权力之行使,它有权裁定总统之行政行为违宪。
(二)议会主权式的分权体制(也称“熔权型”分权制)
这种分权体制以英国为代表,在这种体制中,议会居于最高权力机关地位,其不仅行使立法权,政府亦由在议会大选中取得多数席位的政党负责组成,该政党之首脑自动成为政府首脑。严格说来。此种分权体制并非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分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中,行政权派生于立法权,并不构成两种独立的权力层级。其具体关系简述如下:
1.议会对政府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关系
议会行使立法权,政府必须执行议会所制定通过之法律。同时,议会可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若出现这种情况,政府首脑及其领导之政府要么总辞职,要么由政府首脑呈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大选。
2.政府对议会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关系
在此种分权体制中,政府虽派生于议会,但由于政府所在之政党在议会中占据了多数甚至绝对多数席位,同时,政府首脑身兼政党之领袖,在该党内有着崇高的威望,深厚的资历,因此,政府所提出的法案在议会中不被通过的几率极小,再加上由政府全面管理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领域,这些庞大的资源与技术优势使得国家的大多数立法案都是由政府向议会提出,真正由议会自行订立的法案是很少的,这也更强化了政府对议会的制约。另外,政府首脑可随时呈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这也是政府牵制议会的一种手段。
(三)西方主要国家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的评价
1.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进步性
(1)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确立破除了封建君主集权专制制度。在封建国家,君主个人集立法、行政与司法大权于一身。朕即法律,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是法律,不存在专门性的立法机构;朕即国家,君主掌握执行法律的权力,由其自己行使或由其指派的人行使;朕即司法,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掌控着对其他人生杀予夺的大权。对于上述权力,无论是国家权力之间还是国家权力外部都不存在任何监督与制约的因素,概而言之就是朕即天下。这种体制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资本主义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的确立,从内部而言,存在国家权力之间的牵制与制衡,就外部而言,存在公民以各种途径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如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具有历史进步性。
(2)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建立有效地遏制了国家权力的滥用。权力的运行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不当行使会带来极大的破坏性。而资本主义国家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全方位的,不仅存在于各个国家权力之间,而且深入到了国家机关内部,比如就美国国会而言,不仅受到政府与法院的牵制和制约;而且在国会内部,还存在着参众两院之间的牵制和制约,在立法程序中,若立法案在两院各自的大会上分别通过,则该议案就在国会被通过了;若其中有一院未通过议案,则视该议案未被国会通过。也就是说,在立法问题上,任何一院都不可能撇开他院,独自完成一项立法。
(3)从西方国家的现实政治事件来看,通过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确揭露了一些问题,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其中最著名的是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尼克松在其违规行为被曝光后,企图运用总统的权力罢免联邦检察官,以阻止调查的继续进行。结果,国会介入,国会众议院提出了对总统的弹劾案,并获得了参议院的支持。尼克松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而被迫辞职。由此可见,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并非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且确实发挥了它的作用,应予以肯定。
2.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局限性
(1)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造成了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扯皮,谁也不服谁,从而严重影响了权力运行的效率。邓小平说:“我经常批评美国的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经常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正是由于议会、政府和法院互不隶属,所以他们经常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相互抗衡,相互较劲,由此造成了整个国家机构运行效率的低下。比如,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为实现中美建交宣布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然而此举却遭到参议院部分议员的反对,他们将卡特总统起诉至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地方法院,而该法院法官居然荒谬地裁决卡特总统的此项决定违宪,并宣布其无效。后来,双方仍旧为此事争执不休。一直到一年以后,以美国上诉法院裁定卡特总统此举有效而告一段落。
(2)资本主义国家所建立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本身的分权并不彻底,具体体现在:
首先,在议会主权制国家中,是由在议会大选中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负责组建内阁的,而该政党的领袖自动成为政府首脑。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权实际上是由立法权派生而来,它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权力层级。
其次,在议行合一式体制中,分权制衡的色彩就更弱一些。因为国家立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掌握了全面的控制与支配权。政府与法院从属于议会,并无对其进行制衡的权力。
再次,即使在被视为是典型意义上分权制衡的三权分立式的体制中,也存在着缺陷和漏洞。比如,在美国,立法案经议会两院通过后,需交由总统签署才能最终成为法律,而对于该法案,总统有权不予签署。如果议会要推翻总统的这项决定,需由参众两院全体议员2/3以上多数通过。但是,在社会高度多元化的美国,要做到让绝大多数人对于同一事项做到口径一致是很难的。美国的总统们显然深谙此道,频繁用此举来抗衡国会。实践证明,此举也确实有效,总统否决立法案的成功率要远远高于议会推翻总统否决的成功率。至少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立法权并不能完全控制住行政权。
(3)在分工日益复杂和精细化的现代社会,面对着行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西方国家对立法权的控制与制约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现代社会对于其从业人员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行政机关凭借其掌控的丰厚的财经、政治资源吸纳了大批的专业技术精英。因此,西方国家的议会虽然表面上掌控立法权,但更为实质一些的立法提案权却往往由行政机关来行使。由立法机关直接提出的立法案少之又少,它真正的职能是审议和通过行政机关提出的立法案。然而,即使是在这个程序中,由于议员大多来自普通民众阶层,他们对于这些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立法案,也很难提出一些实质性的反对意见,除了表示赞同以外,似乎也别无选择。尤其是在议会主权制国家中,由于议会多数席位掌握在内阁所在的党派,而此类政党通过严格的政党纪律对于其党员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和控制力,所以内阁提出的立法案在议会被否决的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了。
[1][美]洛克.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浦兴祖.西方政治学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5]喻中.权力制约的中国语境[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6]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李步云.宪法的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8]顾俊礼.西欧政治[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9][美]罗斯金.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0]赵宝云.西方六国权力制衡机制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D9
A
1673-0046(2011)05-006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