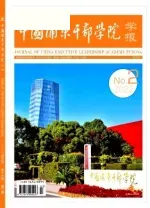共产国际、俄共(布)与中国早期革命者之间的联系——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背景
黄 黎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100006)
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宁欣喜地看到“极大的世界风暴新的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1](P447)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俄(苏俄是指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1922年底苏联成立这一阶段。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指1922年底到1991年间执政的政权——编者注)急于在东方寻求同盟者,但因当时帝国主义封锁海上、陆路的交通而未能实现。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中国革命新动向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怀有极大的兴趣,先后多次派人以各种身份来到中国,了解革命的情况,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特别是在中俄边界恢复交通后,共产国际、俄共(布)对中国的指导和帮助逐渐由间接转为直接,从零碎、表象变为完整、具体。
一
1918年5月,根据列宁的指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直属外国共产党组织中央局成立。该局在苏俄举办各国宣传员训练班,为各国培养建党的骨干。从此以后,一些神秘人物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他们当中就包括波波夫、奥戈列夫和波塔波夫。
1918年5月,波波夫到了上海,在密勒氏评论上匿名发表了一篇题为 《来自一位俄国无产阶级的呼吁》的文章,几个月后返回汇报。1919年五六月间,波波夫再度来到中国,调查了解中国的情况,几个月后回国汇报。1920年初,波波夫第三次来华时已是一名上校了,持有阿穆尔地区布尔什维克部队司令发给的证书。1920年初春,他同波达波夫将军代表苏俄数次拜访孙中山。会谈中讨论了双方的合作计划、确定了今后联络的方式。波波夫敦促孙中山对加拉罕第一次宣言作出公开反应。大约在1920年七八月间,波波夫因在日本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而被驱逐出境后转赴中国。
关于波波夫活动的资料只有警方简略的记录,没有发现派他来华的俄国方面的文件。因此,仅依靠这些资料不能断言,波波夫在1918年至1920年来华时的身份,已经是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组织任命的正式“使者”。
和波波夫几乎同时在中国开展活动的是奥戈列夫(即阿加廖夫,也译作阿格辽夫)。据1920年3月驻上海日本武官的报告称,“俄国人阿格辽夫正与李仁杰[李汉俊]、吕运亨等密函,计划发行俄汉两种文字的《劳动》杂志”。李汉俊是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士之一,而吕运亨则是当时在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的著名人士。事实上,在新近发现的一份秘密档案中,奥戈列夫是被当作维经斯基受派来华前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来记述的。这份档案资料这样写道:“迄今,在中国的工作是由个别俄国侨民做的,如天津大学教授柏烈伟(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出版的法文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报》的实际编辑A.A.伊万诺夫同志(来自巴黎,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老社会民主党人A.E.霍多罗夫(原海参崴报纸《遥远的边疆》的编辑)、A.Φ.奥戈列夫(原海参崴市参议会主席)等。”[2](P50)
波塔波夫原为沙俄帝国的高级军官 (少将),20世纪初在远东服役。十月革命时他正在中国,革命后他转而拥护布尔什维克,开始向苏维埃政权提供远东特别是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波塔波夫在上海期间曾于1920年3月与陈家鼐、姚作宾、曹亚伯、戴季陶、孙伯兰等名士有过交往。4月末曾和朝鲜著名社会活动家吕运亨一起,到过当时著名的“开明”将军陈炯明控制的福建省漳州。4月29日他与陈炯明会谈,提出对陈的革命活动予以援助。5月22日,波塔波夫还加入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大同党”。
与布尔特曼、波波夫等人不同,波塔波夫提供的情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俄的对华工作。陈炯明在接受波塔波夫的访问后写给列宁的信,就是通过波塔波夫送到了莫斯科,并刊登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1921年3月15日)上。
波塔波夫在上海和漳州收集的情报,有些是关于中国共产主义本身动向的,也提供给了苏俄方面。比如,1920年5月1日,他在漳州看到当地举行庆祝五一盛大的活动,这种情形通过他也报告给了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并与他接触过的上海学生领袖一同在维连斯基的文章中被介绍出来。1920年来华的俄共(布)使者维经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有一段称,“我无法同波塔波夫取得联系,因为他去欧洲了,或者回苏俄了”,[2](P29)看来维经斯基来华是以取得波塔波夫的协助为前提的。而在上海的日本谍报机关也在这个时期的报告中说,“波塔波夫从其头领 ‘塔拉索夫’(维经斯基的化名)处得到资金,作为当地的过激共产党人,正在开展活动。 ”[3](P79)这些情况表明,波塔波夫是维连斯基——维经斯基这条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渠道上的重要环节。
二
自1919年3月成立以后,共产国际十分关心东方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是,由于当时苏俄国内战争仍在进行,外国干涉还未停止,因而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和俄(共),只好委托苏俄东部地区的共产党员和旅俄华侨左翼了解中国情况,并与中国进步组织的代表建立联系。从这时开始,俄共(布)的代表同中国革命者开始有了断断续续的接触。
1919年3月,在鄂姆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认为,“准确而及时地将苏维埃俄国和西伯利亚的革命进程通报给美国、日本、中国和其他远东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情报宣传局”,并规定其任务是“与东方和美国的共产党建立联系,组织同他们交换情报的工作,进行书面和口头宣传……”[4](P64-65)
为了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加蓬于1919年6月18日在报告中,建议在区委下设立一个有远东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以便立即突出、全面地把工作开展起来,并且有效地完成其促进东方革命的主要任务。
1919年春,俄共(布)老党员、后来担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主任的布尔特曼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工会方面的工作很感兴趣。在天津,布尔特曼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同激进民主派学生及其领导人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布尔特曼称李大钊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布尔特曼还与天津爆发的声援北京五四大规模游行的工人罢工行动有直接关系。当时经常有一些学生去布尔特曼那里。布尔特曼向中国青年介绍列宁的学说,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告诉同学们必须同天津的纺织工人和码头工人建立直接联系,帮助他们组织工会。关于这个问题,布尔特曼还曾与李大钊谈过两次,李大钊积极支持这个革命倡议。布尔特曼同李大钊的亲密助手邓中夏保持了密切联系。
1920年1月15日,根据组织上的决定,布尔特曼同另4名布尔什维克一起离开天津,经北京、张家口,取道蒙古回国。途经蒙古时,布尔特曼会见了苏赫巴托、乔巴山等蒙古地下革命者,向他们讲述了苏维埃政府解放被压迫人民的政策。1920年7月,布尔特曼在伊尔库茨克组建了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并任处长。1921年的某一天,他准备打猎,在擦拭自己的左轮手枪时,不慎走火,因伤重去世,年仅21岁。
1919年秋,“高丽人巴克京春”即朴镇淳,奉共产国际之命也来到了中国。
朴镇淳生于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移居俄国,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十月革命后,他即致力于布尔什维主义事业。他是在苏俄的外国革命者中最早受苏俄领导人信赖的积极分子,被列宁、斯大林委派为苏俄民族事务委员部朝鲜人民委员。1918年6月,朴镇淳在西伯利亚俄共(布)地方组织的指导下,帮助朝鲜爱国革命领袖李东辉以旅俄韩侨为基础,在伯力建立了韩人社会主义者联盟,次年4月与其他组织合并在海参崴成立了韩人社会党。李东辉为该党主席,朴镇淳任总书记。
1919年8月5日,朴镇淳携带大笔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自莫斯科启程赴远东,约于11月抵达上海。当时的上海是朝鲜海内外独立运动的中心,自朝鲜“三○一”运动后,大批朝鲜爱国志士流亡至中国,一部分独立运动领导人于4月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随着李东辉于9月从海参崴来沪接任国务总理,韩人社会党总部也迁至此地。因此,朴镇淳来华的主要使命是巩固韩人社会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建立韩国临时政府与苏俄的联系。与此同时,他还试图促进、帮助经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对苏俄的进一步了解与接触,并在华组建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1920年春,他返回莫斯科,被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聘为朝鲜事务顾问。他还参与了筹备共产国际 “二大”,并在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1919年初,匈牙利共产主义者缪勒尔作为俄共(布)哈尔滨委员会的代表,到齐齐哈尔地区的中国地方武装中做宣传教育工作。据说,经他努力,这些队伍表示要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在中国进行革命斗争。缪勒尔的目的不是要使这群类似土匪的武装在短期内变成布尔什维克式的部队,而是鼓动他们扰乱和牵制日本军队和中国政府干涉军,以减轻俄国远东地区布尔什维克部队的压力。
1919年9月,缪勒尔从哈尔滨来到天津,与俄共(布)哈尔滨委员会1919年3月派到华北的俄共党员布尔特曼取得联系。那时,布尔特曼以在美籍俄裔企业家施泰因柏格于天津开办的石德洋行任职为掩护,租有一套两间的房子,缪勒尔和他同住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主要是反对同日本直接交涉、取消“二十一条”和“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解散亲日的安福俱乐部等。据缪勒尔回忆,在他到天津之前,布尔特曼已经和京津一些大专学校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同李大钊有很好的私交。他与在天津发生的声援北京五四示威的若干罢课、罢工运动有直接联系。缪勒尔在1957年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早在我到达以前,布尔特曼已经与天津和北京的高等院校里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布尔特曼称李大钊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我在1919年9月与布尔特曼会面时,他依然和学生们保持联系,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各种团体到我们的公寓来。……1920年1月初,在我们离开中国之前,一个由四名学生组成的小组已经与码头工人确立了联合,并已开始从事组织工会的实际工作。 ”[3](P74-75)
三
20世纪20年代初期,苏俄的国内战争结束,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也先后遭到了失败,资本主义开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便进入了一个积蓄力量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阶段。面对新的革命形势,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新的策略。
1920年9月1日至8日,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苏联、中国、印度、日本、朝鲜、土耳其等国37个民族的1891名代表(其中包括55名妇女代表)。中国有7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主要是旅俄侨民,其中有1名中国代表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大会号召对国内外压迫者进行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大会选出了东方各民族宣传和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整个东方的宣传工作,用4种文字出版《东方民族》杂志,组织出版宣传品,开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支持和统一整个东方的解放运动。最后,季诺维也夫在闭幕词中要求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制定了推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战略和策略。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向东方各民族宣传了这些战略和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大会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继续和补充。因此,列宁认为这两次大会表明了下述事实:“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在一切东方的落后国家里,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方式,已经成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和一切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农民谋求解放的旗帜,进行斗争的旗帜。”[5](P295)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促进了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联合,从而推动了东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1921年春,张太雷奉命离开中国去苏俄伊尔库茨克参加筹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他到伊尔库茨克之后收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任命他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的委任,并要他准备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他编写了有关中国情况的通报,并把这些通报寄到苏俄各家报纸的编辑部。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通知,派张太雷和刚从中国起程的杨厚德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杨厚德到达伊尔库茨克以后,和张太雷一道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1921年6月,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份他起草的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详细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
“(一)为了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方面的问题,为了中共同苏俄双方互通情报,同时也为了转达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的指令,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伊尔库茨克)设立中国支部。(二)主持中国支部的有两名书记——其中一名从中共中央派来担任这项工作的同志中选任,另一名则由远东书记处选派。(三)依据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这一总的组织原则,必须承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行(委)会远东书记处的相互关系,也是同样的组织关系,即驻在远东书记处的中共中央代表组成由该书记处所领导的支部。”[6](P615)
在远东书记处工作期间,张太雷还参加了筹备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组织局,并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1921年5月4日,张太雷在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致祝词,祝词中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任务。只有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建立起同日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才能达到这一目的。”[6](P615)
在这次代表大会期间,大家建议张太雷作一个《日本无产阶级与朝鲜贫民》的专题报告,进一步发挥他在祝辞中提出的要把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联合起来的论点。他接受了这个建议。1921年5月7日,他就此问题作了报告。他说:“朝鲜的贫民和工人没有任何理由同日本的工人为敌,相反,应当同他们联合起来,以便一道去战胜远东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资本家和日本帝国主义者。”[6](P616)在这篇专题报告中,张太雷进一步阐发了把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日本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的观点。这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张太雷提出的论断为基础,用日文发表一篇对日本工人的宣言,张太雷积极参加了宣言的起草和以后的付印工作。
张太雷在苏俄的这一经历表明,五四运动以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且也表明,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中国的革命者就开始同共产国际有了比较频繁的来往;同时还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在得到共产国际帮助的同时,也为共产国际做了不少工作,为世界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
1920年1月,由于高尔察克匪军被粉碎,中俄交通基本恢复,设在海参崴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致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要求与中国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俄共党员维经斯基和他的两名助手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朝鲜著名的活动家金万谦)赴华,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执委会东亚书记处。
当时,苏俄人员与中国来往的路线是,从伊尔库茨克出发,可沿四条交通线到达中国:取道蒙古,经恰克图、乌尔嘎;经过满洲里、哈尔滨到达北京;经过哈尔滨、海参崴到达上海;经过赤塔、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尔滨或者海参崴到达北京。维经斯基首次来华的路线就是: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哈尔滨-天津-北京。
与维经斯基一起到中国的,还有来自山东平度的华侨杨明斋,他担任翻译,与维经斯基一起到达北京。就在这个代表团抵达北京后不久,又有两位俄国人悄然来到北京,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其中的一位是俄国妇女萨赫扬诺娃,是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另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叫斯托扬诺维奇,又名米诺尔,俄共(布)党员。萨赫扬诺娃和斯托扬诺维奇前来北京,都是为了配合《生活报》记者代表团执行特殊使命的。
维经斯基等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首先在北京大学拜访了两个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凡诺夫(伊文),寻求他们的帮助。柏烈伟在北京大学担任俄语教员,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中国通。伊凡诺夫在十月革命前即在中国,从1919年9月起受聘为北京大学俄文系讲师,中文名字叫“伊文”。他们说起了北京大学、《新青年》、五四运动,甚至还谈到了“南陈北李”,比较准确地勾画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简貌。听到这些情况后,维经斯基决定访问“南陈北李”。陈独秀已经出走上海,他就请柏烈伟、伊文介绍,前往北京大学访问李大钊。
这时,苏俄已宣布废除沙俄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苏俄抱有好感。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期间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进步人士举行了多次座谈,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实际情况和苏俄的对外政策,使他们对苏俄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详细了解。
为了加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
维经斯基、萨赫扬诺娃和杨明斋很快动身去上海。他们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情况,并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条件已经成熟。5月,维经斯基等在上海筹建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内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中国科的主要任务是:“1.通过在学生组织中以及在中国沿海工业地区的工人组织中成立共产主义基层组织,在中国进行党的建设工作。2.在中国军队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建设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工作。”[2](P39)
1920年夏,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开始筹建共产党组织,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为了输送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1920年秋,维经斯基在上海创办了外文学社。上海外文学社由杨明斋负责,并由他和库兹涅佐娃讲授俄文,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学生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柯庆施、李启汉、任弼时、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等。同时,维经斯基还打算在武汉开办外文学社。为此,他曾派马球迈耶夫等人去武汉。
同年7月,在维经斯基的亲自指导下,杨明斋在上海设立了中俄通讯社,通讯社设于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该社由杨明斋负责。它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翻译和报道有关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资料;(二)把中国报刊上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它在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共建党工作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11月中、下旬,维经斯基根据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同他进行长达两个小时的座谈。会见时,孙中山询问了有关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的一些情况,介绍了袁世凯如何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复辟帝制的情况,提出了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的问题。此外,双方还认真探讨了如何把中国南方的斗争同苏俄的斗争结合起来。维经斯基事后回忆说:当时看得出来,孙中山也对这个问题极感兴趣,那就是:“如何把刚从驻扎在广州的反革命桂军手里解放出来的华南的斗争与遥远的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无法使我们与俄国建立联系’。他一直询问是否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满洲里建立一个我们可以和广州联系的大功率电台。”[7]
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时,虽然马克思主义已在中国有所传播,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建党学说的领会还不深,在很大程度上还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还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维经斯基来华后不久,就很快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等激进的知识分子,并经常同他们进行会谈,向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实况。通过维经斯基的宣传,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8](P432)从而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转化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维经斯基来华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急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组成马克思主义小组”;同时,“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建立阶级的工人工会;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同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思想;了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目标和任务。”[9]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到工人中去开展有组织和有计划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思想上组织上做好了准备。
为了加快在东方,特别是在中国开展革命运动的步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于1920年8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正式代表。马林来华后,很快得到工会国际联合会派遣来的弗兰姆堡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来的尼科尔斯基的密切配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直接派出代表来华,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马林的到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党在成立初期的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从此,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黄修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 [苏联]乌里扬诺夫斯基.共产国际与东方[M].莫斯科:莫斯科出版社,1969.
[5] 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
[7] 伍廷康.我与孙中山的会见[N].真理报,1925-03-15.
[8]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9] [苏]卡尔图诺娃.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援助(1920-1922)[J].远东问题,1973,(1).
-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总目录
- 论赴法勤工俭学先进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