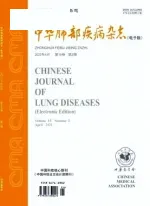支气管哮喘药物治疗的现状
赵丽萍 冯喜英
支气管哮喘是由包括气道的炎性细胞和结构细胞(如:嗜酸粒细胞,肥大细胞,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平滑肌细胞,气道上皮细胞等)以及多种细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炎性疾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其诱发因素多种多样,有些机制尚不清楚,目前我们还不能治愈哮喘,即使采用目前最有效的控制哮喘的疗法,像吸入性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s,ICS)联合长效β2激动剂(long-acting β2-adrenergic agonists,LABA)仍会有近1/3的中重度患者达不到哮喘的临床控制。据世界医学组织专业部门的统计,由于社会的进步、物质的丰富、饮食结构的改变,农业科技的进步,各种杀虫剂、保鲜剂等的应用,全世界每年哮喘患者多达五亿人,而每年有几千万人处于哮喘病的发作,且近年来仍呈上升趋势,现就哮喘的药物治疗的现状综述如下。
一、临床治疗哮喘的常用药物
1.布地奈德(ICS)及新型的ICS:由于哮喘的本质是气道的慢性炎症,因此ICS是目前治疗哮喘最有效的药物,现已成为哮喘长期治疗的一线药物。它主要作用于靶细胞,通过抑制气道炎症而有效地控制哮喘症状。许多研究表明,使用糖皮质激素可明显抑制IL-4和IL-5,而IL-4与呼吸道重构有关。就慢性支气管哮喘患者而言,即使长期给予糖皮质激素也难以降低其持续的呼吸道高反应性,临床上常用的激素有口服的泼尼松、静脉用的甲泼尼松龙,目前最常用的是吸入用布地奈德气雾剂(ICS)、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ICS从药效学及药代学方面来说仍不理想,它仅在小剂量范围内有明显的量效关系,在中等及大剂量范围内疗效并不明显,相反,全身副作用会明显增加。所以探究抗炎活性更强、全身性副作用更少的新型ICS是今后的发展趋势。现阶段研究最多的是新型ICS,如环索奈德(ciclesonide,CIC)、糠酸莫米松(mometasone furoate,MF)、糠酸氟替卡松(fluticasone furoate,FF)等[1]。
2.长效β2激动剂(LABA):以单一ICS并不能有效地控制中重度哮喘。目前GINA推荐的治疗中重度哮喘的首选方案,即ICS联合LABA已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现临床上使用最多的LABA有沙美特罗和福莫特罗,上述两种LABA需12 h使用1次。目前正在研究作用时间更长的所谓超长效β2激动剂(Ultra LABA)正在开发之中,如茚达特罗(indacaterol)、卡莫特罗(carmoterol)、阿福特罗(arformoterol)等[1]。
3.茶碱类:茶碱及其衍生物是常用的平喘药物,应用已经有五十多年,属于黄嘌呤类衍生物。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该类药物除具有直接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的作用外,还具有兴奋呼吸中枢,降低肺动脉压,减少渗出和抗炎作用。研究表明低浓度的茶碱具有抑制气道变态反应性炎症作用,其抗炎作用具体表现为:①抑制IgE介导的肥大细胞释放组胺,通过提高人体内嗜酸粒细胞和肥大细胞内环磷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cAMP)的浓度而抑制其释放;②通过降低支气管哮喘患者呼吸道中IL-4和IL-5的含量来影响花生四烯酸的代谢,从而使嗜酸粒细胞释放白三烯减少约61%;③茶碱可明显抑制中性粒细胞黏附毛细血管壁,进一步抑制其游出毛细血管而发挥吞噬作用,同时能增强单核-巨噬细胞的趋化作用。由于平喘效果显著,是临床上首选药之一。目前临床使用的有氨茶碱、二羟丙茶碱及茶碱缓释片、控释片等。今后主要是以小剂量,长效控释制剂为其研发方向。
4.M胆碱能受体阻滞剂:M受体阻滞剂治疗支气管哮喘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其主要通过抑制支气管平滑肌迷走神经的运动能神经元所释放的乙酰胆碱而起平喘作用,但该阻滞剂由于对M受体选择性差,可引起口干、痰液粘稠、中枢神经系统兴奋等全身副作用而使之在临床上的使用受到限制。新近研发的M1、M3受体阻滞剂,如溴化阿托品克服了以上副作用,日益受到临床哮喘治疗的重视。此药对支气管哮喘伴有咳嗽症状的患者有较好的疗效,而对急性支气管哮喘患者无效。目前临床使用的有溴化异丙托品气雾剂、吸入用噻托溴铵粉剂。此外有研究报道,长托宁与溴化异丙托品比较,长托宁气雾剂选择性更高,其作用更强,副作用更小,在支气管哮喘的治疗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2]。然而,作为一种新剂型,长托宁气雾剂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尚需进一步作临床与实验研究。
5.过敏介质阻释剂:该类阻释剂是以色苷酸钠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平喘药。其主要机制是通过稳定肺组织肥大细胞膜,抑制过敏介质释放,阻断引起支气管痉挛的神经反射,降低哮喘患者气道高反应性。此外,它还抑制炎性介质的释放,具有一定的抗炎并起到防治哮喘发作的作用,同时还具有对肺泡巨噬细胞、嗜酸粒细胞、单核细胞等炎性细胞及其炎性介质的选择性抑制的功效。色苷酸钠适用于各类型哮喘发作,对外源性哮喘疗效尤为显著,特别是对已知抗原的年轻患者疗效更佳。用药后患者症状明显减轻,肺功能改善、肺活量显著增加、呼吸困难指数降低,对内源性哮喘和慢性持续期哮喘亦有一定疗效。
6.抗白三烯类药物:此类药物是近几年来研究发现治疗哮喘的一种新型约物,临床上常用的扎鲁斯特和孟鲁司特就是白三烯受体拮抗药,属于此类的还有白三烯合成抑制剂—齐留通。临床试验表明白三烯调节剂有轻度舒张支气管、缓解症状、改善肺功能、减轻气道炎症和减少哮喘恶化的作用。作为哮喘控制药物,其主要通过竞争性结合半胱氨酸白三烯而抑制白三烯的活性,有效预防白三烯多肽所致的血管通透性增加,抑制组胺和过氧化物的产生,从而阻断气道炎症的发生和发展。目前美国一专家小组已将抗白三烯类药物作为轻度持续性哮喘患者吸入激素的替代药物。但吸入激素仍是目前哮喘治疗方案的首选抗炎药物,抗白三烯类药物尚不可能在所有患者中代替吸入激素疗法。
7.酮替芬:酮替芬具有很强的H1受体拮抗作用,能抑制支气管黏膜下肥大细胞释放炎性介质,抑制细胞内Ca+释放,并可逆转因反复使用β受体激动剂而下调的β受体敏感性。
二、其他具有治疗哮喘的药物
1.他汀类药物:应用辛伐他汀治疗过敏性哮喘是近几年的新发现,它不仅具有降脂的功能,而且在抗炎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它能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及迁移,还有改善肺血管重构的作用[3]。体外实验表明,辛伐他汀能抑制IgE诱导的人的肺脏肥大细胞释放组胺[4],并能呈剂量依赖性诱导哮喘患者EOS凋亡。已有不少学者试用辛伐他汀治疗支气管哮喘,但目前还需对辛伐他汀在临床治疗哮喘方面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2.酚妥拉明:重症哮喘的发生主要是因引起哮喘的过敏原和其他因素持续存在,气道反应性过强而致。常用的平喘药物和剂量往往疗效不佳。有学者报道酚妥拉明有阻断α受体、保留并增强β受体的作用,以及抑制过敏因素释放的组胺(5-HT)的作用,同时与扩张支气管、改善肺循环和舒张支气管平滑肌有关[5]。有人认为酚妥拉明在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应用日趋广泛,而且酚妥拉明治疗哮喘安全有效,对没有呼吸机的基层医院更有价值,尤其在急诊应用中已日益受到重视。
3.肺表面活性物质(pulmonary surfactant,PS):近年来人们开始重视PS在哮喘病理生理中的作用,认为PS功能失调也可能是哮喘时气道阻塞的病理生理机制之一。临床上已有吸入PS成功治疗哮喘的报道,因此,用PS治疗哮喘,尤其重症哮喘,可能是人类治疗哮喘的新手段,但仍需深入研究PS在哮喘治疗中的潜在价值及其与常规治疗的关系[6]。
4.骨髓嗜酸粒细胞祖细胞抑制剂:近年来通过测定骨髓祖细胞表面抗原标志物,发现哮喘患者骨髓嗜酸粒细胞祖细胞数量明显增多,功能异常,其生成的嗜酸粒细胞经血循环聚集于肺,处于持续活化状态,导致气道过敏性炎症及哮喘症状,并认为这是哮喘发病机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吸入糖皮质激素对嗜酸粒细胞祖细胞有一定抑制作用。研究表明IL-5是重要的造血细胞因子,对嗜酸粒细胞祖细胞的分化和成熟具有独特作用,IL-5受体拮抗剂及抗IL-5抗体可抑制抗原诱导的嗜酸粒细胞活化和移出骨髓,降低气道高反应性。维A酸可选择性地抑制骨髓祖细胞IL-5受体的表达,进而降低嗜酸粒细胞的数量及功能活化[7]。
5.钙拮抗剂:此类药物可使气道平滑肌舒张,从而达到缓解哮喘症状的作用,如硝苯吡啶等。
6.秋水仙碱:秋水仙碱在临床上主用于痛风的治疗,近年来发现其有抗炎作用。可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胺,并促使其释放前列腺素E,还能抑制嗜碱粒细胞释放白三烯和IL-1,并可促使哮喘患者功能受损的抑制性T细胞功能恢复。
7.钾通道激活剂:有研究报道,钾通道抑制剂主要通过抑制气道高反应性,产生抗神经性炎症作用,并能减少气道微血管渗漏,抑制多种致痉剂诱发的气道平滑肌收缩。常用的有克洛吗卡林、左旋拉吗卡林。
8.利多卡因:它能显著抑制中、重度哮喘儿童由P物质激发所致的FEV1下降,其抗哮喘的确切机制目前尚未阐明,可能与利多卡因拮抗诱发因素所致呼吸道收缩有关,包括阻滞迷走神经反射和抑制呼吸道平滑肌收缩,但静脉给药和雾化吸入给药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8]。
9.硫酸镁:硫酸镁可直接舒张支气管平滑肌,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用于哮喘急性发作的治疗报道。硫酸镁对己接受常规药物治疗的慢性患者无效,仅对急性、重度患者有效。有报道,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硫酸镁治疗急性重症哮喘患者22例,总有效率为100%,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9]。
10.利尿剂:速尿是临床上常用的袢利尿剂。有学者报道,将速尿40 mg+0.9%生理盐水20 ml雾化吸入治疗哮喘,总有效率可达92%。其机制为松弛支气管气道平滑肌,抑制气道内肥大细胞释放多种介质,减少气道内感觉神经末梢冲动的传入,使气道上皮释放具有扩张支气管作用的前列腺素,改善气道上皮细胞的水转移从而防止黏膜水肿等[10]。但口服或其他途径给药无此效果。
11.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大环内酯类抗生素除具有抗感染作用外,长期低剂量应用可治疗支气管哮喘、弥漫性泛细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等慢性炎性疾病。临床研究显示,长期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可通过抗炎机制减轻哮喘患者的症状和降低气道高反应性。细胞和组织学研究也提示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具有不依赖于起抗菌活性的一系列抗炎作用,其抗炎活性仅限于十四元环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而十六元环的交沙霉素等无此作用。
12.磷酸二酯酶4(phosphodiesterase 4,PDE4)抑制剂:PDE4可提高细胞内cAMP水平,下调炎症介质的释放和致炎细胞因子的产生。新型制剂如西洛司特、罗氟司特已进入哮喘Ⅱ-Ⅲ期临床研究阶段。
三、基因及免疫治疗药物
1.基因治疗:基因治疗是指运用DNA重组技术设法修复或调节细胞中有缺陷的基因,使细胞恢复正常功能,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由于呼吸道被覆上皮的表面积极大,因此可将上皮细胞作为基因治疗的靶细胞,通过雾化吸入方式将目的基因转入,这样不仅可保证使目的基因在肺部局部发挥作用,同时还可减小由体循环注入引起的不良反应。国外已有在鼠类研究中成功应用信号转导及活化子6抑制相关肽(STAT6-IP)吸入,从而减少气道上皮细胞的炎性反应起到治疗哮喘的报告。另外,也可体外转染淋巴细胞或单核-巨噬细胞然后再回输体内,使其在肺部释放出目的基因编码蛋白,调节机体免疫反应[11]。
2.免疫治疗
(1)特异型免疫治疗(special alien immunotherapy,SIT):该法也称脱敏治疗,通过皮下注射常见吸入变应原提取液(如尘螨、猫毛、豚草等),减轻哮喘症状和降低气道高反应性,适用于变应原明确但难以避免的哮喘患者。目前SIT所用过敏原浸液含有多种致敏原和非致敏物质,注射后会引起全身过敏反应或导致新的致敏而恶化疾病。因此,开发高纯度、无致敏性的过敏原制剂是近年SIT研究的重点。
(2)抗IgE治疗:研究表明哮喘患者血清IgE升高,因此,通过减少哮喘患者IgE的产生或拮抗IgE的作用减轻哮喘患者症状,这是治疗哮喘的新途径。现主要制剂包括抗IgE抗体、抗CD23抗体、FcRI上与IgE结合的可溶性亚单位、IgE衍生的肽和寡聚核苷酸等。
(3)其他细胞因子:如抗IL-4抗体、IL-5抗体,IL-4和IL-5在哮喘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其抑制剂可作为哮喘治疗的可行性药物。此外,抗肿瘤坏死因子-α、IL-10、IL-12、IFR-r等也对哮喘的治疗有一定的价值。
(4)卡介苗及其衍生物:其用于防治哮喘的主要机制是刺激抗原呈递细胞尤其是树突细胞的成熟,增强其表面协同刺激因子的表达,并使之迁移到淋巴结和脾脏后呈递给T细胞,使之活化并分泌Thl型细胞因子[12]。目前研究最多的是卡介苗多糖核酸注射液[13]。
(5)免疫抑制剂:一些发达国家开始用免疫抑制药治疗支气管哮喘,已经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这类药物主要是氨甲蝶呤(methoterexate,MTX)和环孢素A(cyclosporine,CSA)。该类制剂通过干扰T淋巴细胞的信息通道而抑制其功能,并对肥大细胞、嗜酸粒细胞、嗜碱粒细胞等免疫效应细胞具较强的抑制作用。为降低MTX的毒性反应临床应用以小剂量为宜。CsA治疗严重的激素依赖型哮喘,主要不良反应是肾毒性,需严密监测。
综上所述,随着对哮喘疾病本质认识的逐渐加深,哮喘的治疗已由单一治疗转变为多种药物的联合治疗,由患者的被动治疗改为患者的主动治疗,结合患者自身特点的个体化治疗,由单纯抑制气道炎症为主的治疗转变为兼顾抑制气道重塑的综合治疗。由于哮喘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复杂,至今哮喘仍是一种只能控制而不能完全根治的疾病。今后随着人们对哮喘病理生理、发病机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及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的进一步发展,哮喘的发病机制最终将被人们所了解,更多新型有效并且安全的治疗哮喘的药物将会不断问世,更多的哮喘患者将会得到良好的控制或完全控制以达到正常人或接近正常人的生活和工作。
1 王长征.哮喘治疗新药的研究进展[J].中华肺部疾病杂志,2010.3(2):1-3.WANG Chang-zheng.Progress of study on new drugs I treatment of asthma[J].Chin J Lung Dis:Electronic Edition,2010,3(2):1-3.
2 张晋瑞.长托宁气雾剂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研究[J].中国现代医生,2007.45(11):77.ZHANG Jin-rui.Clinical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bronchial asthma with penehyclidine hydrochloride gas[J].Chin Modern Doctor,2007,45(20):77.
3 Sonza-Cesta DC,Figueiredo-Lopes L,Alves-Filho JC,et al.Protective effects of atorvastatin in rat models of acute pulmonary embo1ism:involvement of matrix metalloproteirmse-9[J].Crit Care Med,2007.35(1):239-245.
4 Schaafsma D,Gosens R,Bos IS,et al.Allergic sensitization enhances the contribution of Rho-kinase to airway smooth muscle contraction[J].Br J Pharmacol,2004,143(4):477-484.
5 党海燕.酚妥拉明治疗支气管哮喘持续状态的疗效分析[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4(4):172-173.DANG Hai-yan.Effects of phentolamine on treating status asthmatics[J].Chin J Modern Drug Appl,2010,4(4):172-173.
6 江隽瑛,方 凤.肺表面活性物质在支气管哮喘发病中的作用研究进展[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3,26(6):366-368.JIANG Xiu-ying,FANG Feng.Progress of the role of pulmonary surfactant in asthma[J].Chin J Tuber Respir Dis,2003,26(6):366-368.
7 Hansel TT.New treatments for asthma:current and future[J].Rspects Curt Opin Pulm Med,2001,7(Supp1)l:S3-S6.
8 顾经宇.利多卡因治疗哮喘的临床新应用[J].国外医学呼吸系统分册,2004,20(1):9-11.GU Jing-yu.Clinical new use of Lidocaine for treatment of bronchial asthma[J].Sect Respir Sys Foreign Med Sci,2004,20(1):9-11.
9 杨声坤.硫酸镁对急性重症支气管哮喘的治疗作用[J].临床荟萃,2005,20(22):1303.YANG Sheng-kun.Therapeutic action of magnesium sulfate for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bronchial asthma[J].Clinical Focus,2005,20(22):1303-1304.
10 齐激扬,吕冬青,赵 瑾.速尿雾化吸入对哮喘发作期患者的平喘作用[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1998,21(6):374-375.QI Ji-yang,LV Dong-qing,ZHAO Jin.Antiasthmatic activities of spray inhalation of Furosemide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 in its acute attack period[J].Chin J Tuber Respir Dis,1998,21(6):374-375.
11 Kolb M,Mantin G,Medina M,et al.Gene therapy for pulmonary diseases[J].Chest,2006,l30(3):879-884.
12 商 艳,胡振林,李 强,等.卡介苗及其衍生物与支气管哮喘的治疗[J].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03,26(3):169-171.SHAN Yan,HU Zhen-lin,LI Qiang,et al.Bacillus calmette-guerin and its deriva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asthma[J].Chin J Tuber Respir Dis,2003,26(3):169-171.
13 裴学惠.卡介苗多糖核酸注射液对支气管哮喘患者的疗效观察[J].医学理论与实践,2009,22(4):420-421.PEI Xue-hui.therapeutic effect of BCG vaccine polysaccharide nucleic acid injection in patients with bronchial asthma[J].J Med Theory Pract,2009,22(4):42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