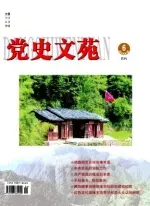解析李大钊新闻思想的包容性
翟金霞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石家庄 050024)
解析李大钊新闻思想的包容性
翟金霞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石家庄 050024)
作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创建者的李大钊,浸透在报业生涯中的一贯的饱含着包容的新闻思想,全面地体现在如父亲仁爱般的对青年群体人生观的启蒙、如导师般的对进步社团的关怀与调和和对未来新闻从业青年的引导与指点之中;鲜明地体现他在作为报纸负责人在引入新的学术思潮过程中平衡地允许反对观点的发表,在与胡适“问题与主义”的探讨过程中承认并吸收对方的合理部分,完善其思想体系的科学性;深刻地体现在李大钊力戒盲目接受、冷静分析、防止片面理解外来思潮,承认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时代性之中。
李大钊 新闻思想 包容性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行者,而且是中国早期著名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的先驱者。与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向紧密相关,李大钊积极地投身于 《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等报业的新闻实践活动,从而奠定了他的无产阶级新闻报业的实践和理论基础,确立了他在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中的领袖地位。与同期其他的参与新闻活动的政治家不同,李大钊的新闻思想的重要特征就是其与众不同的包容性。本文主要针对李大钊新闻实践活动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探讨李大钊新闻思想包容性的方方面面。
一、对青年的关怀仁爱体现新闻思想的包容性
李大钊无论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创建人,或作为北京大学教授,还是作为报纸编辑或主要负责人,他都时刻关注青年一代的成长与发展,关心青年的理想与事业等价值观的构建,引导进步青年社团组织的创建及其各种分歧的调和,关心青年新闻思想及其实务能力的培养。因此,对青年群体活动的关怀与仁爱非常明显地体现着他的新闻思想的包容性特征。
(一)包容青年成长存在的问题,启蒙青年构建科学世界观
青年是人类的未来,是世界的未来,也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未来。作为政治家的李大钊,深知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因而一直把教育启迪青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李大钊与同时期的其他政治家对青年的启蒙侧重有所不同,他不是以居高临下的领袖姿态强硬地将政治教育填鸭式的灌输给青年,而是以宽厚仁爱的胸怀时刻关注并导引广大青年的人格向自由、博爱的方向发展。在当时动荡混乱和颓败的社会,作为青年灵魂导师的李大钊对青年民众、对少年中国依然充满了无限希望。他利用报纸的导向性作用,通过编辑的途径把《晨钟》等报刊作为对现代青年进行启蒙教育的窗口,相继在报刊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为中国青年一代点亮了通往未来人生、事业和革命的路灯。
在《双十字上的〈新生活〉》中,李大钊写道:“爱力愈大,所爱愈博。充博爱的精神,应该爱世界的人类都像爱自己的同胞一般,断断不可把这个‘爱’字关在一个小的范围内。”[1](p62)这是《新生活》的时评,李大钊在把《新生活》作为新一代青年前进迷途中的向导的同时,为青年描绘了自由、平等的生活画卷,启蒙青年和社会所有人包括撰稿人李大钊自己要“博爱”。李大钊新闻思想包容性体现在文章中,则是他引导青年要有“博爱”的精神,而这种“博爱”的精神就是饱含着包容的精神,这就要求李大钊和他所要引导的青年不仅要包容自己的家,包容自己的祖国,更要包容世界的人类。另一方面,李大钊作为《新生活》编辑负责人,在他的新闻思想里,首先包容了正在发展中的有着各种问题与迷惑的青年。正是这种新闻编辑理念对于青年读者成熟前种种迷惑的包容与正确的启蒙,使得报纸编辑及其编辑的报纸对一代人的健康成长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这种编辑理念的包容性,来自有责任心的报纸编辑内心深处的新闻思想,因而往往渗透于他的新闻写作与编辑的方方面面。
在另一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李大钊写道:“我想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人人理想中必定都有一个他自己所欲创造而且正在创造的‘少年中国’。”[1](p11)这个“少年中国”是一个与残酷的现实相对立的、无数青年心中的“少年中国”的理想的一个大集合,这其中又充满了包容的精神理念。他说,“你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不必相同;我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又和他理想中的 ‘少年中国’未必一致”[1](p11);只要青年有健康的理想,无论你是否接受我方的党性理念的要求,这样的青年都是“少年中国”的有理想的青年,都在携手同行,沿着“那一线清新的曙光,向光明方向走”。李大钊作为报纸负责人,他没有像其他党报负责人那样,单方面的进行政党的政治宣传,强制性地从党性上单方面要求青年无条件接受,而是把对青年的教育健康化多样化,启蒙青年要有“少年中国”的理想,并为理想付诸于“少年运动”。这种以父亲般的博大胸怀对青年成长的关怀,体现了李大钊作为政党报纸编辑对青年政治引导外的难得的包容性的理想教育。
(二)包容青年组织面临的分歧,引导青年团结革命力量
对于青年群体成长过程的关怀,李大钊不仅仅停留在发表时评等文章上,对于青年社团活动的长期指导是李大钊的社会活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的对青年困惑和青年组织问题的积极引导,及时地解决了进步青年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引导很多进步青年迅速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北大校园里,李大钊诚朴谦和的态度使很多青年学生愿意与他接近;在图书馆里,他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如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曾怀着深厚的感情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国民》杂志社和《新潮》杂志社是五四运动前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进步社团,当时两个社团之间由于思想倾向不同经常发生争执。李大钊作为两个社团的导师和顾问,根据他多年的报业工作经验对其进行了多方面地调解,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这个共同点融合两个社团努力方向上的分歧,使这两个社团团结在北大学生会周围,后来成为五四运动中一股重要的进步力量。
1920年8月初,天津觉悟社举行年会后,以周恩来为首的11个社员来到北京请教李大钊,他开了一个进步社团的名单。8月16日,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的代表20余人,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举行了茶话会。李大钊的讲话总结了学生组织的积极方面,对到会的青年进行了热情的鼓励并结合各个社团的共同点提出 :“各团体要有一个明确的主义,主义不同,就不能团结一致。”[2](p100)他以革命需要力量的经验告诫青年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这是各个社团互相包容的结果。他以朴实、谦和的态度教育青年包容其他青年团体并对到会青年提出了恳切的希望——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即包容劳工和农民,只有这样,分散在各处的革命力量才会团结起来。李大钊积极促进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让他们了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促使青年尽快成长。李大钊对青年的这些谆谆教诲,为“五四”后的青年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三)包容青年刻板新闻观念,鼓励青年继续坚定革命信念
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需要出发,从青年人在革命活动中的发展需要和青年新闻人才进步的需要出发,李大钊在关心现代青年的成长和活动方向的同时,更关注进步青年的新闻事业活动,因而对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念表现出了宽广的包容态度。
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领袖,李大钊对于未来的新闻记者抱有很大希望。他在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以《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为题的演讲中说:“我以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3](p39)他认为,新闻事业“描写社会现象”如同社会事业一样灵活,因为社会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要想把这些不断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记录下来,青年新闻工作者非要打好扎实的新闻功底不可,这种功底要练就到将细致工作做好,如策划每日新闻选题、如何运用新闻材料等。他列举达尔文诞辰130周年的事例,北京的报馆若有在今日把达尔文的历史、肖像和他的学说概要登出来,把历史的今天和现实的今天结合起来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里,李大钊对青年寻找新闻事件、突现新闻价值的启迪,不是狭隘地将自己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身份去要求青年在政治上如何争取先进、在报纸编辑采访中如何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而是以有经验的新闻从业人员的身份从新闻实务的角度引导青年去更多的学习新闻采写技巧、提高新闻业务能力,这种超越政治局限的对青年新闻工作者的耐心引导与包容,是当时其他办报的政治家和资产阶级报人所不具备的。
“二七”大罢工失败之后,陈独秀等人过多地关注了“二七惨案”军阀血腥屠杀和残酷迫害的严重后果。在上海,他把参加“二七”斗争的青年当作一群鲁莽无知的毛孩子,对他们参加“二七”活动大加训斥。李大钊却像仁爱宽容的父亲一般,把进步青年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热情地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从更加高远的角度引导青年分析革命形势:对于“二七”惨案不应只从消极方面看,更要从积极方面看,虽然有很多的同志牺牲或遭到迫害,但是中国的工人运动不但震动了全国,而且影响了国际,这对今后的革命斗争有着深远的意义。为此,他撰写并发表了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激励青年同志乃至国人:“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3](p375)此时的李大钊用昂扬的革命斗志,用及时有力的评论文章,用对革命形势的理智认识鼓励青年,坚定了进步青年的革命信念。
由此可见,李大钊对于青年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时、包容地关怀与指导,体现了作为青年导师和新闻理论家的包容与引导的最高境界,更体现了他关怀仁爱地导引青年新闻活动的包容性思想情操。
二、思想论争中的全面与平衡体现新闻思想的包容性
在新闻业务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公正、客观的新闻原则所极力追求的就是报道的全面性和平衡性。新闻报道的全面性,要求新闻报道提供各方面的事实、情况、意见;新闻报道的平衡性,要求在突出报道一种主要因素或意见时,还要顾及其他因素或意见,特别是相反的因素或意见,即使是少数人的意见,或者在传播者看来是错误而不加认同的意见,也应无保留地向公众公开报道,而不是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公众。这种新闻报道过程中全面性和平衡性能使新闻受众更客观地看待所报道的事物,更准确地了解事物及其内外联系,从而得到对事物公正客观的认识。与同时期的资产阶级政党主办的报纸相比较,李大钊在主持编辑《晨报》和《新青年》期间尤其注意运用新闻报道的全面性和平衡性来保证新闻传播的公正客观,从而鲜明体现了他的包容性的新闻理念。
(一) 主编《马克思研究专栏》,允许反对观点发表
1919年《晨报》副刊开设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在李大钊的主持下成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该《专栏》在发表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本和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全译本的同时,还刊登了一些反对马克思的文章,其中就刊登了推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胡适的《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等文章,后来李大钊又刊登胡适的《正统哲学的起源》,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纲领。
在当时,由于传播技术条件的限制,中国受众很难及时了解到世界各地的快速变化,包括新的社会思潮的兴起,全国受众处在信息相对匮乏状态。这就需要当时的报纸编辑在介绍外来新生事物的同时坚守新闻传播的全面性和平衡性原则,在报道中尽量提供多方面的信息、多角度的观点,使受众对新闻实事有比较广泛的接触面,从而做出准确、科学的判断,避免形成认识上的片面甚至曲解。在新闻编辑中,平衡性既是一种原则,也是一种新闻编辑理念,这是新闻客观性原则的重要保障,政治家主办的报纸也不能例外。
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晨报》副刊的政党办报的宣传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李大钊的指导编辑下,《晨报》不但没有单方面的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反而刊登了一批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资产阶级改良和实用主义的文章,从两个对立的角度平衡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新闻受众,使读者通过自己的对比思考得出结论,从而判别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意义。当时正是资产阶级政党大呼新闻报道要坚持全面平衡的时候,但是,新闻编辑过程中对于全面性和平衡性的操作大都停留在口头上,李大钊主持编辑的、代表刚刚兴起的无产阶级声音的《晨报》,在刚刚介绍马克思主义之时就如此到位地贯彻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原则,更加深刻地体现了李大钊在编辑《晨报》过程中的饱含着包容的博大的情怀,这是十分难得的。
(二)主动开展自我批评,接受论敌观点的合理成分
在五四前后新闻业务的具体实践中,报纸之间对于新闻导向的不同、一份报纸内部编辑之间对于社会发展哲学的信仰不同是普遍存在的。而作为一名合格的报纸编辑,要想做到新闻传播的公正与客观,如何正确把握他所信仰的哲学理念和与之对立的哲学理念之间的关系,是五四时期各种秉承新闻导向理念不同的报纸编辑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作为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的先驱者,李大钊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当时与众不同的宽厚和包容。这个问题突出表现在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上。
对“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双方讨论的中心在于胡适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只主张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一个一个的去研究解决社会问题。他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4](p141)而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推崇者,主张“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先宣传主义……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2](p50),这样,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另外,胡适还把李大钊对于“主义”的研究归结到对学问的态度上。他说:“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4](p141)李大钊用他仁厚的胸怀避开胡适对的公开讽刺,用他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进行充分的说理、委婉的商讨,来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即“根本解决”的实质“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5](p284),“根本解决”的方法是阶级斗争。同作为《每周评论》的编辑,胡适在他所认同和反对的哲学理念时所暴露出来的少加思考的狂热和对于其他哲学思想的一概否定正是新闻编辑所应避免的,而李大钊对于理论的接受建立在仔细分析判别的基础上,把他推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念解剖开,帮助受众条分缕析的深入细致地解释,以达到传播新哲学思潮的目的。
在论争中,胡适把对“问题与主义”的关系片面归结为“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4](p141)。而李大钊撰写介绍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时并没有像胡适那样一概抹煞马克思主义,他对胡适解决具体问题的主张并未一概否定,而是在勇于自我批评的同时,客观全面地看到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中的合理部分。同时,他还提出:“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去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6](p49)李大钊之所以这样写,表明他并不认为中国当时已经具备了“根本解决”的条件,并希望人们脚踏实地的工作,从而为“根本解决”创造条件。他的这种想法和倡议,把自己坚持的长远的理想目标和从根本改变社会的基本途径与目前胡适一直坚持的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统一在了一起,不仅全面客观、符合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同时也体现了作为《每周评论》编辑的李大钊对待哲学理论问题的谦虚谨慎的态度,尤其是体现了李大钊在对待理论分歧问题时所特有的的包容性的宽广胸怀。
(三)承认实践认识不足,吸纳论敌观点的合理部分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因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无论它产生时多么具有前瞻性,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印记,同时也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趋于更加合理。胡适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持反对的态度,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空洞的理论”,他断言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4](p141)对于胡适漠视“主义”,只重“问题”的见解,李大钊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是群众,而“主义”具有唤起群众自觉、引导群众团结的作用。但是,李大钊在批评胡适的同时,也冷静地分析了他的理论的合理之处,如他对胡适要求具体考察中国社会情形,研究中国社会需要的观点表示了赞同。李大钊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5](p284)他认为,应该加强对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客观认识,考察中国社会具体情形,研究中国社会的真正需要,从而才能找到合适的主义——社会主义,唤起群众自觉来解决所有问题。
正是由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和吸收对方合理成分的包容性,李大钊的总体认识较之照搬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的胡适来说就完整全面了许多。李大钊认为,主义本身“都有理想和实际两方面”,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包含着适应各国实际的普遍规律,其“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5](p284)。同时,李大钊在力主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问题获得根本解决的同时,也明确提出,理想用于实际,应该“因时、因所、因事的情形”[5](p284)。这表明,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合理吸收其他理论中的科学部分使来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更适应于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从而完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作为中国五四时期著名报人,李大钊对外来思想理论流派的公正与客观的认识也显著地体现在他的报纸编辑工作和稿件撰写当中,从而形成了带有极强包容性的新闻思想,而这种包容性又体现在全面与平衡的编辑思想和具体实务操作过程中。
三、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冷静与科学体现其新闻思想包容性
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为中国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作为共产党早期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以政治家身份办报是李大钊新闻职业生涯时间最长、编辑撰稿分量最重的部分,因此解析李大钊新闻思想的包容性终究要联系到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上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分两次刊登在《新青年》上的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一篇论文,也正是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始,使得李大钊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以冷静与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倡导者。因此,很有必要通过他对待马克思主义冷静与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李大钊新闻活动,从而解析其新闻思想的包容性。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章总体所阐释的内容看,李大钊涉猎的资料很多,对各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材料,无论是赞成的反对的还是中立的资料,他都尽可能集中整理,并进行仔细分析研究,形成了他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观,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是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集中缩影。
(一)冷静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力戒盲目接受
报纸杂志的编辑有责任向他的新闻受众及时传播社会上的各种变化发展,自然包括世界各地有影响的社会哲学思潮。1917年的十月革命震惊了世界,也向全世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李大钊作为当时的报业领袖之一,以他开阔的视野和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及时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并及时地担当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责任。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部分李大钊就写到:“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1](p15)因此,他特别强调谁要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尽毕生的精力去加以研究。因为只马克思那本名著《资本论》就3卷,合计2135页,“第一卷和二、三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1](p15)。在对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他始终表现出谦虚认真、冷静科学的态度。他说自己“谈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僭越得很”[1](p15),拼上半年功夫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不过仅能就已刊的著书中把马克思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李大钊特别强调报纸编辑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长期不懈地进行深入研读,掌握了马克思哲学的精华之后,才能科学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不至于在传播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误解和歪曲。
与李大钊不同的是,当时不少人士在历史资料中查不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迹象,却忽然宣称自己也支持马克思主义,要做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士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基本上是来自于他的政治目的和一时的盲目热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盲目崇拜的做法,正是李大钊声明“愿意谈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直力戒的。对比之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是基于他钻研分析过卷帙浩繁的理论著述之后,并严密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适用性。甚至在他花费半年时间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后,还谦虚地与读者说自己只是在马克思反复陈述的主张中“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作为《新青年》的编辑,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谦虚的态度正体现了他新闻思想的科学性和包容性。同时,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伊始就请读者包容他自己的知能谫陋,这种与读者之间默契的相互包容更体现了李大钊作为报纸编辑的博大胸怀。
(二)纠正马克思的片面论述,力求科学完善
作为政党宣传的报业负责人,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甚至包括部分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在对待自己党派所尊崇的信仰时都没有李大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时这样冷静科学的态度,都没有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大胆而科学的扬弃。在李大钊眼里,允许他所推崇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完美的,但是他也更认为自己有责任适当地将这个理论加以完善。而浸透在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这种扬弃态度之中的思想就是贯穿他的整个新闻思想的包容性。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七章重点讲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所占的地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否认现在的经济组织,而主张根本改造”,“其目的在社会的革命”[1](p15),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在这里,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十分严谨,他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美无缺的,他认为马克思主张经济决定论是不完善的,故包容性地主张用人道主义经济学“人心改造论”、“道德的革命”弥补其不足。近百年来从未间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无数的社会实践业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决定一切的理论的确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李大钊主张的“人心改造论”、“道德的革命”也在世界范围内的无论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体制的国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报纸编辑的李大钊,能在接受和传播新的哲学思想的开始,就能发现并弥补其不足,突出体现了他对于新的哲学思潮内涵缺陷的包容性,也体现了他作为当时著名编辑勇于承担对广大新闻受众传播新事物新思想的崇高责任。
(三)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反对将真理绝对化
报纸编辑是报纸的“头脑”和新闻传播的把关人,其编辑素养和知识素养直接决定了新闻传播内容的格调和方向。李大钊作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世界观和知识储备以及他对于科学的严谨态度决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最终也才决定了新闻受众通过报纸杂志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
李大钊从他特有的新闻素养出发,指出马克思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1](p15)。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后期的西欧,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在当时的实践中形成的,欧洲产业革命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因此他主张,既不能希图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1](p15)。他说:“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时代的环境就是了。”[1](p15)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初期,李大钊始终以实事求是和科学的态度对待他所推崇的理论,一方面,包容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客观冷静的新闻传播的思路是当时其他的报业领袖所不具备的,而正是这种客观冷静的少了对新生事物的狂热和盲目崇拜的文章,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多了理性少了歪曲。
综上所述,李大钊作为报纸负责人、新闻杂志编辑、引进西方哲学思潮的传播者,他的新闻思想的包容性特征全面地体现在他的新闻活动和革命生涯之中。这种富有现代感的新闻理念,不仅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界和新闻界具有重要的先锋性,即使用当今的新闻观念来分析,也还同样显示着科学而严谨的专业性新闻理念的色彩。同时,李大钊饱含包容性的新闻理念无论对于当代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还是新闻传播实务操作都具有深刻而广泛的指导意义。研究李大钊新闻思想的包容性特征,不仅是现代新闻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李大钊整体研究的需要。
[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
[3]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胡文生:走进胡适 向西方学习[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阎稚新、李善雨、裕声编著:李大钊与中国革命[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
翟金霞(1985—),女,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