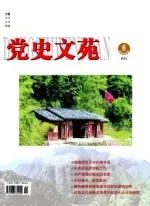从《新青年》看中国人革命思想的转变
徐 目
(吉林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12)
《新青年》作为一部综合性的月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可以称其为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一代名刊。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最重要的理论阵地,它的创建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提供了很好的舆论宣传,它所开辟的“马克思研究号”发表了以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以及苏联革命的文章。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原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是“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一、《新青年》产生之前的中国人革命思想
《新青年》产生之前的新闻传播刊物,可以概括为以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发表新思想、新文学的天下。这些前一时代学人所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源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对国人革命的方向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对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应同时看到,当代思想史进入到“五四”阶段时,这些老一辈人物的思想已成为旧时代的产物。
康有为与章炳麟两人可以说是占据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中心地位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二人的文章著作、泼墨挥毫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随着历史的推进,以康有为、章炳麟为代表的思想策略已成为落在时代后面的陈旧思想,成为保守的象征。康有为提倡孔教的至高无上的价值,与当时“打倒孔家店”恰恰是针锋相对、不符合大众主流的内容;而章炳麟反对白话文的运用,主张习读古经,也是与时代脱节,违背时代大主流,和新思潮背道而驰的。至于他们二人之间只有少数人能够体会的津津有味的今古文问题的讨论,除了少数的专门学者之外,更是引不起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兴趣了,也因此逐渐远离了时代的大方向。
1902年初,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 《新民丛报》。通过阅读作为主笔的梁启超在 “论说”栏里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不难看出他执意 “新民”,而且在启蒙的逻辑构成上偏重于从国民与国体、立人与立国的关系入手。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政府之于人民,尤寒暑表之于空气也。”“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从这几句话里便能看出,梁启超认为国人的生存依仗的是国家的存在,每个个人所要思考的都应是如何能够使国家发展的更好,而不应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他认为有了“新民”,就会有“新政府”,就会有“新国家”,认为个人是为国家而活,不需要有为自己活的因素存在。“民”不但是工具,而且是新工具;不单是国家的御用工具,而且是社会的道德工具;不但是民主新政的手段,而且是救亡独立的手段。[2]从这种价值判断出发,梁启超进一步得出这样带有明显时代性的结论:“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3]梁启超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个人的自由是不重要的,贬低个人的价值、忽略个人生存的意义,一味只强调团体、社会、国家的存在价值,过度忽略人的意义。他的思想核心就是群体意识,他曾在《余之生死观》的文章中说:“人的个体物质存在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因为他是次要的,很快便会湮没无闻;真正可以依赖的是群体的集合体,因为在这个结合体中包含了每一成员的精神价值,成为一个永久的存在物。”梁启超甚至推论说,只要大我具有生命力,小我的生死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导致他们的革命思想不能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关键原因,也是给后代人以警钟并使之走上成功的革命道路的重要因素。
1914年春,《甲寅》在日本东京创刊。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在革命失败后的心理变化都通过文章在这个刊物上表现出来。在抵抗帝制、倡导自由的舆论能力上,它无疑是一支独秀。当时聚众于《甲寅》的有识之士有章士钊、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以章士钊为首的知识分子站在不同的视角对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新一轮的论证。在人权与国权的辩论中,章士钊表达出了个人权利优先于政府、国家、社会的观点。在他看来,思想自由是人的主动权,国家不应该去侵犯个人的自主权利。在《国家与责任》中,他说:“吾人有提倡为国家主义者,意在损个人以益国家此说之可取,亦是夫所谓损益之界说若何,若漫无经界,犯吾人权根本之说,余敢断言之曰,此伪国家主义也。此曲学之徒,软骨之士,奉为禽犊,以媚强权而取宠利者也。”[4]这一观点实际并不影响这些爱国人士对于保卫祖国利益的肯定,只是在保卫国家利益的同时开始思考变换革命思想方式,开始思考民主、开始思考人的价值。他作为《甲寅》主笔,提出这一观点绝非偶然。
二、《新青年》倡导的中国人革命思想
提起《新青年》的思想,就首先要提起陈独秀的办杂志的经历。陈独秀办杂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4年春创办的《安徽俗话报》, 《说国家》一文则是他关心国事民情的直接表达。尽管从这时陈独秀的文章中已能感觉到他对个人与国家间利益冲突的思考,但他此时还没有超越梁启超等人的个人与国家观念的革命思想。总观梁启超、章士钊、陈独秀的这一时期观点,不难看出,无论是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有没有国家思想,还是章士钊说国家思想是交易,抑或陈独秀说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他们都是从批评国人缺乏国家思想进行启蒙的[5]。如果陈独秀的思想只是止步于此的话,也不会有后来的可以说是改变国人革命思想本质的 《新青年》杂志了。陈独秀的国家观念是层层递进的。如果说在梁启超的文章思想的影响下,陈独秀在 《安徽俗话报》上的言论属于典型的国家至上型的话,那么在章士钊主办的 《甲寅》上提出观点中所体现的则是属于民主思想的范畴。循着陈独秀在主持 《新青年》时期,也就是1915年至1919年间的文章,不难看出他关于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思想脉络。
如果说梁启超的群体主义思想是已被大家明确抛弃的旧时代思想的代表,章士钊所提出的立国观念则过于程序化的话,那么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青年》时代,陈独秀的价值取向则有了全新的跨度。与梁启超强调个人的义务相呼应,陈独秀关心的是这个大社会、大国家、大团体是否能够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一个能够发挥的平台,能否保障个人的自由与独立。如果假设国家不能保证个人利益的存在,那么个人就有权利去表达自己的声音、发表自己的意见、去争取人格的平等。他甚至在文中这样告诉国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6]巩固个人利益就是不为传统世俗所束缚,“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这里,陈独秀就明确地寻找到了自己的思想定位,这也为他以后创办《新青年》杂志明确了思想定位。他此时已经意识到个人在为国家存在谋取利益的过程中所能够起到的巨大作用,不再一味的强调国家的利益,而是以在国家谋求利益发展的同时,考虑到个人的利益的保障,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来发展二者的利益。因此,他在《新青年》中提出了个人主义为本位,就是要冲破社会和家庭的罗网,反对传统的封建伦理对个人的钳制。
陈独秀明确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定位,也就明确了个人与国家关系之间的基调,从而也就有了个人本位与开放世界观念的紧密结合。在他笔下,人应以理性战胜情感,有独立思想和判断能力,不为身处的迷局所困扰、所蒙蔽。固然,《新青年》初期会存在不同的声音、会存在标新立异的新奇观点、会存在各方质疑不解的声音,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关系定位确定为主编陈独秀这样一个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基调上。这个观点可以从《新青年》杂志上其他同仁文章中看出。
论及《新青年》及其同仁,除却上面重点提到的主编陈独秀,还要提到胡适。而论及胡适,其思想火花的最重要处也可以说是在于他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在他看来,“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是一个基本常识,但他在两者之间确有着个人优先原则:“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催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单独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7]同是在该文里,他把家庭、社会国家对个人的催折、腐败、黑暗一一加以分析,他将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系置于一个对峙的层面上,他的意思极为浅显透明:反对他们借着“公益”的名誉去骗人钱财,害人生命,作种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当然,在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也不免有失偏颇,但在过去的那个时代,也是为革命思想指明新道路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启迪。
在《新青年》同仁中,还有一位活跃于《新青年》上的自由主义者——高一涵。应该说,他是《新青年》杂志上论述国家与个人关系最为深刻有力的一位。他旁征博引,详细论述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主张在传统的社会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所谓个性,所谓自由,皆被一种依附性关系理论所取代。而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独立自由与平等必须建立在契约伦理关系之上。因此,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要一改传统的伦理关系。高一涵强调:“国家者,非人生之归宿,乃求的归宿之途径。”在他看来,小己人格不能被侵害,否则“互相侵没,皆干惩罚”[8]。
再来看看周作人,如同我们对他的著作名称如雷灌耳一般,他一加入《新青年》队伍,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文学天才和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周作人的“改良人类的关系”,也是说要置换个人与类群、国家以及社会的关系。他在文中说到,“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9]。这样简单的话语却代表着有深刻意义的革命思想。个人都是有其存在索要追求的利益,个人之所以存在,之所以要为革命奋斗,在于革命成功,国家利益的保卫能够使得个人完成自己的利益,找到了二者的相同点,才能够确保革命的成功。
作为一本新闻思想传播的月刊杂志,《新青年》可以称之为思想传播的典范,为广大受众带来了正面的思想引导,起到了积极向上的引导作用,并且能够将革命宣传思想传播至人们内心,形成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这是其作为新闻传播媒介最成功的意义所在。
作为革命思想宣传刊物,《新青年》的创刊加速了一个时代的过渡、转变。它不仅仅是一部在国难民伤的情况下,向身处水深火热情境下的百姓传播外来进步思想的文化宣传刊物,更是一部在时代转折点上,带给国人对革命以重新思考的精神慰藉。它由具有新思维的进步人士,包括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时代的佼佼者以全新的思考方式来重新定义革命的意义、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成果。对五四运动甚至整个时代的革命思想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最伟大的意义在于摆脱过去一味强调国家利益的陈旧思想,倡导个人价值提升,意识到个人价值得到实现,才能更好地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更切实际、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更能够贴近中国人思想的革命道路,使革命的意义现实化,更加坚定了中国人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
[1]梁启超.《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
[2]张宝明.《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199页,2007年.
[3]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新民丛报,1902年 5月 8日.
[4]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 1卷 8号,1915年 8月 10日.
[5]张宝明.《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202页.
[6]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 卷 4号,1915年12月.
[7]胡适.《易卜生主义》.新青年 4卷 6号 1918年 6月.
[8]国家非人生之归宿,青年杂志,1卷4号,1915年12月15日.
[9]人的文学,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