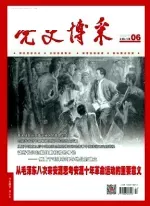青年毛泽东圣贤救世思想与儒家传统教育
王 垒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广州 510500)
青年毛泽东圣贤救世思想与儒家传统教育
王 垒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广州 510500)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的经典,就是整个社会统治思想的体现,是既高高在上又普遍深入的绝对的精神文化权威。身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传统文化氛围深厚的中国社会之中,虽然当时的毛泽东已是一个具有相当强烈反抗精神的少年,但他还并不能摆脱这种儒学绝对精神权威的支配和影响。关于青年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知名学者汪澍白先生著有《传统下的毛泽东》一书,富有启导意义。[1]笔者于2010年曾撰《儒学渊源与毛泽东的文化选择》一文,对毛泽东与儒家文化的深刻相关性提出了一些基本认识。[2]毛泽东在整个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以儒家文化精神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教育是系统的、全面的,与之形成了难以割舍的精神联系,并对他的人格气质、价值理想、道德理念、审美情趣的形成都有相当深刻的影响,而在他此后毕生所从事的事业中打下了传统儒家文化这一道道深刻的烙印。这一方面,从青年毛泽东毕生强烈的圣贤救世思想中尤其突出体现了儒家传统教育的深刻陶冶。
一、浸润于传统儒学教育中的毛泽东
从9岁起[3],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在韶山先后读了6年私塾,而在8岁前寄宿外婆家中,也已多次旁听过外家私塾的课程。他在私塾里所读的主要就是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这一类传统儒家文化经典。少年时期的这一段求学经历,给了毛泽东毕生以非常深刻的影响。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对少年时期求学情况,仍有很清晰的追忆。他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4]他当时在私塾写的文章,今天已寻觅无踪。但是,那时毛泽东“很相信孔夫子”,则是连他自己都非常明确的。事实上,他青少年时期的思想的确是深刻地体现了儒家文化特质的影响。他后来在第一师范就读时期留下来的几篇著作,言必称孔孟之处,所在多有。如发表于《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一篇之内,即征引四书、五经达八、九处之多。而他读德国泡尔生所著而由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时写的《批注》,所运用的哲学术语,如“良知”、“良能”、“尽心”、“知性”以及“浩然之气”等,就大多出自《孟子》一书。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子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5]这就表明,他那时是强烈指望着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1920年4月,毛泽东为驱逐张敬尧事从北京前往上海活动,特意绕道曲阜和邹县,拜谒了孔孟的故居和陵墓。他后来回忆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一条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6]
少年毛泽东崇尚孔孟,虽然他早在私塾读“经”时,已经萌发了许多“异端”思想。1906年在井湾里私塾读书,他已具有相当的自学能力,喜欢阅读被塾师视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小说。这些小说,人们通常认为即是“异端”小说。然而,这些所谓“异端”小说,与其说是儒学的异端,不如说是儒学的普及性通俗读本,还更合乎实际。因为其中所宣扬的旨趣,与儒家正统观念固有一定的差异,但细究其实,所谓“异端”小说与儒学经典,同样倡导以忠孝为本的价值追求,两者层次有异,本质实无差别。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除了要读当时称为“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史地课程之外,还是照旧要课读儒家“经书”。其时,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尧舜、秦皇汉武的业绩表示仰慕,也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在东山学堂期间,毛泽东还读了表兄文运昌所赠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其中有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这一时期,毛泽东已身怀强烈的救国救民抱负,正需要寻找思想上的导师。于是,便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康梁力主变革传统社会,却与传统儒家思想血脉相承,有着无法割断的历史联系,传统儒家文化精神对毛泽东的影响,比如变化日新、“大同”理想等方面就更多是通过康梁这个中介而展开和实现的。
后来在湖南一师求学,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则是杨昌济和徐特立两位讲授伦理学、修身等课程的教员。杨昌济治学融中西于一炉,然就其主要倾向上看,居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中学”。而在“中学”中,他既深研程朱理学,又特别重视以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儒学经世的文化传统。从程朱陆王、王船山、曾国藩到谭嗣同,他们所力倡的心性之学、独立品性、经世致用以至冲决网罗的精神,都是杨昌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与组成部分。杨昌济执教一师,又通过言传身教,把这些文化精神传统悉心传递给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辈新人,为他们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创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学说体系,提供了相当丰厚的思想养分。
杨昌济在湖南一师讲《伦理学大要及本国道德之特色》,采用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课本。但是,他“所讲不限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7]在中西两个学术渊源中,杨昌济显然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且对宋明理学尤为推崇。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自然深受乃师的熏陶。他在一师读书时,与蔡和森、张昆弟等经常讨论的就是宋明理学。他精心研读过《近思录》、《朱子语类》、《小学》等书,对朱熹和王守仁每每衷心钦慕。在与黎锦熙、萧子升通信时,他不厌其烦,多次征引朱熹语录,并加以申论。当年毛泽东游览朱熹讲学遗址时,还情不自禁地发出过“千载德犹馨”的赞语。
二、独得“大本”的圣贤人格和舍我其谁的救世情怀
青年毛泽东认为,“天下之生民备为宇宙之一体”,而由于各人心中所具之真理“有偏全之不同”,品位就分不同层次。“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5]在这里,他把是否探得“大本大源”看作是上智下愚的标准。
在《致黎锦煕信》中,毛泽东对这种圣贤创造历史的观点作了更为系统的发挥:“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5]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青年毛泽东认为真正探得“大本大源”的只有“曾文正”。曾氏以毕生卓越的文章事功,终获清廷赐以“文正”的谥号,他素崇孔、孟、程、朱之学,以“转移风气而陶铸一世之人”自命,在学术上固然无大建树,但却善于将程朱义理与现实斗争相结合,使之成为护卫传统伦理纲常、镇压太平军的精神利器。因此,他历来被士大夫们尊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儒门“完人”。杨昌济曾反复研读过曾国藩的著作,手抄其《求阙斋日记》。1915年4月5日,杨昌济与毛泽东谈心以后,还专门在日记中写下寄予这高足之殷切期望:“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7]。
早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毛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尚收藏有清光绪年间传忠书局木刻本《曾文正公全集·家书》的第4、6、7、9卷,每卷的扉页上都有毛泽东手书的“咏芝珍藏”。而在杨昌济的教诲下,青年毛泽东更以虔敬的心情重新认真全面地研读了曾国藩的生平著作,写过许多批注和笔记。如《讲堂录》中,就有一些曾氏语录。还记下了曾氏《圣哲画相记》中的三十二圣哲,并抄下曾氏所倡导的赖以立身行事的“八本”,奉为生活信条。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信中,更极口称赞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尽抢四部精要”,“孕群籍而抱万有”。读此书以通经史子集,可“察其曲以知其全”,“知其微以会其通”,“守其中而得其大”“施于内而遍于外”,[5]故奉之为国学津梁。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当他把曾国藩对比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历史人物进行衡量时,便坦然断言,独有曾国藩抓住了“大本大源”。对被时人奉为“立德立功立言”的楷模,古今第一完人的曾国藩,斯时毛泽东所传达出来的衷心倾慕之情,溢于言表。无疑,曾氏所取得的文章事功,并“圣贤”(修养)“豪杰”(事功)于一身,其所达到的“完美”境界,也就是青年毛泽东所努力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曾国藩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考究事实、多思多算、经世济民的务实传统,的确也深刻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
青年毛泽东热切地期待圣贤出世,担当起拯救“小人”的重任。毛泽东坚持传统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他说:“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陷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5]他觉得圣贤不应该独善其身,而应该以慈悲为怀,尽力把广大群众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对穷苦百姓的苦难的深切同情,不断驱使青年毛泽东强化舍我其谁的救世情怀。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恭录了宋儒张载的著名格言:“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录与《张载集》和《宋元学案》略有异文),并进而对“为生民立道”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指出“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5]青年毛泽东坚决反对君子置整个社会以及黎民百姓的苦难于不顾,去追求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他对君子的期待,也是对自己的要求。而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总不能得到解决,民众苦难难见解脱,就不断强化了毛泽东舍我其谁的救世情怀。
[1]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2]王垒.儒学渊源与毛泽东的文化选择[J].党史博采(理论版)2010(3).
[3]通常认为毛泽东从8岁起开始入读私塾,此处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见该书第2页“1902年九岁”一节,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1968.5)[M].武汉:武汉造反派1968年编印.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6]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7]杨昌济.达化斋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王垒,广州体育学院社科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