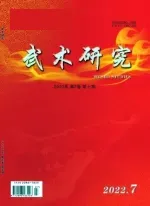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发展之路的历史探究
杨 卓
(陕西教育学院体育部,陕西 西安 710100)
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发展之路的历史探究
杨 卓
(陕西教育学院体育部,陕西 西安 710100)
文章采用历史文献、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术进行百年回顾。主要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转型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学术改革关系进行探讨,试图从中发现问题,寻找规律,为当代民族传统体育的学术重建提供必要的历史经验和理论基础。
民族传统体育 体育学术 历史探究
19世纪以来,由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跃居主要地位,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环境与条件下,爆发出探索真理、争自由,求解放的新的爱国激情.在体育文化方面出现了“土洋之争”,从而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改革。上世纪80年代民族传统体育又经历了一些新的变革。进入21世纪,当代社会转型促使多个传统的文化模式失范,并要求传统文化及时进行自身改造并重塑自己的范型,和积极主动地实现文化范式转型。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如何重新认识民族体育的传统、打破传统,并重建新的传统,建立新观念、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只有创新传统,才能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求得生存,真正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转型。
1 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百年回顾
民族传统体育的改革与发展,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早在清末,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近代体育。首先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教育中,开有包括武术在内的体育课。梁启超培养“新民”教育中大力提倡武术;谭嗣同在宣传“动静结合”的传统体育方面做出努力[1]。可以说清末的民族传统体育改革主要体现在,把民族传统体育部分地与西方体育相结合,并纳入了学校教育和培养“新民”教育中,这是民族传统体育为教育和社会服务改革新尝试。
当然,在近百年历史中,改革创新最盛的是“五四”运动。1916年《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革命开篇之作——《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从此开始,新文化运动也从此真正形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新文化运动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种种改革,并主张引进西方文化、观念和方法。一时间西方体育更是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提倡。如徐一冰1914年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建议在中小学革除兵式体操,增设西式体操、游技(包括球类运动、田径运动、儿童体育游戏等)[2]。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也提及西洋体育:“体育者……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3]。到1922年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从此,兵操在学校体育中被彻底废止,体育课与课外体育活动内容更加丰富,田径、体操、球类运动等得到进一步发展[4]。随着各界人士提倡“正当体育”,使体育走向正轨,这时武术的改革也同时进行。在徐一冰“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中有“高等小学中学师范亟应添习本国技击一门”的建议。1915年武术正式纳入学校的体育课程,随后全国的一些高等师范院校以及传播体育的各种组织相继开设了武术课,规定了授课内容、教学时数、学制安排。当时改革后的学校体育包括课内、课外两大块;课内由普通体操和兵式教练两部分组成,而课外则有国技(武术)。但在学校教武术的所谓体育教师则被看作是“打拳竞艺走江湖的”。即使当时有人写了一本《中国式应用武术新体操》的教材,该教材“种种式子,方法,差不多完全是‘美国化’”[5]。可见,当时对武术虽然已有改革,甚至有创新的意愿,但还是一种模索阶段,根本没有武术体系可言。
约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我国“洋”、“土”体育的争执非常剧烈。有些学者认为在国难当头,提倡“国术”,弘扬习武精神。陈敦正喊道:“中国固有的‘武术’——现在‘国术’;中国‘国术’的精神,即中国‘尚武’的精神”[6]。方万邦作为中间调和派出来调解道:“鄙意以为食‘洋’不化,和食‘土’不化,同是一样的错误”[7]。又有邵汝干说“建设中华民族本位所需要的体育,……是新中国体育的建设基础”[8]。可见,土洋体育两派之争各有各的理,谁也不服谁。
时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复兴民族体育和对其改革的呼声又高涨起来,如程登科提出“中国是否需要‘民族体育’的问题。强调“中国目前确实需要‘民族体育’,非有此不足以‘复兴民族’及取消‘东亚病夫’之讥”[9]。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民族体育的改革是出于强民救国的目的,也是针对西方学术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讥讽的回应,在体育强国、救国和发扬民族精神的社会背景下,一些人对中西体育进行了反思,1945年陆家珺对“现在西洋的体育,也和别的科学一样,渗透到中国来了,它是否合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哲学精神?”提出异议[10]。可以说,这是我们民族体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尽管战争导致研究资料图书匮乏诸多不便,但仍然出现了一时的学术勃兴。“中国武术史上第一次震耳欲聋地喊出了‘国术科学化’的时代口号”。这样一种学术背景和当时一批武术研究者唐豪、许禹生、王庚、张之江、程登科、蒋维乔等等在特殊时期艰苦卓绝的研究工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尤其是武术)学科迈向科学打下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国家领导人指出:“要加强研究,改革武术、气功等我国的体育项目”。但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初,传统学和民族学、民俗学的体育传统被冠以资产阶级学科被打入冷宫。虽然1958年至1961年,原国家体委组织过武术专家编写了教材,但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实践和学术研究几乎中断。约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民族传统体育(以武术为代表)经历了恢复、逐渐形成壮大,发展中兴的阶段。但是,民族传统体育如何改革?创新之路怎么走?民族传统体育的国际化依然作为主要问题存在。民族传统体育冲向世界,武术学科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学科,民族传统体育科学理论与方法,与西方体育、学术思想的融合等等,绝非短期内能够解决。不能否认的是,近百年来,特别是改变开放以来,有一大批学者,尤其是老一辈学者,在民族传统体育的改革创新方面殚精竭虑,作出不少贡献,虽然堆积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并非是前人没有努力,而是有历史的问题、社会转型的问题……,应该说,民族传统体育尤其是武术学科获得的成就是惊人的。
2 与时俱进,重建学术传统
无论什么文化和任何一门学科,它的改革创新必须迎合社会需要,与社会发展同步。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说:“如果你想了解一门科学是什么,你首先要看的,不是它的理论或发现,当然也不是它的辩护士对它的说法;你应当看的是它的实践者们做的是什么”。在现代社会,国家的政治、经济,人民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都在发生改变,各门学科都面临多元化冲击,创新是必走之路。所谓创新,通俗一点说就是“破旧立新”,要敢于打破传统,创立一种新的学术、新的文化传统。
传统在现代意义上是英文tradition的汉译,是指由历史沿革来的,具有一个外延最宽,反映客观事物最一般规定性的概念。民族学指出:“在原来那个‘共同地域’内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语言、共同体征、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的共同心理素质,具有较久、较强的稳定性,故不会很快就能轻易消失殆尽”[11]。可见,一般说的“传统”是指先人传给后人,前代传到后代的文化遗留。通常人们习惯于把“传统”与古老的事物等同起来,即将传统作为一个“过去”的时间概念来理解。事实上,如果传统仅仅是历史上形成的或曾有过的事物,处心积虑地研究传统就似乎没有必要。张岱年指出:“文化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耗散结构,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如果我们忘记了‘共时态’研究方法的有条件性,否认文化系统稳定的相对性,把结构分析方法变成一种静态的方法,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新陷入英美传统那样的形而上学思维,即把文化系统仅仅看成是既成事实的各种形态的总和”[12]。这就是把传统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过去我们把民族传统体育视为古代文化的“遗物”和历史的“回声”,当作静止的、僵死的东西是错误的认识。以探讨现代性及现代社会变迁著称的社会思想家吉登斯(Giddens)指出,现代性消解传统的同时重建了传统。这里最关键的词是“重建”。对传统的重建,并非排斥传统,也不是把传统进行重新组合。这一重建就是把现代性与传统的结合。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本身就是各个不同民族交融的结果。千百年来,又经历印度传统价值观念、精神心态和西方传统价值观念、精神心态的挑战、冲击,没有被外来的传统所同化、泯灭,失去其存在的根据,显示了强劲的生命力。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传统武术从蜿蜒的历史走来,虽屡遭封建统治阶级的严禁,但始终没发生传承的断裂,其积淀、绵延的活动样式、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循循善诱着无数昄依弟子,引起多少习武者‘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折腰苦求。传统武术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全息影像’,有着自身的内涵与内容”[13]。同武术一样,源于春秋战国、秦汉三国的赛龙舟、舞龙、舞狮、棋类……,均在历史上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发挥过巨大作用。然而,社会在变迁,时代在发展,在历史某个时代是进步的文化,在现代可能就落后了。比如传统武术中有七戒、八戒、武士须知、习武拜师等武林教规,还有赛龙舟抬神像和到龙王庙祭龙等繁文缛节也都不合时宜了。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人类各种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世界视野,使人们能够站在全球的立场上反思本民族文化模式的特点。吉登斯对这一时代特点进行了概括说:全球化是重新塑造世界的变革过程,是充满可能性和矛盾冲突的开放时代[14]。尽管我们强调要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德育、仁义、礼仪等思想)为现时所用,但古时武林中讲的“文以评心,武以观德”也有它的时限性。“道德具有一种时空的流动性。武德中某些属于特定社会内在伦理已不适应于时代,需要加以批判”[15]。在这个开放的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应该对当代民族传统体育做出新的学术解释,分析当前社会转型与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和需要做的事情,特别应该解释民族传统体育在国际对话中的失语、失声现象,充分利用知识信息资源,用一种开放的、全球意识的眼光来看待和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再开发,描绘出民族传统体育美好的发展远景。
3 民族传统体育学术之路
与其它学科一样,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该学科的学术资源。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同样是这样一种分层划分,其学术资源十分丰富,甚至是与其它学科有交叉、边缘的关系。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必须结合相关学科,使思想贯通、方法共享。以武术为例,其研究几乎无所不包——武术文化教育、美学、哲学、宗教、考古学、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文艺民俗学、高科技的信息通讯学以及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的路子越走越宽了,但面临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和更为复杂。换句话说,我们要准备接受西方和多元文化的冲突、甚至是挤压。这次中西体育文化论争与“五四”前后的“土洋体育”之争有所不同,应该说现在的中西体育论争是客观、理性和科学的,既对本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有更客观的认识、反省,甚至是批判,这就是在克服“自我中心主义”上的自觉。同时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客观评价,对西方文化的科学性、规范性是认同的,但学者们也越来越清醒认识到模仿西方,“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甚至是对本土文化的传承是危险的。站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东西方文化问题,就应该看到,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优长和短缺,善于取长补短,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对话方式,要多从别人的主体性来认识世界,从他人的视域来理解世界,这是大家一致认同的。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从学科发展的趋势看,各学科间的渗透与交叉是历史的必然,科学的、实用的研究方法自然被其他学科吸收采纳,从很大程度上说,研究方法是大家所共享的。研究方法历来受到高度重视。王国维强调“吸收西学注重逻辑的分析和注重思辩的综合方法,在学术研究上既能实证分析,又能理论概括,从而使传统学术臻于自觉之地位”[16]。梁启超认为“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新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17]。他又说:“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冯友兰在估价西方逻辑学在中国传播的作用时指出:逻辑方法的传入是“真正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18]。回顾民族传统体育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其理论脉络是清晰可见的。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理论的揉和,也就是以“田野作业方法”、“文献学方法”和逻辑学为主的研究方法。到80年代以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方法渐渐丰富起来,如武术学研究“除运用现代体育科学的相关学科理论,如人体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学、运动医学等人体科学的学科知识外,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广泛地运用于武术的研究”[19]。
总体上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方法多见的是分类法、归纳法和逻辑学方法,而真正运用民族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比较法、实证分析法还是少。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一二种方法,也可以多种方法,并不能说那一种方法就优于其它方法,更不能贬损一方而抬高自己。科学的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科学态度。其次,研究方法还应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特点,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而定,切忌那种几乎是不可更改地使用一种方法的偏好,或者是完全公式化的理论体系。一般而言,研究方法要提倡多样化,但多样化也有远近、亲疏的问题,就是说,与该学科研究相近的方法应放在重要位置,再推而远之,融通其它方法。
4 结语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社会变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每次社会变革都一次又一次地引发了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反思与改革,并在改革中得到学科的提升与发展。这就说明,作为一门研究本土体育文化的学科,必然要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真实问题。当前,我国正在发生一次更大的社会转型,并且在全球多元文化语境下,中西方文化发生了更激烈的冲突,与其它学科一样,民族传统体育的学术传统受到了新文化浪潮的冲击,再一次面临进与退的决择。我们常说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民族传统体育的学术之路要走出困境,首先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要进行改革与创新。过去那种过份强调自己学科独特性的思想,等于是画地为牢、自闭自封。因此,我们一定要从一种研究本土体育文化的学问中解脱出来,扩大视野,开放思路,与时俱进、融会中西,为创立一种科学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理论体系作出努力。
[1]王俊奇.中国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11-21.
[2]《体育杂志》第2期,1914.6.26,第1-6页.
[3]原载《新青年》第三卷第2号.1917.4.1.转引自《新体育》,1978(8):2-7.
[4]编写组.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19.
[5]《学灯》,1921(10):20-31.
[6]《国术周刊》第127期,第1页;第128期第2页.1937(10):27.11.
[7]《教育杂志》第25卷第3号,1935(3):29-38.
[8]《体育杂志》第1卷第1期,1935(4):5-6.
[9]《勤奋体育月刊》第4卷第1期,1936(10):2.
[10]《中华体育》第1卷第1期,1945(1):6-12.
[11]杨 群著.民族学概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4.
[12]张岱年,程宜山著.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
[13]周伟良.论当代中华武术的文化迷失与重构[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1):5.
[14]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M].译林出版社,2000.
[15]旷文楠等.中国武术文化概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199.
[16]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1册)[M].上海:上海书店,1983.
[17]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传[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34.
[1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中译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378.
[19]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编.体育科学研究现状与展望[Z].北京: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内部发行),2004:120.
On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History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 Science
Yang Zhuo
(P.E.Department of Shaanxi Education College,Xi'an Shaanxi 710100)
With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literature,logical analysis,the paper does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academica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 science,and mainly probes the relations of the change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the academic reforms of natinal traditional sport science,tries to find out the changing rules and find some historical expericencesand theory basis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national sport scienc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rot sport science historical study
G85
A
1004—5643(2011)08—0107—03
杨 卓(1983~),男,助教。研究方向:武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