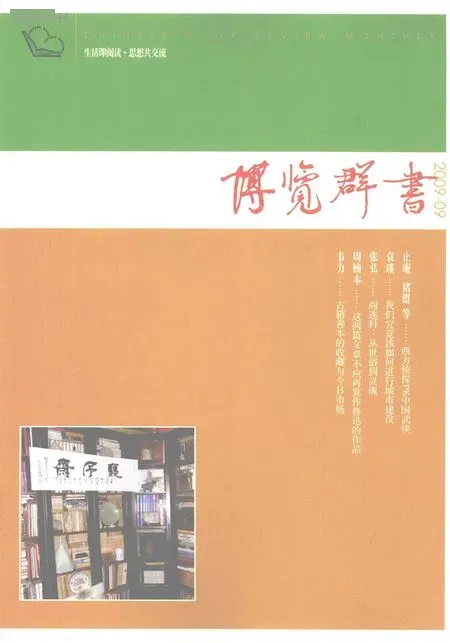叔本华与尼采的悲剧观
○赵 菲
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强烈地渴求进步与文明,是传统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但是,叔本华和尼采却对素以思辨理性主义著称的德国古典哲学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提出了与理性主义相抗衡的意志主义。一百多年来,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风靡漫延。
人生痛苦的描绘与解释
生存意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叔本华在他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文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世界是我的表象。”他对这个“真理”的论证是:一切自然界的现象都是意志的客观化,以至于人的身体构造也都是意志的产物。意志贯穿于人的生活的每一瞬间,即使睡眠时,意志活动也始终继续着。在他看来,这个意志是一种盲目的、永动不息的欲望和冲动。在一切冲动中,最根本的是求生欲望的冲动。这种欲望又以两种方式来表现,一个方式是自我保存,这叫“生存意志”,是最基本的。还有一个方式是繁衍后代,这叫“生殖意志”,生殖意志是把生存意志保存的生命在时间上加以延续,两者都是为了求得生命的存在。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人生悲剧的本体。因为意志分化出的欲望是无限的,满足无限的欲望则是不可能的。“在欲求已经获得的对象中,没有一个能够提供持久的,不再衰退的满足,而是这种获得的对象永远只是像丢给乞丐的施舍一样,今天维系了乞丐的生命以便在明天又延长他的痛苦。”(《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著,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P273)紧接着他说:“一切意欲都是由于需要,因此都是由于缺乏,也都是由于痛苦。某一愿望的满足便能结束了这个意欲,然而,对于一个已经满足了的愿望来说至少还有别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只要我们意识中充满自己的意志,只要我们沉溺于一堆欲望及其不断的希望和恐惧之中,只要我们是意欲活动的主体,就永远无法得到长久的幸福和平静。”(《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卷三)这就是说,意志本身意味着欲求,而任何一种愿望的实现一般都会经历无数的坎坷,这必然带来痛苦和烦恼,然而当一种欲望得到满足时,快乐只是短暂的,无聊会紧随其后,于是人生犹如“钟摆”,永远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摆动。
那么,知识的发展能消除痛苦么?不,“一个天才便要忍受最大的痛苦”。在叔本华看来,低等动物的痛苦少,人的痛苦多。智者劳心,越懂得思考的人,越会被自己的思索所累。
更可悲的是,这种痛苦永无尽期。受生殖意志的驱使,人们又要生儿育女,这就不断制造着新的痛苦与不幸。意志随着新的生命诞生而诞生,代代相传,延续、重复着旧路。在叔本华心目中,生命只有山重水复而无柳暗花明。对作为向往无限的有限的生命物——人类来说,死亡充满了悲剧色彩,这种必然的死亡结局会把每个人的一切梦想全部化为泡影。而事实上,充满欲望的人所追求的一切满足到头来全是空幻的。甚至有时候都不知为什么而活,正如“人好像钟表机器似的,上好了发条就走,而不知为了什么要走。每有一个人诞生了,出世了,就是一个‘人生的钟’上好了发条”。(《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P441)如此看来,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都只是过眼云烟,生命毫无价值,幸福只是转瞬即逝的梦幻。这就是叔本华所描绘的一幅充满痛苦的人生画面。
权力意志:尼采的悲剧精神
尼采与叔本华不同,他把权力意志当作世界的本质,他不满于叔本华把意志作为求生存的欲望,而忽略了其自主的要素。在尼采看来,“权力意志分化为追求食物的意志、追求财产的意志、追求工具的意志、追求奴仆(听命者)和主子的意志。”(《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P17)
世界上只有意志,只有一个意志征服另一个意志的关系。由于不同的人的权力意志在质和量上是不同的,因而,人生来就不平等。权力意志质优量多,即强者、上等人;权力意志质劣量少,则弱者,下等人。这种不平等的权力意志表现为强者统治弱者。他把这种权力意志一并用以说明科学、社会、艺术,乃至一切现象的形成。正如尼采所说,如果要给世界一个名称,对世界作出解释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
尼采也承认人生是悲剧,只不过这悲剧是兴奋剂。他认为叔本华在悲剧中只看到人生的徒劳、痛苦与虚无,而看不到旺盛的生命力之所在,这种悲观主义是错误的,只能磨灭人的意气;尼采认为只有经过悲观而达到乐观的人才是有深度的。他把悲剧精神定义成展现生命力的价值,悲剧的快感源自于强大的生命力敢于与痛苦和灾难相抗衡的一种胜利感,并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正如日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趣和乐趣;酒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不要失掉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
悲剧人生的解脱与超越
达者之境:叔本华的审美直观与虚无
我们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里,看到的是一幅意志支配人生的痛苦画面。意志仿佛是罪恶的渊源,它引起无穷的欲望,但又无法一一满足,给人类带来必然的痛苦。人要减轻以至于最终摆脱这种痛苦,达到无欲望,即内心的井然有序状态,就必须否定意志。
叔本华认为,真正的艺术是超功利性的,艺术的创造者和欣赏者都应该超出生存意志和功利主义的要求。在宁静的美的状态中,转移注意力,暂时忘却永无止境的欲求,忘却意志,获得短暂的平静,短暂的幸福,而艺术正是一幅令人陶醉忘我的图画。“这样,人们或是从狱室中,或是王宫中观看日落,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P275)这种审美境界,叔本华称为“自失”。
然而,通过审美所获得的解脱,只是短暂的,一旦曲终人散,必须要重新回到充满欲望的生活中去。痛苦的人生要想获得永久的解脱,只有通过对“意志的绝对否定”才能实现,即压制一切本能,磨灭一切激情,取消一切欲求,淡化一切感情,使身心绝对宁静下来,最终达到一种“无欲”的境界。叔本华说:“无欲是人生的最后目的,是的,它是一切美德和神圣的最内在本质,也是从尘世得到解脱。”(《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P275)要得到永久的解脱,就必须是生命意志自我扬弃。
在这里,自杀不是解脱之路。叔本华认为:生存意志的否定,不是说要消灭肉体来达到,因为这只能得到更大的痛苦。“自杀”这种自我对个体生存的毁灭,只能说明无法承受生存的痛苦,这反而是对生命意志的肯定,是愚蠢的行为。因为物自体——人种、生命和意志——一点也不会因此受影响,这就像一道彩虹,虽然维持它的水滴在急剧降落,但它依然存在。个体的死亡并不能终止不幸和斗争,只要意志还在人世,它们就会延续下去,痛苦依然存在。只有在意志完全听命于理智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
在叔本华看来,最好的途径是信仰宗教,过禁欲的生活来达到佛教中的“涅槃”境界,忘却现实生活,进入无物、无我之境。基于佛教教义,叔本华认为“涅槃”是一种在参透表象世界、看清万物的痛苦,让自己身处世间,却能冷静、清晰地发现、观察这些周围的事物,从而自觉地放弃各种欲望,不受意志所控,最终获得一种解脱,进而感到由衷的欢快,步入达者之境界。在那里,没有生死之别,一切意欲都彻底泯灭,绝无所求。无所求便无所缺,也就无所谓痛苦与苦难,随之而来的便是心境平和,怡然自得。
超越之境:尼采的酒神精神与超人
意志是世界的本质,如何超越意志带来的痛苦呢?尼采认为摆脱仅是在意志活动之外去看待意志,而超越则是在意志活动之中去体验意志本身。
首先,肯定悲剧艺术,倡导酒神精神。以审美的态度看待人生,那么人生就是一种悲剧艺术。人生苦难,然而人在与这些苦难抗争中,会感到生命的力量,体尝生命的快乐,这就是人生的悲剧美。尼采认为悲剧的实质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两种精神——日神(阿波罗)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对立和冲突。前者代表静穆的美,是人以冷静的理智观察世界的态度;后者代表生命力,是人创造世界、创造人生的生生不息的力量。理性和生命力合而为一,就达到了悲剧艺术的最高形态。悲剧的外在形象是日神,其内在本质却是酒神。而酒神精神的本意就是在抗争苦难中肯定人生,连同其所包含的痛苦与快乐,体尝人生的悲剧美。
其次,肯定权力意志,提出超人学说。尼采强烈抨击自苏格拉底以来的西方传统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鸦片式道德”、“奴隶式颓废道德”,提倡主人的道德。他有感于基督教对人的束缚,使人低估自己,导致人类失去存在的真实性,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新价值的创造者——“超人”的形象。到底“超人”是什么呢?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中说:“我告诉你们什么是超人。人要超越自身的某种东西。”“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超人”,他是有着酒神精神、健全生命本能、旺盛的强力意志、独特个性、生之欢乐的人,他是超越一切传统道德规范、处于善恶之彼岸、自树价值尺度的创造者,不为现代文明所累的未来王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著,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哲学思想的反思与启示
叔本华与尼采,犹如佛教的小乘与大乘。他们都悲观,但是,叔本华的悲观是完全的出世,否定人生,尼采却是出世复入世,否定人生然后又力图肯定人生。
叔本华的错误,是用非理性压抑了理性的作用,从而把人降低到同动物相提并论的水平,用悲观主义否定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导致了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而尼采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少数高贵者身上,终于把健全的本能和超越的精神视为这少数高贵者的禀赋和特权。
两位哲学家都用自己悲剧的一生,展示了现代西方人在传统价值崩溃时代的迷途之痛苦和探求之渴望。生命是人的自属本性,如何生活是每个人的自选结果,了解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对人们思考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所带来的启示必定会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留下深刻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