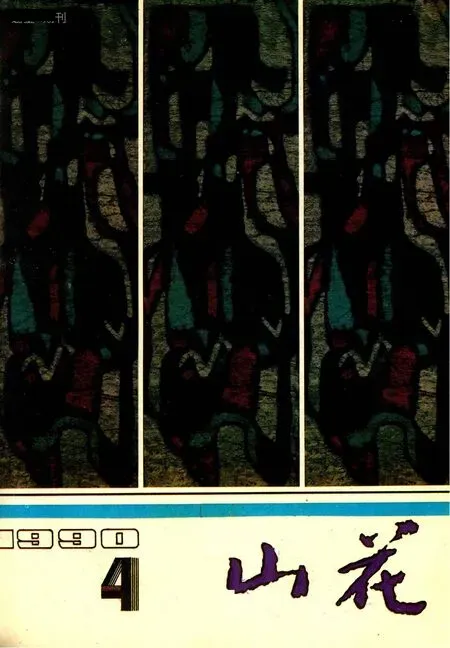鲁迅与沦陷区文学
申 勇
鲁迅与沦陷区文学
申 勇
沦陷区文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军事占领区的中国文学。其主要部分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文学时代结束,形成以上海、南京、武汉等为中心的华东、华中等南方沦陷区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优秀的爱国分子高举鲁迅的旗帜,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主张抗战救国。东北沦陷区和华北沦陷区的乡土文学写作,揭示了沦陷区人民真实的生存困境与不屈不挠的民族生存意志,延续了鲁迅开创的乡土小说写作传统,东北沦陷区杂文作家没有继续坚持鲁迅的写作风格,但其文学创作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也为抗日救国运动尽了最大的努力。本文探讨鲁迅与东北沦陷区文学关系,鲁迅与华北沦陷区文学关系,鲁迅与南方沦陷区文学关系。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东北沦陷区文学也由此开始,延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成就主要是小说和散文,整体文学风格雄浑、厚重,强调对原始的“力”的赞美,代表作家有萧红、白朗、罗烽、端木蕻良、骆宾基、山丁、秋萤、袁犀等。东北沦陷区作家的创作深受“五四”传统和鲁迅文学的影响。尤其是萧红、萧军1935年到上海后得到鲁迅的帮助,他们各处原长篇《生死场》、《八月的乡村》被编入《奴隶丛书》出版后,轰动文坛,更加深了鲁迅和东北沦陷区文学的关系。
在小说创作上,1937年移迟的短篇小说《山丁花》发表后,山丁写了《乡土与乡土文学》、《乡土文学与〈山丁花〉》等文扯起了乡土文学的大旗,他指出“满洲需要的是乡土文艺,乡土文艺是现实的”,称乡土文学为“描写真实”和“暴露真实”。东北作家对乡土文学的倡导扩大了鲁迅提出的“乡土文学”对东北作家的影响。鲁迅写过不少反映故乡风土人情的乡土文学作品,对青年时代美好的乡村生活的回忆和渗入乡村封建文化的批判,流露出强烈的文化意识。与之相比,产生于三四十年代的东北乡土文学作品,则洋溢着浓厚的民族抗争意识,烙印着鲜明的时代痕迹。现实主义是东北沦陷区小说创作的主潮。作家把普通人乃至社会最下层的人物,整体带入文学画廊,以乡土小说作为实践现实主义的文学样式和种类。文丛、文选派的作家山丁、秋萤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乡土文学”的创作主张,而且还与袁犀、移迟等人自觉地从事乡土小说的创作。《矿坑》、《风雪》、《雪岭之祭》等作品都是带有鲜明乡土特色和风俗色彩的佳作。在东北沦陷区作家中,与鲁迅精神最契合的莫过于萧红。萧红有意识地师承鲁迅的思想精髓和精神真谛,《生死场》中的时代的滞留与生存的麻木;《呼兰河传》中比死亡更可怕的沉寂,都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式的洞悉、深警。她的作品以觉醒者的高度暗合了鲁迅文学创作初衷,即“我的取材,多取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同时由于时局的残酷,东北沦陷区作家还经常运用鲁迅惯用的曲折、隐晦象征等曲笔表现手法。
在杂文创作上,鲁迅的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甸弊常取类型”[2],其坚韧的战斗性对沦陷区东北作家产生很大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古丁和李季疯。他们的杂文风格很像鲁迅,笔锋犀利,讽刺意味既浓且强,恶劣的现实环境使他们意识到:“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3]古丁的散文诗集《浮沉》受鲁迅的《野草》影响很大,面对黑暗的现实社会,以设喻和隐喻的表现手法,强烈地表现了与现实不妥协的精神。杂文集《一知半解集》和《谭》,文笔犀利,内容深刻,针对性强。《大作家随话》(出自《一知半解集》)针对不敢当在《满洲随话·文艺》一文中的提出关于在满洲会不会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的问题展开讨论,认为要当鲁迅似的大作家首先要当鲁迅似的大战士。
在鲁迅研究方面,山丁在《明明》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特辑上译出了日文的《鲁迅著书解题》,比较详尽地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和著述,为东北文艺界全面地了解鲁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萧红以散文笔法对鲁迅、鲁迅的小说及小说文体进行了新颖独到的评价。“鲁迅的小说的调子是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而鲁迅却自觉地和他人一起受罪。”对鲁迅小说的文体特征,她说:“鲁迅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如《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鸭的喜剧》等等。”[4]这些见解完全是“萧红式”的,其表述方式和语言都给鲁迅研究带来崭新的气息和资料。
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形成日本统治的华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文学正式启幕。华北失守后,大部分作家纷纷逃难,还有一部分作家留守在北平不愿南迁。包括周作人、钱稻孙、俞平伯、沈妻无、袁犀、梅娘等。在七·七事变开始的几年内,这些作家一直保持着沉默的态度,中止了所有的文化活动。到1941年这些保守沉默的文化人中的一部分作家受日本军阀及伪组织的威逼或利诱,成为了文化汉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周作人、钱稻孙等人。
在华北沦陷区文学开始的几年,华北文苑曾一度凄清。在日伪所办的《中国文艺》、《星光》和《艺文杂志》等刊物上,所发表的作品多是周作人及其弟子的小品和掌故类等作品。沦陷区作家出于对精神和生存的需要,不得不从艺术上取得慰藉,注重凡俗人生的写作。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谈到“饮食男女”作为在乱世延续中国文化精神的意义,在沦陷区文坛上产生了影响。在一些文学青年自发创办的《逆风》、《覆瓶》和《辅仁文艺》等刊物上,所载作品也多远离现实,并在艺术上也流于浅薄。1940年,从爱国文学青年中发出了“建设新文艺”的呼唤,要求改变文坛状况。此后,《晨报》、《新民报》、《庸报》等虽相继开辟文艺副刊,并有《燕京文学》、《国民杂志》和《妇女杂志》等刊物陆续问世,但这些报刊所发表之作品也多为见花落泪、看月伤心的闲逸作品。而这些创作是与鲁迅的写作传统相违背的,他从不赞成闲逸文艺,他主张的文艺是“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救的注意”。[5]直到40年代初期,1941年日本在满州发布《艺文指导纲要》,加强了对进步文学的摧残,关外作家遂陆续入关,华北沦陷区涌现了一批新作者,被称为“新进作家”群。他们对“乡土文学”的提倡,对“色情文学”的批判,改变了汉奸文学和闲逸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他们延续了“五四”的血脉和鲁迅的乡土文学的写作传统,并包含着民族主义立场和个人道德实践,带有反抗现实的意味。相比之下,较有特色和影响的是梅娘和袁犀等从东北入关的作家的创作和关永吉的文艺理论。关永吉是模仿鲁迅式杂文最下力的作家之一。他的《新文坛的危机》、《游牧、老爷、名士和文学家》、《谈旧帐与唱老调和就此打住》等大量杂文,批判了沦陷区文化界的颓废、堕落和庸俗,以文笔犀利健康著称于华北沦陷区文坛。关永吉提出“乡土文学”的要求,其动机和企图,是认为“乡土文学”是克服当时文坛堕落倾向的唯一武器,才拿这武器正确地认识现实、把握现实,而且在形式的内容上,要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和具备民族性的性格。从这些论述来看,在沦陷区的政治背景下,国民性、民族性、现实性,几乎就是乡土文学的代名词。沦陷区的乡土文学理论不仅仅只是继续了“五四”时期鲁迅等人乡土文学理论的传统,同时还在内容上有所丰富、深化和发展,这是沦陷区的文学理论的重要成就之一。更重要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沦陷区的乡土文学理论表明的一种对于现实的政治、文化环境的反抗意识,隐含着民族主义立场,具有抵抗性质。梅娘的作品体现的多为女性在战乱时期的悲惨命运,她代表作《鱼》、《蟹》等水族系列中,女主人公心理总在矛盾中。这些女性都受过高等教育,不甘于沉闷的现状、女性依附男人的地位。但根源于女主人公传统和现代意识的冲突,构成她们的性格上的怯懦。当面临最后一步时,她们没一个“负着子君的灵魂”出去,为些女性永不具备追求人生真谛的勇气,只能在懊恼悔恨里做传统家族的顺民。
抗战爆发后,新文学阵营几乎全部转移到国统区和解放区,于是通俗小说在沦陷区获得了宽广的空间和较大规模的发展。其中武侠小说界涌现出一批成就卓著的作家,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合称“北派五大家”。武侠小说对侠义的探寻,对文化的融汇,对人性的挖掘,尤其是白羽以写实化的风格开拓了“社会反讽”派的武侠小说,是对鲁迅社会批判小说的通俗演义和发展,以更大众的宣传方式在群众中传播反对封建的思想。华北沦陷区通俗小说还包括社会言情小说,代表作家刘若云、陈慎言的小说能引发读者对人性的情爱问题的思考,颇受读者喜爱,阅读量很大。
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之后,华中、华南也相继沦陷,形成南方沦陷区。但在文学贡献上则以上海沦陷区文学为其代表。上海沦陷后,大批“孤岛”文学作家纷纷流亡内地或海外。留在上海沦陷区的作家虽仅有柯灵、李健吾、许广平、许杰和张爱玲等为数不多的作家,但其作家数量与整体实力在大陆各沦陷区文学中仍居首位。这一时期,既有抗战文学,又有爱国文学,还有汉奸文学。在“孤岛”沦陷之初,留沪的作家用鲜血和沉默对抗日殖的暴虐和汉奸们鼓噪的“和平文学”,经受着民族大义的考验,故上海文坛曾冷寂一时。稍后,柯灵等留沪作家与爱国有通俗文学界达成默契,由柯灵接编并改造“鸳鸯蝴蝶”派刊物《万象》,使之成为留沪作家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
在散文、杂文创作方面,杂文创作的声势明显衰弱。议论性的散文,特别是鲁迅式的尖锐的政治、社会、文化批评的杂文,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杂文写作内容也发生变化,由大胆揭露和抨击敌伪的罪恶转为鼓励读者不泯生活信心、隐晦批判敌伪罪行。正如王予在散文集《见山楼什文·前记》中说:“杂文已被鲁迅先生写到最高峰。但是,需要杂文的时代没有过去,不过究竟不同了,我们必须换个写法。”上海沦陷后,“鲁迅风”的杂文作家们发生分化。柯灵等坚持不与日伪来往,先是隐居辍笔,以后虽复出却多事小说、戏剧等写作。周黎庵、文载道则堕落为汉奸文人,热衷于谈古忆旧的闲适散文。这时期写作杂文较多的作家是丘石木、何之、严谔声、柳枝等。比较适于生存的是“闲话”体的文字。胡兰成发表在《苦竹》、《天地》、《人间》上的《随笔六则》、《新秋试笔》、《关于花》等篇章,涉及文学、文化、哲学、政治、人生、人情世态各个方面,别有新意,发前蛤所未发。
在上海沦陷区文学中,其主要文学成就体现在具有独特的文体风格和描写、讽刺都市生活同知识分子的小说上,师陀、钱钟书等知名作家的创作代表了南方沦陷区文学的成就。师陀的《无望村馆主》、《果园城记》以农村文化背景深厚的“乡下人”视角,来探讨知识分子回乡时心灵的冒险,家乡时间滞后对知识分子心理造成的巨大冲击,在留恋感伤之情中隐含着否定和批判,与鲁迅小说《故乡》、《祝福》的“回乡”主题有异曲同工之妙。钱钟书的《围城》是剖析现代社会某一部分人类的基本根性,与鲁迅对国民劣根性批判形成互补。在此期间较有特色并影响较大的是张爱玲。鲁迅和张爱玲对现世人性阴暗面与劣根性揭批尖锐与犀利及其前所未有的笔墨深度是他们共同的特征。张爱玲于1943年以描写战时上海与香港两地洋场生活的《倾城之恋》而引起人们注意,其代表作《金锁记》又被称为“女性的情欲研究”而受到众多读者的追捧。苏青的《结婚十年》及其续篇,生动地展现了女主人公的矛盾心理——努力追求自立而又不自觉地寻求依附,拼命想抓住生活、享受生活而又下意识地渴望着安全保证。这是从家庭妇女向职业妇女转变途中的女性们的典型。对“五四”时期以来的妇女解放的主题作了新的开拓。同时也是继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对妇女出路问题的新的质疑。沦陷区和大都市的特殊环境,使张爱玲、苏青这类没有明显政治内容的作品得到了滋长的机会,也造成了特写时代女性文学在上海沦陷区的重要收获。
在南方沦陷区发生过这样一段插曲,1944年1月华中沦陷区岛田正雄在日文《大陆新报》上发表《民族文学的确立》里提到中国沦陷区文学的出路是“回到鲁迅”,章克标马上撰文《鲁迅乎》表示异议,以后岛田正雄又发表《民族家鲁迅》坚持自己的看法,在3月《大陆新报》召开的该报记者与日中文学名人的“中国文学现状座谈会”上,日本在华中沦陷区文艺办的负责人草野心平也发表了“提高(沦陷区中国作家)文学的精神,其方法是回到鲁迅时代”的意见。“回到鲁迅”的讨论争论主要是在日文报纸上进行的,也没产生什么实际影响。但也看出鲁迅对当时中日文化界的影响。
[1]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26.
[2]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
[3]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险.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92.
[4]聂绀弩.萧红选集·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
[5]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68.
申 勇,男,1971年1月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