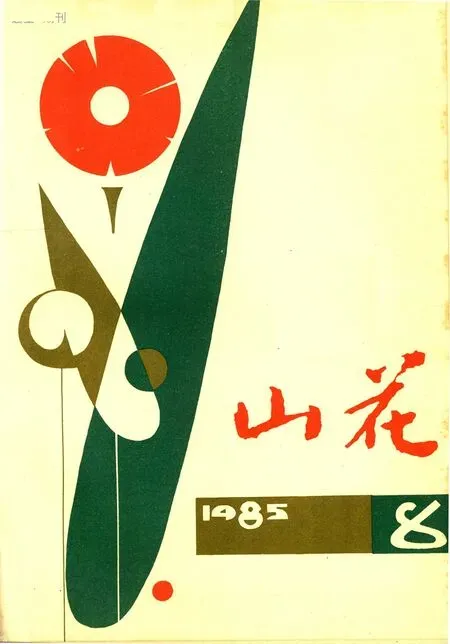尼玛的塑像(外一篇)
嘎玛丹增
尼玛的塑像(外一篇)
嘎玛丹增
距离尼洋河和雅鲁藏布江交汇处不远的地方,德木寺耸立在一座陡峭的山顶上。茂密的森林、草地和零星的民居包围着它。
下午的时候,天空和大地很安静。偶有微风路过,在柳树和经幡刷刷轻响一阵,水波样翻过山原谷地,草叶树木此起彼伏地涌向远方。黄土便道凿在山崖上,汽车上下都很惊险。我原本应该从小路上爬上去,那样更安全。当地信众就是通过弯曲的小路,将酥油和朵玛源源不断送进了寺庙。高原的阳光太灼热,黏在皮肤烙铁般滚烫,于是选择开车,没想到,陡峭的山道,让我的四肢僵冷。汽车惊叫着向上攀爬,我的额头冷汗淋漓。因为贪图安逸的一念之差,我把自己送进了进退维谷的陷阱。
德木寺依然在高处。亮晃晃的阳光下,依稀可见房顶上刺眼的经幡,以及四周摇摆不定的树木,看不清寺庙的表情。
尼洋河在山下,静静地穿过深秋的丛林,河谷滩地草黄一片。雅鲁藏布江在更远的地方奔跑,无声地追赶着洁白的云朵和连绵的高山。远远看去,雅鲁藏布江河岸沙尘弥漫,要不是对西藏早已有所认识,很容易把飞舞的沙尘错误地诗意成云雾。
可能是神谕。尼玛措的出现,极大地缓解了我的惊慌。这是一个穿着袈裟的孩子,暗红色的袈衣外面,披着一件沾满油渍的灰色夹克。他笑嘻嘻地说,人家大卡车都能上来,师傅的手艺不行。尼玛措站在道路前方,指手画脚地指引汽车。我得以安全地到达山顶。
之前,我对德木寺的行程没有计划。我沿着尼洋河谷南岸迷人的秋色,信马由缰地到了水泥路的尽头。路上,遇到了一群又一群的苯教(藏地原始宗教)信徒,他们背着重重的行囊,环绕苯日神山朝圣转山,三步一磕或缓慢行走,一身尘土,满脸喜悦。不时有人友好地用手臂向我挥舞。人们转山,给我的直觉就像散步一样,轻松而愉快,尽管转山一周需要两天。就在水泥道路尽头,在牛羊、骡马、猪和鸡狗频繁出没的米瑞乡街头,一位满身酥油味的藏族大哥,用不太流利的汉语告诉我:到了米瑞,就应该去德木寺。我和汽车,毫不犹豫地走向了通往德木寺的黄土路。
尼玛措打开寺院侧门,回头招呼我进去的间息,我已经顺时针绕着寺庙经筒,转经一周。这并不表明我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只是敬畏,一种对高原人生永怀的崇敬。在追求心灵和平高于一切物质存在的青藏高原,我的行走,对于心灵就像一次散步。信仰的缺席,已将我对物质世界的迷恋画地为牢,一次次与真理擦肩而过。门匙高出尼玛措许多,他踮起脚,小手放在门扣上,脸上充满了真实暖人的微笑。
这是一个孩子!14岁,单纯可爱。上到小学五年级,去年被家人送到了德木寺。从此,尼玛措将与经文和酥油灯相伴一生。如果尼玛措是我的孩子,我会送他到寺庙吗?这种假设很无聊,也很残酷,就像我沉迷于物质世界的灵魂,永远不能完全接近真理一样残酷。
在德木寺门前高高的石阶上,我很想抱抱尼玛措,就像一个父亲,和儿子久别重逢那样。突然出现的柔性,让我手足无措,男人那种外强中干的思维惯性,阻止了我的冲动。我甚至打消了拍一下尼玛措肩膀的念头。再说,在藏区不能随便拍人肩膀,那是禁忌。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像有无数的目光躲在暗处,心怀鬼胎地注视着我。事实上,我才是我的鬼胎,那是世俗生活附着于心的厚重蒙尘。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能由心而为。习惯和经验,魔咒般导演着我们的言行。
如今的德木寺很小,佛堂内除去供奉的佛像和护法神像,以及历世德木活佛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圣物,狭小的大堂内只能容纳十多个人。室内光线昏暗,酥油钵里燃着四芯灯火。虽是充满神性的场所,但我的身体多少感觉有些阴冷。喇嘛们此时在户外劳动,砍柴、种地或修补房屋。简易的木凳上,放着厚厚的袍子,喇嘛诵经的时候会披上它,以抵御高原地区漫长的寒冷。看到空空的座位,我不止一次地想:一个孩子,生活中没有键盘和卡通,在诵经习法的白天黑夜,该如何抵抗漫长的寂寞?要从一个自由任性的孩子,成为辨经认证的格西或堪布,又该经历多少孤独冷清的岁月?尼玛措在我前面,不时伸出小手牵引着我,生怕我在光线暗淡的佛堂内摔倒,并轻声地教我辨认塑像和唐卡中人物的身份。
所有的迹象表明:这是一座香火冷清的格鲁派寺庙,人们已经很难从眼前的情形看出它在历史上的宏大和繁荣。在直线距离这个地方22公里的鲁朗镇,我去过德木寺最初的遗址,那个曾经被五世达赖称为神仙居住的地方。鲁朗,距离南迦巴瓦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很近,也是从318国道到达能够观赏景区最近的地方。当年,四世德木活佛和五世达赖从鲁朗进京,清朝政府正式确立了五世达赖在西藏的宗教和政治地位,政教合一的历史由此开始。而德木寺在林芝地区的地位和影响也因此节节攀升,从昌都八宿到工布江达,曾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庄园。鲁朗德木寺毁于波密王朝的刀剑和火把之下。在于今德木寺周边的米瑞乡,曾经是规模庞大的德木寺旧址,1950年发生的8.4级大地震,又把一切都毁掉了,只有名字被保留了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德木寺,是历史上的第三次重建,那是十世德木时期的事情。于今的德木寺为何如此冷清?其间缘由不得而知。
显然,尼玛措不能给我任何答案。洛桑主持也许知道这个答案,但他不会轻易告诉我。我跟着洛桑喇嘛艰难地爬上了二楼经堂。这里的通道和房屋一样窄小,和我们在西藏其他地区参观的很多寺庙都不一样。经堂内供奉着格鲁派历史上诸多的圣人圣迹。洛桑主持不懂汉语,我在德木寺见过的几个喇嘛都不懂汉语,而英文又奇怪的流利。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状态?尼玛措充当我们的翻译。我和洛桑的交谈,就像在街边随便碰到一个陌生人的交谈一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二楼的光线更加黯淡,荟供台上也只有一盏酥油灯,要想看清那些精美塑像和唐卡的细节,只能借助洛桑临时打开窗户后涌进的光亮。下午的阳光很干净。站在窗口,可以俯瞰平坦辽阔的尼洋河,以及苯日神山色彩绚丽的秋天山林。这样的风景,可以把人惊呆。我不知道,德木寺的喇嘛们,是不是经常站在同一个地方,怀念起山下的生活?经堂内的唐卡塑像,他们凝结的表情,为我们保存了足够多的往事。靠窗的地方,摆满了喇嘛们泥塑的小神像,它们站在温润的阳光下,散发出神圣而迷人的光芒。这是令我的镜头最着迷的光线和物质。师傅,买一个塑像嘛,50块钱。尼玛措在身边重复着说。洛桑主持站在窗前,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和尼玛措。其实,洛桑主持这个时候的心思我明白。作为德木寺的物质管理者、精神修炼者和传导者,扩大寺庙规模,提高喇嘛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是压在他的肩上的沉重责任。在清修的道场,佛像和菩萨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但修行者必然需要饮食,而这一切,大多源自信徒和旅游者的供养。
尼玛措已经明白这个道理。那些小塑像,就是喇嘛们制作的结缘物、加持品,当然在某些人眼里,它们只是不折不扣的旅游纪念品。
走出佛堂大门时,我跪在油光发亮的石头地面上,举着相机,对准大门上的黄铜门环拍个不停。门环上拴着一条哈达,已经变色,在逆光下显影的质感,深深震撼着我麻木的感官。尼玛措靠着木板墙,眼睛透亮,大惑不解,他先是抿嘴微笑,最终朗朗地笑出了声。在尼玛措有限的经验里,我无疑是一个来自现代都市的疯子,拍什么不好?总是对那些腐烂和陈旧的物象痴迷失语。
洛桑和尼玛措领着我,参观了德木寺所有可以参观的地方。有几个喇嘛和当地信徒在后院劳动,低矮的僧舍房檐下堆满了整齐的柴禾。尼玛措向我介绍罗布喇嘛时,充满了孩子式的机智和幽默:这是罗布,罗布大师,嘿嘿。罗布带着近视眼镜,首先笑弯了腰。德木寺顿时笑成了一团。天空、风铃、经幡、草木也跟着笑出了声。这是我熟悉的笑声,连矜持的洛桑主持也笑了。一个孩子的存在,给德木寺带来了快乐。尼玛措很容易把人带到生活现场,让人想起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离开之前,我才拿出一些银子给尼玛措:我请几个小塑像,但我不带走,就放在你们的经堂。尼玛措即刻将供养交给了洛桑主持。洛桑喇嘛再一次笑了,显得异常热情主动,要同我合影留念,并亲切地把右手放在了我的肩膀上。我知道,洛桑喇嘛在为我加持。此时此刻,我满心欢喜,这是我最愿意领受的精神抚慰。
尼玛,太阳之意,措,在藏语里意为湖泊。尼玛措,太阳湖。我在林芝地区米瑞乡德木寺恩遇的阳光雨露,是一个孩子和洛桑主持给我的。于此,我期待已久,行走在这块神谕的土地上,德木寺保管的时间和精神,才是我试图接近的源头。
上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德木寺草木葱郁的院落,看见尼玛措跳起身子,不断地比划着踢球的动作。这个动作告诉我,作为孩子的尼玛措,在德木寺很快乐。作为喇嘛的尼玛措,孩子,你快乐吗?
如果再去德木寺,我会送尼玛措一个足球。
洛桑主持背对着我,锁闭了寺庙的后门。十分钟前,我经过它,站在孤零零的山顶上,观赏过美丽的尼洋河和雅鲁藏布江,尼玛措、洛桑主持和罗布喇嘛,笑容满面地陪同着我。
下山的时候,我再也没有感到惊慌。
我非常愿意假设,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洛桑喇嘛应该是尼玛措的父亲。
哨楼湾
秋天的这个傍晚,哨楼湾的炊烟,在我眼里,就像挂在博物馆墙上的一幅画。
如果可以假设,去掉公路两侧排着长队的水泥电线杆和横七竖八的线缆,我所靠近的乡村,正是我想继续的行程。
哨楼湾是存留在川东地区为数不多的老宅之一,典型的大户人家建筑式样,一楼一底,当地人习惯称其为“走马转阁楼”,它最初的主人范绍增将军已经作古。据说,范将军年幼的时候,很是顽劣,年少时就加入了袍哥会,曾经有过因违犯帮规而被活埋的历史,在死亡边缘转身重回人间,多亏了他威风八面的爷爷。一个帮会中年龄最小的孩子,尽管早熟,很多时候还是不懂那么多规矩,所有喜好完全服从天性。直到后来成为川东袍哥头目,有过抗日爱国的光荣历史以后,方知世事无常,规矩甚多,解放前夕率部起义,最终和平民站在了一起。范将军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把这座庞大的房子捐献给了政府,如今居住着近20户村民。这样的一处深宅大院,是很多人祖祖辈辈的梦想,就像我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想拥有这样的老宅一样。
高高的山墙,即便在阳光灿烂的正午,它所沉积的耄耋之气,也足以让你以暮色视之。傍晚时分的宁静,让它显得老旧,自然也就愈发地庄重而悲悯,瞬间就让我追寻旧物古迹的心思手舞足蹈。青石墙基风化严重,那是无法修复的时间,无声地层叠着过去,虽然经过不断粉饰和修葺,石头的斑驳和木头的腐朽,都在指正着时间本来的寒冷、无情。对于旧物古迹,要保留它的温度和姿态,一直就很艰难。
有几个孩子站在老宅门楼东侧田坎上,对着荷塘中央的几朵荷花指手画脚,看得出来,他们正在商量摘荷。挨近路边的荷花已被路人摘光,剩下的几朵纯白,在距离塘坎稍远的荷塘中央,有些孤单地坚守着一池浓绿。如果我是孩子,早就挽起裤腿下到了荷塘,就像我在那个年龄所做过的一样。用不着犹豫,无知者无畏,为了达到目的,无须虑惧荷塘水深水浅,卷起裤腿下到池塘就是了。孩子们的快乐,没有成人的那种顾虑,任何时候,都不用担心生活中会有很多的陷阱。小时候下河抓虾摸鱼,只是脏了衣裤,顶多回家以后,被母亲数落几句。不过,在我年幼的时候,绝不会为一朵花的美丽而去冒险,最大可能是为了泥鳅黄鳝才无所顾忌。
花朵不是粮食,在肚子没有填饱之前,世界上有很多的美好不在饥饿者的视线里。当年的乡村除了认识粮食,对花朵的身份不明就理。一个被饥饿频繁纠缠的孩子,自然更关心田野里即将成熟的稻谷,以及山原谷底四处飘散着的迷人而热闹的秋收气息。
这是一个露出污泥的荷塘,它的边缘紧挨着哨所湾的门楼。塘水轻浅,鹅和鸭子留在淤泥上的爪印清晰可见。荷叶浓密,伞叶上方,已有几茎莲花苞稍显性急,匆匆露出自己青嫩的身子。孩子们如果下到塘里,可以轻易地藏身,我当年在荷塘抓鱼摸虾就是那样干的,不管母亲站在塘坎上如何叫喊,她永远看不清荷叶下方笑容满面的秘密。
在川东大竹县哨楼湾的傍晚,我很愿意成为荷塘边的孩子,但我不会因为一朵美丽的荷花下到淤泥深深的水塘,一如老宅里坐在檐下摇扇乘凉的老乡,永远不会像我一样,因为见到布满青苔和薅草的青石老墙兴奋不已。我知道,这是久居都市的一种病态,也是生命滑向暮年的信号。这些年,我的相机在流浪途中,总是为旧物旧迹的日渐稀少而失魂落魄。
显然,孩子们最终没有下塘,嘻嘻哈哈一阵,纷纷沿着田间小径陆续消失在炊烟轻笼的田野。孩子们并不知道,我所看到的这个黄昏,会在多年以后,必然成为他们心中格外想念的背景。
没有听到犬吠。房舍四周倒是有密密麻麻的蚊虫在飞舞,它们原本很尖细的叫喊因为“蚊子王朝”时刻的到来,显得异常兴奋和喧闹。
大竹是苎麻之乡,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植物,在川东这片浅丘地区,到处都能看见它们。有的在土地里生长,有的浸泡在稻田溪流的一角,有的堆放在檐下,有的晾晒在竹杆上……在路上,你随时都可能见到背负着一肩苎麻的农人。眼下,我就看见一个妇人端坐在自家院坝,正用夹在拇指和示指上的铁夹,认真地剥离着苎麻的皮衣。整洁的水泥地面上已经有一大堆苎麻皮衣,麻瓤栓成一个花结,整齐地码放在竹编大斗腔里(大簸箕),给人一种劳动的井然有序。男主人端着饭碗坐在柴房门槛,细嚼慢咽的样子很是闲适。大黄狗远远地监视着我,并不停地在堂屋前方走来走去,给人强硬而又危险的警告。这是一条凶猛的公狗,外婆和母亲从小就教导过:叫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
这样的景象,我太过熟悉,我曾经在梦里千百次来过这里。金黄的稻穗和柏树枝叶,扶着微风在耳语。炊烟飘散在竹林丛中越聚越密,它们会一直站到夜的尽头,成为黎明时分最纯净的人间烟火。我能在越来越沉的暮色中,准确分辨出牛儿竹、硬头篁和慈竹的生长区位。它们各自的模样,就像布景在我记忆的故乡,即便双目失明,依然方向明确,随时都能准确辨认。周边散发出苎麻被水浸泡之后,浓烈而又清润的气息。这种气息很容易让我的感官恍惚,时间瞬时倒转,似乎看见外婆坐在石灰坝子边缘纺麻线,院落里弥漫着薰蚊柴草的刺鼻烟气。装满针头线脑的竹篮上面放着一把棕叶扇,老人偶尔会停下手中的活计,用它驱蚊。母亲很可能在柴房做饭,灶膛里不时有桔杆或瘪壳的豆角在爆响。鸭子们嘎嘎嘎地叫个不停,大摇大摆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异乡的这个傍晚,充满柴烟、苎麻和牲畜粪便的味道。苎麻对于我的记忆,虽遥,但无间隔。麻衣、麻裤、麻鞋、麻蚊帐、麻被子、麻毛巾,过往生活中,一切暖身近体的东西,无一不和苎麻亲密相连。现在的麻卖不了几个钱。以前还可以用来纺线织麻布,现在再没人穿它了。我们连蚊帐都不用挂,点个灭蚊器,啥子虫虫都没得。
细细端详,这个大姐和我外婆当年一般年岁,手脚十分麻利,也很健谈,一边干活一边和我唠嗑。在大竹遍地生长的苎麻,早就离开了农家的纺车和织机,这种到处都能生长的物种之所以在大竹还能存续,一半源自传统,另一半因为管理简便,无须施肥撒药松土,多少也能给农家添加一些收入。苎麻去皮晾干全部廉价卖到了麻纺厂。这些温暖过漫长历史的苎麻,如今经过化学和机械处理以后,完全脱离了它原始的属性。实际上,经过现代化工厂加工的苎麻,更加美观和贴身。我们一直在改变这个世界,源源不断地颠覆着传统,所有深具个性的事物本相,已经被科技改变得面目全非。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真相,真相已经不再重要,所有的真相就是彻底改变真相。粗麻布衣哪有细纱软线美丽?社会在进步,在更加接近我们想要的那种文明。我怀旧病态中的焦灼,只不过是刻意在僵冷面孔下的一相情愿,完全忽略了坚持传统和维护个性所要支付的时间和生命成本。
青砖黛瓦的房子已经难觅踪迹,越来越多的水泥房顶也没有炊烟升起。我日渐麻木的感官,对记忆中的稻谷香味无从感受。虽然我被包围在行将收获的田野,稻谷成熟的香味却并没有进入我的感官。我只是在想象中,非常刻苦地捕捉着它的气味,以及,回响在时间深处的阵阵蛙鸣。我总是妄想时光回转,就像我在寒夜中不停地行走。乡村暖色的背景,以及家园的地址存在,不管如何努力,我的精神已不能安全地还乡。
漫无目的地穿行在秋野田畴,稻谷以金黄的色彩铺满大地,一直伸向火烧云点燃的天际。
偌大的停车场只剩下我那辆满身灰尘的汽车,在沉静的暮色里,用一种刺眼的方式,完全破坏了这个可能会更加古老沉静的乡村黄昏,让我的身份一下子变得十分孤立。我越来越厌恶我的城市背景,标注在身体上的每一个标签,大多和利益攸关,全部努力,以获得更加优越现代的生活。而习惯就像魔咒,把我封印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一个人的精神就是所有人的精神,一个人的历史就是所有模糊不清的历史。这种病态的轮回,让我们的精神荒芜,杂草丛生。
我对乡村并不陌生,在我离开鸡鸣犬吠很多年以后,不管是哨楼湾的傍晚,或是保管在我心中的故乡,它们对我潦草的缅怀已然陌生,就像我经常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弄不清出处和去路一样。
胡大妈出现在这个傍晚尽头,我并不知道,这次邂逅会成为一生中,最干净的一次“交易”。她从瓜架下方探出头颅,我恰好经过她的身边,筲箕里刚刚摘下的丝瓜和黄瓜,激发了我对乡村田园持久的热情。没有打过农药,都是种来自己吃的,大哥买点?胡大妈随口一句戏言被我当真。我对大地上生长的一切,从来都是充满深厚的感情的。我赶紧掏出十元纸币,接过胡大妈手中的筲箕。胡大妈说,钱太多了,我再给你摘一点。挂架上剩下的丝瓜,大多结瓤,蓄留做种,以前人们用干瓤洗碗刷锅。还有几只青嫩的丝瓜长在瓜架高处,即便踮起脚尖,也很难摘到。看到胡大妈在瓜架下一次次跳起身体,我很是过意不去。最后在陆续到来的农民兄弟帮助下,摘下了瓜架顶端的丝瓜。胡大妈一再念叨给我的菜蔬值不了十元钱,非要把我引到她家堂屋,用青椒、玉米和苦瓜把手提袋塞得满满的。
多拿点,我明天要进城看女儿,一个人也吃不了。纯朴的唠叨,就这样,把我的内心也装得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