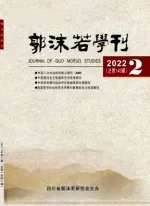海与岸的交响——谈《女神》中诗歌的情绪与表达
张 欣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对于郭沫若的《女神》,不同人有不同的见解,或欣赏它充满动和力的狂飙,或批评它语言的粗俗叫嚣、毫无蕴藉,或指责它缺少本土化的地方色彩等等。正所谓诗无达诂,一般的接受者可以见仁见智,从事研究的人却应该抛弃那种凭借一己审美取向的好恶来对诗歌的表层文本发表言论的做法,而是更应该抱着一种体贴的心情走进诗人用自己的理解、感受所营造的诗歌世界,在那里发现郭沫若诗歌创作中的独特规律。本文就是笔者在此原则指导下所展开的一点初步尝试。
一、诗歌本体——有节奏的情绪世界
想要走进郭沫若《女神》中的诗歌世界,首先要做的就是明确当时郭沫若自己对于诗歌本体的理解。这种对诗歌本体的理解、阐述既是先于诗歌创作而存在的前理解,又是对自己在诗歌创作过程中体验、感悟的总结,抓住了它就等于抓住了郭沫若与诗歌关系的过去和现在。郭沫若标举“主情主义”的诗歌本体观,强调“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诗是情绪的直写”“诗的创造便是在感情的美化”“情绪的律吕,情绪的色彩便是诗”。这种诗歌本体观直接影响到郭沫若诗歌创作的视野和情绪体验的存在方式。
郭沫若的诗学观念和早期白话新诗相比发生了质的突破,正如梁实秋所说:“新诗运动最早的几年,大家注重的是‘白话’不重‘诗’,大家努力的是如何摆脱旧诗的藩篱,不是如何建设新诗的根基。”[1]早期白话新诗忽略了对诗歌本体的探讨,只在语言载体(白话)上做文章,在对仗、用典、格律等技巧和功用的层面上颠覆设防。一方面致使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凝聚情感的特定意象、典故缺失,更重要的是将传统诗词中抒情的思维方式加以有意排斥;另一方面将用于日常经验交流、生活现象描述的白话引入诗歌创作,却又忽略了情感对语言的茹润和艺术对语言的打磨,使其不能在短时间内创造出能够负载新情感的意象,更多地延续了白话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即呈现出诗的日常经验主义倾向。
诗风到郭沫若为之一变的根本原因是,郭沫若将诗看作诗,忽略了“用”的层面上细枝末节的束缚,复归到诗歌的本体思考:个体情感。正是因为人的情感体验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国界、越时代的特性,致使郭沫若凭借主情这一观念,不仅跨出了早期白话新诗的局限,打通了从诗经时代就开始的古老诗国的作诗经验,反复强调《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乎声,声成文谓之音”与自己诗学观念的契合,[2](P336,P349)也打通了和中国之外其他诗人沟通的鸿沟,呈现出中西诗人并举的现象,“将屈子的《离骚》、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李杜的歌行,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统归为‘雄浑’的诗,将周代的《国风》、王维的绝诗,日本古诗人西行上人与芭蕉翁的歌句,泰戈尔的《新月集》统归为‘冲淡’的诗。”[3](P14-15)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忽略了个体之间差异的并举,是因为郭沫若诗歌的个人情感本体论使他不会屈就于任何单个诗人的影响,他只在他的阅读对象中寻找与自己“振动数相同”“燃烧点相等”的那一部分,只求刹那间的情感契合而非全盘接受他的阅读对象,这致使郭沫若的诗歌接受呈现出一种穿梭于古今中外的跳荡,即如他所说,“我每逢着这样的诗,无论是新体的或旧体的,今人的或古人的,我国的或外国的,我总恨不得连书带纸地把他吞了下去,我总恨不得连筋带骨地把他融了下去。”[3](P14-15)他常常由外国诗人的作品而联想到他所喜欢的中国古典诗人的风格,比如由泰戈尔、海涅而想到陶渊明、王维,由斯宾诺莎而想到庄子、王阳明,由惠特曼而想到屈原、李白,并用这种中国固有的古典风格对这些外国作家加以命名。由此可见,这种跳荡是以中国古典诗歌作为前理解的,骨子里透着的还是中国风韵,即在打通古今的同时,捎带着通过连类取譬的方式将中国之外的世界诗歌纳入自己原有的诗歌知识体系,并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古典诗歌存在的合理性。
郭沫若在打通诗歌本体的同时,也就复活了情感的载体,这种载体可以是意象、典故、语言形式技巧,但更为本质的是抒情过程中的运思方式,在本文中笔者名之为“岸”——情绪的依托。诗情、诗语固然可以因时代而变,但是表达情感的思维方式(诗思)是一种内化于头脑里的记忆、习惯、看问题的方式,只要主体不要像早期白话新诗那样刻意地对它设防,它就会在有意无意中参与到为情绪情感赋形的过程中去,使得文本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意蕴。与此同时,情绪作为诗歌本体,既可感,又无形,并且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只有把握住郭沫若体验情绪的特质,才能不至于把郭沫若这一个与其他人混淆。那就要追问郭沫若的诗歌情绪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对此他是这样自述的:
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便是诗地本体,只要把它写了出来,它就体相兼备。[3](P14-15)
我从前有过一种想法,我以为大宇宙的生命就是音乐,它是无差别的,无形相的,无内外的,一片生动的流,然而又是极有条理,极有秩序,极有抑扬顿挫的,和谐的海。——不,不是从海外面看的海,是从海内面看的海,我不是在一切的外边,我是在一切的内边。[4](P78)
将诗歌创作时的情绪取譬于海,海不是作为具体的意象而存在,相反,海是郭沫若感知情绪的方式,也是情绪在诗人心底的存在方式,它时而滔天巨浪,时而涟漪泛泛,但都具有本体意义。而海心就是郭沫若在自己情绪之海中自身的立足点,他所看到的海,四维无边的宏阔、色调单一的紧张、宏大简单的流动,正是这种感知情绪存在的方式将原本诗人心中无形的情绪感觉转化为可视、可感的物理心象,还原了“情绪自身本是具有音乐与绘画二作用”。外界的一切刺激都会转化为这一心象的千变万化,而将这种种心象(海)用特定的思维方式、诗歌技巧(岸)加以自动生成的结果就是郭氏诗风的诞生,即“诗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不是用人力去表示情绪的。)我看要到这体相一如的境地时,才有真诗、好诗出现。”[5]
二、诗歌表现——海与岸的交响
由上文的论述可知:郭沫若从诗歌本体的思考出发,在标举主情主义诗歌观的同时,无意识地打通了古今中西的诗歌壁垒,将中国传统的抒情思维和抒情方式转化到现代新诗。这些元素在与郭沫若所特有的情绪存在方式——海相结合时,呈现出以下三种鲜明的诗歌形态:
第一,将海的情绪状态直接转化海的意象书写。这是内外转换最为直接的方式,在观物取象的层面上体现了传统古典诗歌物我融合的精义,可是,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现实的海浪固然可以模拟心海的波澜,但心海中那些抽象的个人体悟却无法转化为海的言语,所以海的意象常常会被浓烈的个体理念胀破,抒情主体不断地跳出来,将那种抽象的感受用口号式的语句叫喊出来,例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诗的前半部分还沉浸在将自己精神的一瞥投注到白云、北冰洋、太平洋的宏伟壮丽的情景,但是这种壮丽还不足以融汇诗人的抽象感慨,他在后半部分不断地叫喊着“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浴海》的第一节写“我”在无限的太平洋所营造的圆形舞场中“血同海浪潮”“心同日火烧”的情感同一状态,但在它的末尾就又叫嚣着要在“这烈日光中放声叫”,第二节更是招朋引伴强调“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中华底改造/正赖吾曹!”将心理海洋与物理海洋直接对接、转换,它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物我交融的困难,前后情调的难以为继,即在试图达到物我交融这种传统审美境界时出现了现代与古典情调的断裂感,相类似的还有《梅花树下的醉歌》,虽然吟咏的不是海洋,但却呈现出相同的审美风格。
第二,用抽象语言的风暴去模拟海的情绪。既然要去模拟海洋的情绪,那么我们就不得不结合海的特点来谈郭氏语言构形的特点。除了海,郭沫若还曾经将情绪比作“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弦上弹出来的Melody”,这些取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强调一种整体的流动感而不是静止的点段。那种横截面式的品味在郭沫若诗中是没有意义的,获得的不过是一两句标语口号似的叫嚷,相反,只有在简单的语言结构、粗暴坚硬的用词、单一的色彩泼墨和复沓咏叹所模拟的情绪浪涛中,你才能感受到郭沫若诗歌中那种绝大自信的冲击力和饱满的生命力。
海浪——诗人情绪的沸腾。这种为沸腾赋形的重章叠唱手法取自《诗经·国风》,但是他用海的磅礴精神冲破或者说改造了传统意境中的清新干净,化作波澜万丈的情感浪涛从你的心胸、你的喉咙、你的嘴唇中喷薄而出,语言的超快感伴随着情绪上的高峰体验,那是因生命活力的迸发而感到的我心飞扬。例如《匪徒颂》,
一
反抗王政的罪魁,敢行称乱的克伦威尔呀!
私行割据的草寇,抗粮拒税的华盛顿呀!
图谋恢复的顽民,死有余辜的黎塞尔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政治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二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底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维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三
反抗婆罗门的妙谛,倡导涅槃邪说的释迦摩尼呀!
兼爱无父,禽兽一样的墨家巨子呀!
反抗法王的天启,开创邪宗的马丁路德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宗教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
全诗六节,咏叹加复沓,每一句都形式简单直白,但是有力度的大词、硬语镶嵌其间突出了每一句的强度,多个有力度的句子相叠加,堆积成一排巨浪构成一节,节与节之间通过部分的重章叠唱连缀成连绵不断、前赴后继的滔天巨浪破空打来,语言本身没有深意只有语流恣肆所形成的目无古今、心无南北的刹那间力的快感、力的叫嚣,这样的诗歌还有《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晨安》等。
海心——诗人情绪的立足点。诗人是被情绪的洪流所包围的,他的情绪感知视角是四面八方全方位的,给人一种站在宇宙中心看海浪不断延展的整体宏阔感。《女神》中的这一类诗歌大都呈现出一种东南西北、前后左右的全方位汉赋般的铺排,包笼宇宙、横锁四野,用这种巨大的空间感来为五四时代中西古今交汇的时代心理赋形是再适合不过的了。例如《晨安》以太平洋为世界的中心从西海岸的中国吟咏东海岸的美国再回到太平洋上的岛国扶桑,《凤歌》更是以自己所在的丹穴为中心控诉了“我们飞向西方,西方同是一座屠场!我们飞向东方,东方同是一座囚牢!我们飞向南方,南方同是一座坟墓!我们飞向北方,北方同是一座地狱!我们生在这样个世界当中,只好学着海洋哀哭!”的整个世界!但是这种情感的奔突叫嚷带来的最大弊端就是狂飙而来,狂飙而逝,语言的快感所夹带的情绪快感过后是自我被无限扩大后的无所皈依感和情绪倾泻被掏空之后的空虚感,不耐咀嚼、没有余韵。
第三,用传统的抒情思维去承载海的情绪。这是最深层、也是最具复杂性的海岸交响。它可以是将海的情绪转移到传统诗歌创作的情境中,比如说登高望远、临海望月。情感抒发时营造熟悉的环境,再伴随着海的情绪对周边外物环境的弥漫——以海的节奏、气势、神色移就到所观看的外物之上——在使原物保持自身属性的同时又添加了另一层“以耳视,以目听”的神韵。例如登临望远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最为经典的氛围之一,那种“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的审美心理积淀在每个中国文人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而《笔立山头展望》:
大都会底脉搏呀!生底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底波涛,瓦屋底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
自然与人生底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箭呀!
人底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沈沈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这首诗之所以能够被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审美倾向不尽相同的接受者所认同,一方面是由于诗中充满了现代文明的动感,这动感是海的情绪对都会脉搏的感受、对山岳瓦屋波涛汹涌的移情体验以及语言赋形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登临望远这种传统抒情氛围的熟悉,对这种将自然与人生并置的思考方式的熟悉,而这一方面的功用恰恰是使全诗情思得以展开的承载框架和平台。无独有偶,《蜜桑索罗普之夜歌》将心海的宁谧投射到无边的夜空,营造天上人间的梦幻天海,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的情感氛围在诗中得以某种程度地场景复现,既是陌生的唯美,又有古旧熟悉的情调,难怪闻一多也不得不称它“是个特别而奇怪的例外”。
如果说创作情景、情调和观看对象的熟悉还属于是抒情思维的外部渗透,那么,内部具体操作层面的渗透就更为本质,主要体现在对单纯情思进行改头换面的过程中传统抒情思维方式的融入。中国古代社会的思维是一种比附性思维,将自然人伦化,而君臣、夫妇的人伦关系又是异体同构的,试看曹植的《七哀诗》:“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从表层看是讲尘与泥的异势,夫与妇的分离,深层意义上暗含的是君(曹丕)与臣(曹植)的不见信。而这种思维方式在《女神》中屡有出现,比如《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日暮婚宴》《死的诱惑》等将眷恋祖国的情绪、人与自然的亲密、自然万物间的和谐等原本简单的情感利用比附的思维方式转化为异质的形象,这就会出现一种思维的叠加,最明显的是《炉中煤》诗中将“炉——煤,黑奴——年轻的女郎,诗人——祖国”这三层进行叠加、比附。形成了诗歌本身涵义上的纵深感和层次感,召唤阅读者去透过表层结构去挖掘深层意蕴,这就使得这些诗篇别有韵味,值得再三涵咏。但对于那些熟悉这种思维方式的读者,它所取得的效果就仅仅是观新而温故,获得一种感受上的顺遂、因熟悉而产生的会心而已。从本质上说这类诗歌还是旧的气息太浓,还不能算是上乘,因为它的程式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最具郭沫若鲜明个性的海的癫狂。
笔者发现,只有当郭沫若海样性格最大限度地化身为巨大、飞动的原始意象时,才能够激活传统的比附思维,如《天狗》《凤凰涅槃》。这不同于前文所说的“将海的情绪状态直接转化海的意象书写”,因为前者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看已经外化了的情感形象,却又忍不住跳出来喊口号,形成前后情调的断裂。而这里是将自己最大限度地融汇到意象中去,是一种无距离的比附,我就是天狗,天狗就是我。此时的形象就是郭沫若的血泪、自叙传、忏悔录,不论他如何叫嚣他都是天狗,赋予了全诗一种整体意象的完整性。在这种完整性的包容下他还可以将用抽象语言的风暴去模拟海的情绪的方式纳入其中,如天狗海一样的叫嚣着“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经上飞跑。”短句叠加、急凑迫近,传达着海一样瞬息万变一泻千里的情绪,既获得了自我表达的自由而又避免了粗俗无蕴藉的弊端。加之这意象又是如此的久远,久远到可以涵盖整个华夏民族的历史,凭借着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记忆,汇聚成一个时代、一个种族的大我的声音,惊破寰宇。只有这个层次上的郭沫若《女神》诗歌才是开一代诗风的近乎完美之作!
郭沫若的《女神》既不同于晚清诗界革命以新意境融旧风格,也不同于早期白话新诗那样强调在语言形式上与古典诗歌的断裂。因为它们都是以二元的思维去思考新诗的创作(以此入彼或是非此即彼),而《女神》是在诗歌本体是主情的基础上的无分彼此,服务于自我情感表现的拿来主义,既新且旧、新旧交融,在海与岸自然而毫无强迫地交响中创造出崭新的审美境界。无论这种境界好或不好,在今后都无法复现,这种不可复现的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他存在的独特意义。
[1]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J].诗刊(创刊号),1931 年1月。
[2]郭沫若.论诗三札、文学的本质[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3]郭沫若.《郭沫若致宗白华[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4]郭沫若.高渐离[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七卷[M].
[5]《时事新报·学灯》,1920-2-24 .
参考资料:
[1]胡忱、王泽龙:《近三十年郭沫若〈女神〉研究综述》,《郭沫若学刊》2009 年第3期。
[2]陈永志:《〈女神〉校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9月。
[3]桑逢康:《郭沫若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年1月。
[4]李怡:《超越于时空之上的自由——关于郭沫若感受方式的一点札记》,《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年.
[5]王爱军、魏建:《郭沫若诗歌研究述评》,《郭沫若学刊》1996 年第l期。
[6]李怡:《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郭沫若诗歌的传统文化阐释》,《郭沫若学刊》1994 年第3期。
[7]《三叶集》《文学论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
[8]王富仁:《审美追求的瞀乱与失措——二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北京社会科学》1988 年3期。
[9]王富仁:《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境界》,《郭沫若研究》1988 年第7期。
[10]王训昭、卢正言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