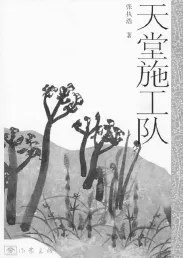身后事与生后诗
■李以亮张执浩

李以亮(以下简称李):《糖纸》作为成名作的意义是很显然的,我们谈得很多了,这里不再多谈,虽然你也说以它为代表的风格化写作持续时间是太长了。《美声》在我看来应是你第二阶段的总结性作品,无论评论界还是我们相互之间也已谈得比较多了。我虽然写过一篇关于你的诗歌写作的长文《<美声>之后》来探讨你第三阶段的诗歌写作,但让我讲出标志性的篇目来,我还觉得困难。这说明这个转变不是突变,而是“渐变”——这表现在《亲密》和《覆盖》二大组诗的写作上。而此之后,我感觉你的诗歌变化更大了,你的“音质”似乎都变化了,调性发生了很大改变,“喧叙调”代替了“咏叹调”,语调更加沉静,舒缓,偏冷,同时,在语言选择上,口语成分在增加。我个人感到《无题十六弄》无论在分量还是阶段性转变方面,也无妨作为标志性的篇目来对待。
张执浩(以下简称张):你的这个观察非常准确,尤其是你谈到的“音质”和“调性”的变化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写作中最为关注的。很多诗人似乎不太在意这些,但我在诗歌写作中是非常讲究音调的,这可能与我长期生活在音乐学院这样的环境里有关。我总认为,诗歌之所以是诗歌,首先在于它的形式,其次是语言的节奏感,还有腔调。诗歌就是一种古老的技艺,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的“思想性”也是这种形式的附带品。有的人写了很多年的诗,其实并不明白诗歌为何物,因为他只是想表达,他并不尊重诗歌这样一种形式。譬如,诗歌为什么要分行,每一行代表了什么,在什么地方转行换气是最恰当的,你都要去思考,反复推演。
《无题十六弄》由16个片段构成,为什么要叫“弄”呢?“弄”并不仅仅表示一段,其实还有一种潜在的调性。这首诗写于2005年春天,写成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些困扰过我的东西豁然开朗了,再之后我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从容。所以,这首诗肯定可以视为我写作生涯中的一次转变。这种转变我自认为体现在处理题材上面不再有顾忌,信手拈来,日常生活随我所用,不再拿腔捏调。
李:在《美声》为代表的阶段,我见到有人将你界定为一个精于隐喻的诗人,精于隐喻而长于抒情。多年来,诗界有个说法叫“拒绝隐喻”。发明权归于杨黎还是于坚可能不太重要,我看到的现象是这种主张倒是的确影响了不少人。你怎样看这个比较著名的说法?
张:“拒绝隐喻”的说法必须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才有效。事实上,我们现在对诗歌(特别是现代汉诗)的所有论断都是有时效性的,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准则。隐喻作为一种古老的诗歌技法在中外诗歌史上曾成就过许多杰出的诗篇,只是到了我们这里,在一些蹩脚的诗人手里它才变得艰涩,变得僵硬。一些打算不说人话的诗人故意兜圈子,把诗歌变成了智力游戏。这才有了“拒绝隐喻”的主张。我曾经说过,诗意不是诗歌,月光不是月亮,如何在也已成型的文化尘埃中发现真正的诗,肯定需要不断提升写作者个人的修为。
李:是的,鲁热维奇就讽刺过:“一个糟糕的隐喻是不朽的。”“拒绝隐喻”应该是拒绝那些糟糕、蹩脚的隐喻。我感觉,在《无题十六弄》之后,你还有一些变化。先说第一个,那就是我以为在你的诗中反讽的成分在加大。《无题十六弄》在我看看来充满反讽。另外许多短诗也是:“街道上到处都是看免费洋相的人”(《荡漾》)、“老子吃了一辈子土豆,还要吃官司”(《老黄》)、“一头称职的困兽”(《野兽为什么总有迷人的气息》),还有《唏嘘》、《少年与猴王》等几乎通篇皆是。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人都开始“反讽”。我自己在2000年前后也热衷于此,时间长了觉得是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诗变轻了。后来看到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论反讽。他有一个观点,反讽不能提供任何正面的指引。“在反讽的世界勾留得太久,唤醒了我们对不同的可能更有教益的作品的渴望。”的确如此。
张:在一个“变态即常态”的时代,诗人何为?我经常问自己。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的确迥乎有别于以往的任何时代,首先体现在,时间的整体性被打碎了,拼贴,剪辑,强行植入与瞬间修正,以及戏剧性、无厘头的元素充斥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这样的境况下,适度的反讽可以减缓我们生活的难度。我也希望自己具有“正面强攻”的勇气和力量,但目前,我还只能写“能写的东西而非想写的东西”。
扎氏的说法提醒我们,文学要有庄重感,但对庄重感的获得必须要求写作者具有神圣而庄严的情感基石。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及当下我们写作者尚未学会处理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每当我们试图表达公众情感时普遍显得幼稚,为什么会这样,真的值得思考。中国是一个没有严谨宗教的国度,我们现有的文化资源在许多情况下是相互冲突的,庙堂与山野,入世与出世,都有可能结出文学奇葩,但也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单一的文学认知审美向度。我感到,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困境是,在庞大的体制之下写作者的自我放逐,既缺乏恒定的操守,也缺少心灵的丰富性。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作品都是事先存在于既有的阐释系统里面的,没有挣扎,没有质疑,更谈不上反抗。
李:当世界的无耻无信无义无情和荒谬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时候,反讽意识,即承认我们的无知,就成为必然的缓冲带。你的这些体察和思想很有价值,对人很有启发。我想说的第二个变化,是我感到你越来越有了“介入意识”,如新年你的第一首诗就叫《大泽乡》。是这样吗?对于诗的介入,诗人们的态度是复杂的。但比起一味唯美或再走形式主义路子的诗人来说,我更欣赏介入的诗人。
张:诗歌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种:写给自己的,写给心目中预期的读者的,写给任何人的。《大泽乡》无疑属于第三种。《大泽乡》之后我还写了一首《中国候鸟》,今后我打算写一批这样的诗。如果你留心了我最近这两年的写作,你会发现这样的变化其实一直在孕育着,包括我去年写的《什么意思》,甚至是前年写的《你有多久没有接吻了》,这些诗实际上在试图“介入”当下的公共情感生活空间,它们采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只是直接面对,坦陈我们内心生活里那片隐秘其实也是公开的区域。不过,今年初的这两首在选材上面可能更具普遍性,或者说是社会性。
一方面,我们承认诗歌“无用”,另一方面作为诗人我们又心有不甘。诗歌究竟有没有力量进入当下的公共生活?我认为,诗人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价值观混乱无序的时代,诗歌至少可以做到像闪电一样给迷途中的人以方位感,哪怕是短暂的。所以,前不久我们在新浪微博上发起了“微博体(Twitter)诗歌”的倡议,希望出现更多的、能够直接率性地面对我们生活和生存困境的作品。也许这样的写作并不足以对我们的生存状况产生多大影响,但它至少可以修正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社会时的贫血,苍白和怯懦。
李:这其实还是一个诗歌能否面对大众发言或者如何面对大众发言的问题。要介入,我以为,可能真还离不开你提到的情感问题。说起“微博体(Twitter)诗歌”,我认为作为尝试无疑是可以的,至少可以加强诗歌的及物性,而我们看到的太多诗歌的确太无关痛痒了。
第三个变化是我感到你现在更多地写短诗了。这些短诗构成了台湾版《动物之心》第二卷的主要内容。以前你在一个访谈里提到过长诗写作的方方面面,都是你的一些独特心得。我知道的很多著名诗人其实是并无长诗的,如席姆博尔斯卡、希尼,而布罗茨基只有个长诗计划(未写完)。但这一点并不影响他们的杰出。北岛在回顾个人创作时也得出了现代诗不适于长诗的看法,虽然他也写过一首《白日梦》。有趣的是,我看现在也有人热衷长诗写作,名字我就不说了。
张:的确,我最近几年没有写作长诗了。关于诗歌的长与短的问题,照我看,当代中国诗人普遍缺乏写作长诗的直接经验。长诗需要写作者的架构能力,除此之外,还需要强大的内在精神推动力,不是说篇幅长就是长诗。我更倾向于将诗歌分为“大诗”和“小诗”,有些诗尽管寥寥几行,却有包纳万象的气象;而有的诗洋洋洒洒数百行上千行,却丝毫没有空间张力。我个人觉得,一首诗的长与短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至于我,为什么更偏爱短诗,是因为我厌倦了那种不断游走的、炫技的、绕来绕去的写作,我更喜欢直接,喜欢把气韵和力量蓄积着,然后一击而中。再则,这是一个看似波澜壮阔其实浪花朵朵的时代,那种冗长的慢节奏的絮絮叨叨的写作,往往是无效的。
李:在你的诗句里,似乎有过将“抒情”和“叙事”并列的提法,比如“长久的叙事之后/不免片刻抒情”、“我想抒情但生活强迫我叙事”。在《<美声>之后》一文里我曾说,在“抒情”和“叙事”之外,张执浩已更多关注人生的“哲理”层面,事实上,这点在你2004年后的作品里表现非常明显。当然“抒情”和“叙事”的成分肯定依然存在,毋宁说“综合”更成为你的特征。
张:我早期的作品基本上是抒情的,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在诗歌中注入了许多叙事的成分,这与我那一时期开始写作小说有关,我曾经用同一个标题分别写过诗歌、小说和散文,譬如《亲爱的智齿》等。这种“互文”写作的练习使我后来越来越走向开放性的文本,不再拘囿于体裁的限制。当我在1997年发出“我想抒情但生活强迫我叙事”的感概时,我是真的感觉到了诗歌写作的危机,这种危机感既有对诗歌这种载体的不信任,也有我对生活的重新认知。
我知道,很多当代诗人是反对抒情的,但抒情性却从来没有因为他们的反对而退出诗歌的肌体。为什么呢,因为抒情性是保证诗歌有别于小说或其他文体的一个关键要素。反对空泛的抒情,反对不及物的抒情,其根本目的还是要回到如何恰如其分的抒情这一点上来。所以,抒情不抒情不是问题,关键是怎样抒情。
把叙事元素引入到诗歌里可以冲淡过于腻歪的抒情,可以使反复空转的情感落实到具体的物象上来,这无疑是当代诗歌的一大亮点,但如果迷信叙事能拯救诗歌就不对头了。至于你说到的“哲理”,我没有专门思考过我的写作,当然,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随着你咽下去的生活内容越多越丰富,你自然会想从中提炼出一些相对结实可靠的东西来,这些东西能够支撑你的人生,前提是你得张开嘴巴将生活遇到的酸甜苦辣都咽下去,消化掉。
李:是的,我理解很多人提出反抒情,其实就是因为不满于空泛的抒情。至于叙事,诗歌肯定干不过小说等叙事文体。诗歌可以而且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搞拿来主义。
你的诗集《动物之心》,是在台湾出版的大陆先锋诗丛之一种。诗集采取的是我认为的诗集最好的编辑体例,即按时间顺序,呈现历时性发展与变化。在80年代中,台湾现代诗歌无疑是给予我们很多启示的。因为他们是得欧美风气之先,但在新鲜感过后,大陆诗人的作品好象已明显将台湾诗人的作品抛到了后面,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你认为你的作品在台湾——“先锋”当然是他们的一个定位——与他们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张:按年代编辑诗集最大的好处在于,你能给阅读者一个清晰的写作脉络,让读者看见你的幼稚和成长。《动物之心》是黄粱先生精心策划的“大陆先锋诗丛”之一本,作为编辑家,他有丰富的经验。《汉诗》去年第2期曾编发过一个“台湾中生代诗人小辑”,也是由黄粱先生帮助组的稿,入选有零雨、黄粱、孙维民和阿芒等诗人的作品,他们都是台湾目前很活跃、前卫的新一代诗人。当时,我们的编辑思想是,通过这个小辑来了解最近一、二十年来台湾诗人的写作面貌。对于早一拨台湾诗人,大陆读者基本上是了解的,但缺乏对这新一拨诗人真的了解。这期杂志出来后,收到一些读者的反馈意见,汇总起来主要是,感觉台湾当代的诗人似乎还停顿在对形式感的追求上,他们的作品缺少对生存境况的关注,再就是语言太生硬,意象过于繁复。以上几点,相比之下大陆当代诗人要做得好些。
我个人的作品嘛,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很多,首先是写作的面似乎比他们宽泛,其次我们使用的是比较成熟的现代汉语,而他们的作品在语言和语感上都过于文绉书面化了。最后一点是,我觉得我们对生存包括生活痛感的挖掘要有力的多。
李:2010年底你又出版了诗集《撞身取暖》。由于种种因为我还没有读到全书。这本诗集与以前你出的诗集有何不同?从诗歌受众角度来说,你的作品算是比较有人缘的。这其中成功的秘密你认为在哪里?
张:《撞身取暖》这部集子收录的是2003年到2009年底的作品,共计119首。以短诗为主,突出阶段性比较重要的作品。我不是一个写作量很大的诗人,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平均每年也就二十来首诗,一个诗人的作品被人喜欢,于作者而言固然是件幸事,但我其实不是那种会“讨巧”的写作者。如果让我来谈,我要说我只是忠实于自己,用平常心来对待写作,对读者尽量少玩花招,要时刻记住,不要低估读者的智商,他们在很多时候远比你深刻、聪明。
李:说得好啊。屈指算来,你自进入自觉和成熟的诗歌写作也有二十多个年头了。虽然现在来谈一生的“题位”也许为时太早,如果用比较简短的话概括一下,你可能将自己诗歌写作的终身“题位”放在什么上面?
张:诗歌是一种技艺,需要心智上的修炼与挖掘,更需要生活的不断充盈与磨砺。一个好的诗人,你总能看到他(她)在成长,他(她)始终葆有好奇心和敏锐的感受力。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希望至少能写到六十岁,那时候大家还认为我是一个诗人——不是因为以往写过诗,而是觉得我还可以写出好作品来。
李:谢谢你接受我的访谈,让我受益颇多。借此机会,祝你新年如意,创作丰收。
张:也谢谢你牺牲节假日和我做这次交谈。祝新春大吉,多出好作品。